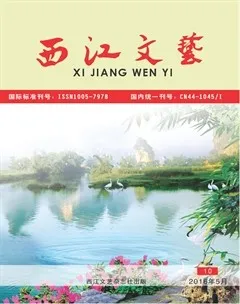論汪曾祺小說的佛教色彩
王雪梅
【摘要】:汪曾祺的小說和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問題,在學術界曾經引起了廣泛而熱烈研究。時至今日,這方面的研究已經基本達成一致,即汪曾祺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作品中深刻的體現了傳統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本文的研究立足于汪曾祺的小說作品,對其小說進行仔細研讀,結合大量汪曾祺作品的研究資料進行分析和研究,試圖揭示汪曾祺與中國傳統的佛教文化之間的關系。
【關鍵詞】:汪曾祺;小說;佛教思想;禪宗意蘊
一、 汪曾祺對佛教思想的接受
一個人接受某種思想必然會有特定的原因,并且這種接受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伴隨著人生的成長,來自于家庭、社會、周圍的生活環境等因素共同影響,才會使一個人慢慢接受某些思想并形成自己的世界觀和人生觀。
首先,汪曾祺的家鄉對于他佛教思想的接受有重要的影響。汪曾祺的故鄉在江蘇省的高郵市,而在汪曾祺的筆下,尤其是新時期以來的作品中,高郵成為了汪曾祺先生魂牽夢繞的地方,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關于故鄉的風土人情的。
其次,長輩對汪曾祺佛教思想的接受也有重要影響。我們知道,孩童的人生經驗和知識的獲得都是來源于自己的家長傳授和周圍環境的影響,從這一點上,汪曾祺小時候思想的接收是深受家庭影響的。汪曾祺的家庭在舊時代的高郵是一個大戶,是一個舊式地主家庭。
最后,汪曾祺的經歷養成他隨遇而安的人生哲學。汪曾祺在家鄉度過了他的青少年生活,他在這里讀了小學、初中和高中。讀高中時正逢抗日戰爭的爆發,到處輾轉躲避戰亂因而導致學業時斷時續。正是在這一時期,他和家人到鄉下的一個小庵住了幾個月躲避戰亂,這幾個月對汪曾祺來說是全然不同于他日常的生活,這是他近距離接觸佛門生活。這段生活經歷給汪曾祺提供了豐富的佛教的養料,《受戒》里的菩提庵、僧人和英子一家的原型都源自于此。
汪曾祺的思想中是切實存在著有關佛教思想的,這些思想是來源于他在家鄉寺廟中的見聞感受,源于他家庭生活的影響,源于他的長輩的言傳身教,源自于他復雜多難的人生經歷的歷練。這幾個因素結合起來促使佛教思想在汪曾祺的腦海中生根發芽,占據一定的地位。作為一個作家,汪曾祺必然要通過作品來展現他的思想,對社會和人生進行關照,這使得他的作品呈現出一種富含佛教思想、禪宗意蘊的獨特樣態。
二、佛教思想在文本中的流露
汪曾祺的小說通過童年、青年的眼光來描寫自己故鄉的風情和人物,呈現出一種清淡委婉、平淡自然的狀態,隱含著他對于生命形式和生活樣式的獨特追求,流露著自己獨有的思想,其中包含有一些佛教的思想。汪曾祺在他的小說中所涉及佛教思想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是一些佛教思想的基本展現,另一方面是一種富于禪意的生活情趣的體現。汪曾祺在小時候的生活受到了來自于家庭和家鄉生活的影響,使他對佛教思想和寺廟生活都有直觀的了解。有了這樣的文化積淀,他所寫的作品或多或少的涉及了佛教思想和佛教題材,他通過小說中佛教思想的流露表達自己對于人生和社會事件的關照。 這些作品有的是題材直接取自于佛門,如:《復仇》、《幽冥鐘》,有的則是反映佛門生活的,如:《受戒》、《廟與僧》、《仁慧》、《三圣庵》等。我主要以《復仇》、《幽冥鐘》、《螺螄姑娘》三篇小說來闡述一下汪曾祺在小說中涉及到的一佛教思想,如:冤親平等、救苦救難、現世報應等。 汪曾祺在他的小說中并沒有涉及更多的有關佛教的思想,他的作品更多的是在整體上呈現著一種富有禪意的生活情趣和生活樣式。
汪曾祺曾經這樣講到:“小說是談生活,不是編故事,小說要真誠,不能耍花招”,認為“現代讀者要求的是真實,想讀的是生活,生活本身。現代讀者生活不能容忍編造”。從汪曾祺對自己小說的幾句的評論中,我們得知汪曾祺對小說創作的獨特思想,就是本著生活的原貌寫,小說即是現實生活的真實反映,不靠自己編造來顯示生活,小說中社會風情和人物世界都與現實生活保持著相對的真實統一。汪曾祺在他文章中涉及到的地區以高郵、昆明、北京和張家口這四個地區為主,他對這四個地區進行了一個細致的民情畫的描寫,其中參入了大量的社會風情描寫,塑造了大量的人物,形成了一個小市民的世界。 正是基于汪曾祺這樣的追求,使我們讀他的小說感到十分貼近自己的人生經歷,沒有距離感,就像是自己身處在文中一樣。汪曾祺在小說中所描寫的人和事物都是取自于生活之中十分常見、日常的事物,他只是對這些事物,人物的心理狀態做了平常的記錄,將他們的日常生活做了簡單的搬運,把他們從生活中不動聲色的搬到了小說中。而汪曾祺說到他筆下的人物時曾經說他寫的“是小市民,我所熟悉的小市民”,這里就讓我們看一下他筆下的這些日常的小市民和小市民構成的平民世界。
在《跑警報》中,汪曾祺為我們描寫了一群為了躲避日本侵略者飛機轟炸的學生和市民。小說沒有描寫日軍轟炸的硝煙彌漫,敘述的是躲避轟炸過程中一群人上演著的各式生活。《雞鴨名家》中的余老五,在“炕蛋”期間,他兢兢業業,來不得一丁點馬虎,將自己的本職工作做好,確保雞蛋的孵化率。在完成“炕蛋”這一神圣的工作之后他就悠閑的多了,這時候他可以拿著茶壺到處溜達,聊天喝酒了。汪曾祺并不訴說余老五人怎么樣,只是將余老五的現實生活做展現,他的生活就是在“炕蛋”和悠閑之中轉換,年年如此。《異秉》中藥店里的管事和伙計們各司其職,各管其事,將藥店打理的有條有序,他們工作之余就是聚在一起閑聊,聊天聊地,享受著平常的生活。《戴車匠》中,戴車匠的工作就是做木制的工具家什,他沒有別的奢求,只一天到晚在自己的車床前辛勤的勞動,“他就和這張床子一體了,一刻不停的做起活來了”,這是戴車匠的日常的生活。《收字紙的老人》中,老白負責到各家去收集廢紙,把這些字紙背到文昌閣去燒掉,而這就是他的工作,而這種工作一干就是幾十年,最終在九十七歲無疾而終。《如意樓和得意樓》講訴了兩個茶樓的老板的故事,平實的敘述了兩個茶樓的日常經營活動,老板的精神狀態。 汪曾祺在他的作品中所描寫的這些平常人物和平常生活中恰恰體現出了一種平常心,一種順應自然的態度,體現著隨遇而安的生活態度,這正是佛家所講的“見性”之說,是這些人物找到了自我。仔細看一下汪曾祺筆下的人物,他們隨都是平常人,都是平民,但是他們具有了一種平常心,他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做著自己的本職的工作,達到了一種對于生活的平淡,這種平淡是一種隨遇而安的精神。前面講汪曾祺對佛教的接受的時候我已經提到,汪曾祺由于特定的原因養成了隨遇而安的哲學,他筆下的人物同樣具有這樣一種性格,平淡、順應自然、隨遇而安。這些人物過著平凡的生活,但是他們在這平凡的生活中找到樂趣,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即便是他們面對著人生的苦難和挫折,他們依然能夠隨遇而安,達到一種禪的樂趣,悠然自得,在平常簡單的生活中找到自我,解脫自己了。
參考文獻:
汪曾祺:《說短》,《汪曾祺全集》第三卷,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年版,第223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