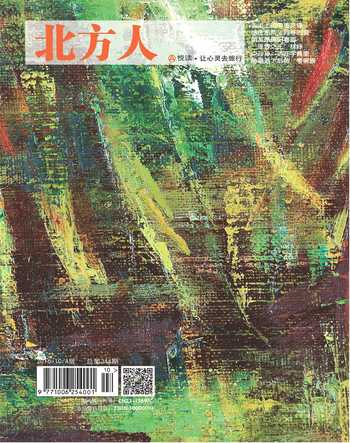陸谷孫:活在詞典里
潘真
在《英漢大詞典》的編者頁上,那些去世的編者名字都不加黑框。主編陸谷孫堅持,要讓每一個曾經的戰友都自由地“活”在這本詞典里。他說,這是大家的成果,也是逝者生命的延續。
而今,陸先生也遠行了。2016年7月28日,陸谷孫因病去世,享年76歲。
他是著名翻譯家、散文家、莎士比亞學者,首屆全國師德標兵、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貢獻獎獲得者。但他本人最在乎的,一個是《英漢大詞典》主編,一個是當選復旦“十大最受歡迎的教授”。他活在詞典里,活在學生的生命里。
陸谷孫1940年出生于上海,17歲時考上復旦大學外文系,碩士畢業后分配留校。“文革”初期,他被工宣隊發配去編詞典。在為上海“寫作組”翻譯東西時,他趁機涉獵各種原版資料,隨手摘錄新詞,偷偷編進詞典。1975年《新英漢詞典》面世,法新社、《紐約時報》《遠東經濟評論》等海外媒體注意到其中收錄了不少英語新詞語和新用法,“是一部跟上時代潮流的詞典”。
上世紀80年代中期,陸谷孫被任命為《英漢大詞典》主編,從此“不出國、不著書、不兼課”,一門心思做起“全職編輯”。1991年,《英漢大詞典》上下卷終于出齊。這是中國獨立研編的英漢詞典之最,收錄詞條20萬個,共5000頁,近2000萬字。在大詞典序言末尾,他寫道:“累土而不輟,丘山崇成。”樣稿最后還有他畫的“zzz”——終于可以放心睡覺了。
之后,他謝絕了編香港三聯版《英漢大詞典》的邀約,說要回歸教學和科研了。然而,安子介先生的一句話:“林語堂、梁實秋他們英漢、漢英都做過”,激發了陸谷孫更大的“野心”。1999年,他又領銜啟動了更大規模的《中華漢英大詞典》工程。陸谷孫說:“編詞典就像做廚子,受不了做飯做菜的熱氣,就不要輕易進詞典編纂的廚房。”這種勞心勞力的活,評職稱時卻不能算作成果,浮躁、逐利者避而遠之。他卻沉浸其中,三十個寒暑,烏發染霜。
自研二時,因系里缺教師,陸谷孫就教起了五年級畢業班。此后五十余年,他都“精細地備課”,一字一句批改作業,需警醒處畫上“大眼睛”,還寫長長的評語。寫論文的主要參考書,他先看一遍,劃出要點,做很多批注,以便研究生閱讀。即使成了名家,他仍把教書視為天職。
他當外文系主任,開出“白菜與國王”系列講座,遍邀海內外名家,開拓學生視野。有鑒于研究生水平急劇下降,他還堅持招人先看本科出身,對“海歸”也不放寬標準。學生出國請他寫推薦信,他必親自起草……
陸谷孫的研究生不足二十名,大多從事教育事業,喜歡讀書,每人都從導師那里學到一兩門看家本領。他說:“學生是我學術生命的延續。”
在所鉆研的各個領域,陸谷孫都出類拔萃。他研究莎士比亞,論文發表于劍橋大學出版的《莎士比亞概覽》,引起國際反響;出版《莎士比亞研究十講》。他寫散文,有《余墨集》《余墨二集》行世。他搞翻譯,出版與父親陸達成先生合譯的《星期一的故事》,還有《幼獅》《胡謅詩集》《一江流過水悠悠》等。
當年上海市市長朱镕基率團出訪,指名要陸谷孫當首席翻譯。當朱引用“群賢畢至,少長咸集”,他翻出了古漢語的韻味,還附注典出王羲之《蘭亭集序》。港督引用莎氏名句與朱攀談,他隨口將名句背下去,令港人驚艷。
陸谷孫提出的“學好外國語,做好中國人”,成為復旦外文學院的院訓。他作“留住中國文化的精神線索”演講,告誡學生:對弱小要有由衷的愛,對自由要有一種向往,對權力話語要有一種懷疑。警示學生干部:從小學會“官本位”,長大很可能當貪官。可是,有多少學生聽得進這種“不合時宜”的話呢?
他自己,不當掛名編委白拿稿費,不出席商業活動和榮譽頒獎禮,寧可幽居陋室,琢磨中英互譯的美妙。他處世的準則是,不幫閑,不人云亦云,不做“歌德派”“兩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