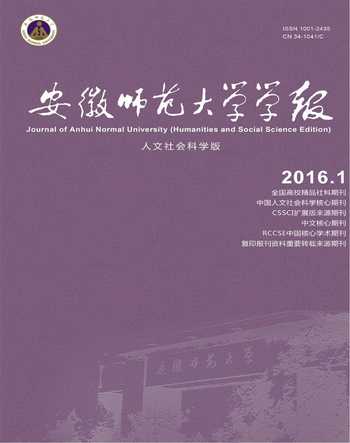鄉規民約的當代意蘊
鄭文寶等
關鍵詞: 鄉規;民約;鄉規→民約→鄉規
摘要: 倫理性、多民族和廣地域決定當代中國鄉規民約仍需存在。鄉規和民約二者不能混為一談,更不能簡單地將鄉規民約理解為單一的鄉規或民約。歷史上鄉規民約經歷了“鄉規→民約→鄉規”的變遷過程,社會形態變更期重鄉規、穩固期重民約,當代中國鄉規民約建設應以民約為主,當下學界盛行的“當代鄉規民約建設就是村民自治章程建設”的觀點并不完全正確。當代鄉規民約的存在并不是基于制度性的目的,而是為了實現倫理性的規范,必須摒棄道德思想樹立倫理理念、淡化道德的功利目的彰顯其本源性功能。
中圖分類號: D64;C912.8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 10012435(2016)01010507
鄉規民約作為社會治理方式之一,已經被寫進了黨的會議公報:“支持各類社會主體自我約束、自我管理,發揮市民公約、鄉規民約、行業規章、團體章程等社會規范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1]這是當今中國法治理念的真實寫照,更是學術意義上的一次巨大進步。鄉規民約最早是傳統社會的產物,具有醇化社會風氣、維護社會秩序、協調人際關系等作用,但是歷史上鄉規民約又往往被宗族勢力所把握,維護著封建族權,成為人們沉重的精神枷鎖。那么,國家又為何重提鄉規民約?并且將之寫入了黨的會議公報里,對于這一現象又做何理解?
一、鄉規民約何以可能
眾所周知,道德與法律自古以來都是國家治理之二柄,所謂“法治者,道德之顯爾;道德者,法制之隱爾”(《知言·修身》),內傾式的農耕生產方式決定了中國傳統社會在社會治理上采取以德主刑輔策略,即“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春秋繁露·精華》)。傳統社會以此理念為指導,經過數代精英努力,構建了一個十分完善的社會德治系統。這個德治系統包括道德觀念和道德規范兩個方面,道德觀念以仁、義、慈、勇、恕、廉、恥、謙等為代表,道德規范以神道設教、樂教、鄉規、民約、社約、族規、會約、家規等為代表。道德觀念作為精神指引,對人們信念進行感召,道德規范作為現實規則,對人們道德行為進行約束。鄉規民約屬于道德規范范疇,它的表現形式和作用發揮是與法比較相似的,都是一種制度性規定。
其實,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朝代都不缺少律例,秦律、唐律、大明律、大清律等都是著名法典。以大清律為例,四十卷、三十門,律例嚴密周詳,覆蓋了民眾的全部社會生活。那么為什么還需要鄉規民約這個非法的制度性規定呢?區別于宗教型社會和法理型社會,中國是個倫理型的國家,中國社會問題的解決和治理不能像西方社會那樣單純依靠法律,倫理道德(既包括倫理觀念又包括倫理規范)在中國有著西方社會所不可理解的重要作用,所以作為道德規范的鄉規民約在當代中國仍有生存的空間和存在的必要性。另外,中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作為規范社會秩序的法律根本無法顧及各個地域的實際情況和風俗習慣,法律只能作為一個對抗共識性錯誤舉動的標尺而存在,無法做到對抗各民族、各地區的差異性錯誤行為,而且又因為“法”是與“罪”對應的,它根本無法約束和制裁違反道德旨意卻沒有達到犯罪層面的行為。這些參差不齊的違反道德意旨卻未至罪的錯誤行為只能由鄉規民約等道德規范來約束。即,在全國統一的法的規范之下,面對各地不同的風俗習慣,各地還應該存有針對非罪錯誤行為的治理措施,鄉規民約便是這種地方性治理措施的主要表現形式。
概言之,雖然當代中國已經走出傳統社會進入到了信息時代,但是有兩個基本的事實沒有改變:中國依舊是一個倫理型的社會;中國的民族依舊眾多,風俗依舊迥異。這兩點恰恰是鄉規民約存在的前提條件,所以盡管歷史空間發生了轉變,但鄉規民約在當代中國的存在既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
既然鄉規民約的存在是必然的,那么它的存在是否真的就能夠起到實際作用?如果能夠發揮作用,究竟會在哪方面發揮作用?讀史可鑒今,鄉規民約的作用可以從歷史中管窺一斑。
鄉規民約具體起源于何時何地,已難詳考。目前可見的最早文本形式的鄉規民約則是北宋時期藍田《呂氏鄉約》,陜西藍田呂氏四兄弟“俱游于張(載)程(二程)之門”[2],均為當時著名的理學家,因此《呂氏鄉約》從“德業”“過失”“違約”“禮俗”“撫恤”等多個儒家生活視角對民眾行為進行了倫理規范,民國時期張驥考證后得出“關中風俗為之一變”(《關學宗傳》卷三)的結論,可見《呂氏鄉約》作用之大。除《呂氏鄉約》之外,后世較為著名的還有王守仁制定的《南贛鄉約》,以及后來先后出現的成為鄉規民約宣講重要內容的官方教化綱領的“圣諭六條”“圣諭十六條”“圣諭廣訓”等等——鄉規民約都已經上升到了“圣諭”層面,足可見鄉規民約教化地位之重要詳見陳時龍《圣諭的演繹:明代士大夫對太祖六諭的詮釋》,《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5年第5期。
。鄉規民約的這種強勢發展勁頭,直到19世紀末至“五四”期間,伴隨著“西學東漸”,在近代“道德革命”沖擊下,才開始逐漸弱化。但是在緊接著的20世紀20至30年代,在梁漱溟等人“倫理本位、職業分立”[3]思想指導下,河南、山東、廣東等地再次興起“鄉村建設運動”。雖然這次運動最后發展并未如人意,但是所有的這些都能夠說明,鄉規民約在歷史上于道德和社會秩序而言,曾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當社會發展至瓶頸之處時,精英們總是期望借助它克服重重困難。
換言之,鄉規民約的積極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了,但是需要明辨一件事情:無論是“關中風俗為之一變”的《呂氏鄉約》,還是《南贛鄉約》、“圣諭”系列以及后來的“鄉村建設運動”,都將規范對象指向了民眾的生活層面,重點是在規范民眾的道德生活,而不是經濟生活。即,鄉規民約建設的是道德秩序——當前國家將鄉規民約視為社會治理方式,其實是專門針對當下的道德亂象而言的。這一點意蘊極為悠遠,應該值得學人注意——國家是想通過鄉規民約的建設來規范、治理當前的道德亂象,鄉規民約是一種道德手段而不是經濟手段。
綜上所述,鄉規民約作為一種社會治理方式,特別是道德亂象的規范方式,有著價值合理性的一面,各個歷史時期都可以辯證地借鑒、運用。當下所言及鄉規民約并非是要復辟傳統鄉規民約的內容,特別是傳統鄉規民約的陳腐內容,而是要借鑒傳統社會運用鄉規民約進行道德建設的這種社會治理方式。
二、正確認知鄉規民約的內涵與發展
鄉規民約在當代中國是必然的也是可行的,但就目前現狀看,鄉規民約的建設內容和建設準則還不甚清晰。只有將這兩個問題解決,才能將鄉規民約的可能性轉變為現實性。
當代中國鄉規民約研究是伴隨著改革開放進行的,20世紀80年代隨著村民自治政策的出臺,鄉規民約研究也逐漸興起,并在90年代初具規模,延續至今。這些研究視角迥異,重點不同,取得了豐碩成果,為當代鄉規民約建設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但是仍有一些前提性、關鍵性的學理問題還沒有被認知清楚,以至于影響了當代鄉規民約的建設進程。即,鄉規民約在當代語境下的研究與建設仍有許多問題需要商榷。
(一)鄉規民約的內涵還需要進一步厘清,這樣才能準確把握當代鄉規民約的建設內容
鄉規民約就詞源視角分析,是“鄉規”和“民約”的組合體。“鄉規”說的是一種規定,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制度性“規定”,從制定到最后形成都有著嚴格的規范和程序,體現出強制性色彩;“民約”則是一鄉民眾共同制定并遵守的一種“約定”,雖然一旦形成也具有約束力,但它的制定過程卻是一個相對平等的“約定”過程,而不是自上而下的“規定”過程。
現在許多研究者將當代鄉規民約等同于村民自治章程,其實這是一種不嚴謹的觀點。村民自治章程絕對不等同于鄉規民約,它只是鄉規民約的一部分,是一種典型的“鄉規”,但不是“民約”。因為村民自治章程是根據《村民委員會自治法》,嚴格按著“自治法”規定的程序、步驟由“村委會”牽頭組織、制定,實質上是一種“規定”,而且這種“鄉規”內容也已經不再是傳統意義的道德內容:(1)本村享受誤工補貼的人員及補貼標準;(2)從村集體經濟所得收益的使用;(3)本村公益事業的興辦和籌資籌勞方案及建設承包方案;(4)土地承包經營方案;(5)村集體經濟項目的立項、承包方案;(6)宅基地的使用方案;(7)征地補償費的使用,分配方案;(8)以借貸、租賃或者其他方式處分村集體財產;(9)村民會議認為應當由村民會議討論決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項。[4]這是國家村委會組織法所規定的村民自治章程的具體內容,這九個方面重點關聯的是土地、經濟等利益要素,并無倫理風尚內容。這便是當今“鄉規”也就是村民自治章程的主要特點——在古代,“鄉規”“民約”都以鄉村道德內容為主;在當代,“鄉規”卻單一地指向了鄉村經濟問題。
可見,村民自治章程只能算是鄉規民約中的“鄉規”,并不是完整意義上的“鄉規民約”,而且村民自治章程專注于經濟問題并不關注道德風尚問題,不能也不是為了解決道德問題而出現的問題域,而國家當下提倡鄉規民約是為了解決道德問題的,因此這種“鄉規”雖與當前所言及的“鄉規民約”名稱相同,但本質卻大有不同。
當代針對道德問題出現的鄉規民約不是村民自治章程,也不是鄉規民約中的“鄉規”,而是典型意義上的“民約”。貴州開陽縣清河區禾豐鄉水頭寨寨頭豎有布依族“民約”石碑,內容涉及睦鄰鄉里、尊老愛幼、美化環境等諸多方面,細致到修墳造林、偷盜懲戒、牛馬放牧、菜園種植等生活細節。[5]這種“約定”內容沒有涉及土地、租賃等經濟要素,更不像“章程”那樣具有制度性質的強制力,也不具有傳統鄉規民約宗法勢力的淫威這里有必要澄清一下民約與族規的區別,族規是一種規定,更加側重于宗族勢力的介入,具有一定的強制性,而一般性民約卻更加側重平等性、民主性,遠離強制性。當然,族規是一種較為特殊的民約形態,但是在當今社會,族規已經不可能復存。
,它不是強制約束,而是一種道德感召或是一種理念的倡導,是所有村民的道德愿望所歸和希望所在,出發點和歸宿點既不是國家層面也不是階級層面,而是世俗層面,甚至可能會出現一些非理性的要素如水頭寨布依族的鄉約中就頻頻出現“人神怨恕俱不得善終”“若昧天良白骨現天”等非理性字樣,黔東南有偷竊鄰里雞鴨者需宴請全村之非理性規定,云南民約石刻中也有盜伐樹木需賠以百斤酒米之非理性規定。
,但是對于凈化風俗、美化生態等“非經濟”“非利益”方面卻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概言之,“鄉規民約”是“鄉規”和“民約”的組合體,但是“鄉規民約”所包含的“鄉規”和“民約”卻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鄉規”主要體現統治意志,本質上是一種“規定”,是理性的;“民約”卻主要體現民眾愿望,本質上是一種“約定”,是世俗的。像《呂氏鄉約》就是純正意義上的“民約”,由呂氏兄弟帶領一方民眾自行“約定”而成,《南贛鄉約》和“圣諭”系列均由統治階級代言者站在政治統治立場上“制定”,都是政治御用色彩極濃的自上而下的“鄉規”,并非是純正意義上的“民約”。或許受此影響,研究者們在面對鄉規民約時存在著一個矛盾現象:在思想上認定鄉規民約的“民約”性質,在建設方法上卻肯定“鄉規”的做法。即,思想認知上認為鄉規民約應該是一種“約定”,“所謂鄉規民約,乃是民間自愿組織制定的道德公約、互助公約。”[2]但是在建設鄉規民約之時卻認為鄉規民約是一種“鄉規”,只談“鄉規”建設鮮有“民約”內容在當代鄉規民約研究中,張明新、張洪波等人多次發表見解,認為當代鄉規民約的表現形式和內容為村民自治章程或者是習慣法,其實無論是村民自治章程還是習慣法都是一種規定,是典型的“鄉規”而不是“民約”。
,而且“鄉規”建設的主體內容也偏離了道德路向,旨在規范鄉村的經濟事宜,不再是道德領域的范疇了。
鄉規民約研究者將歷史上所出現的“鄉規”和“民約”統稱為“鄉規民約”,并沒有進行嚴格的區分,而且似乎也沒有必要進行區分,但是在本文視域下,在當代鄉規民約建設目的論論閾中,這種界分就有了必要性,因為概念和理解不同就會直接導致建設重點和內容的不同,這是當代鄉規民約進行正確建設的前提。國家并不是在經濟視域中重提鄉規民約的,而是在道德視域中重新啟用鄉規民約這一倫理學范疇的,重提鄉規民約的目的是要借鑒鄉規民約這種道德建設方式對當代道德亂象進行規范和治理,進行道德建設。因此,雖不能否定作為特殊“鄉規”的村民自治章程聚焦于經濟要素的正當性,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這種“鄉規”內容并不是當下國家所提倡的“鄉規民約”的道德取向,也就不能將當下“鄉規民約”建設簡單的等同于村民自治章程建設了,二者之間有交集但并不等同,這是當代鄉規民約研究需要注意的一個關鍵問題。
眾所周知,改革開放以來道德建設乏力一直是個不爭的話題,究其原因十分復雜,但就本文論域而言則是因為存在了太多的自上而下的“規定”,卻缺乏一種民眾自發的道德“約定”。就道德建設而言,經過多年的建章立制,相對而言我們并不是特別缺乏“章程”式的道德條例,被“制定”、“規定”出來的道德口號、道德條例比比皆是,只是源自民眾內心的禮俗“約定”卻寥寥無幾。現實生活中人們的迷茫彷徨,并不是因為缺少理性條例式的“章程”依據,而是民眾內心生活化的情感無處寄存、無處表達,道德情感無處寄托、無處表達自然就會直接導致諸多道德亂象的出現,當代道德建設乏力、道德建設效果不佳的原因也就在于此。而“民約”由民眾約定而成,較“鄉規”更能體現一方民眾的情感、愛好、喜惡,換言之就是更能直接體現一方民眾的道德訴求。因此,在正確區分“鄉規”和“民約”之后,就當代鄉規民約建設而言,便可知曉當代缺少的不是“鄉規”,而是“民約”。建設能夠寄托、表達人們情感的“民約”而不是“鄉規”,是當代鄉規民約建設的重中之重,只有這樣當代鄉規民約的道德規范功能方有可能。
(二)鄉規民約發展背景還需進一步厘清,這樣才能正確理解當代鄉規民約的建設準則
我國目前可見的最早文本形式的鄉規民約為《呂氏鄉約》,但是這并不代表著之前就沒有“鄉約”的實體形式和內容存在。中國千年鄉規民約的變遷歷程實質上經歷了“鄉規→民約→鄉規”的變遷軌跡。“據考察,鄉約淵源于周禮的讀法之典。”[6]西周對鄉村如此規范:“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赒;五州為鄉,使之相賓。”(《周禮·地官》)這其中的“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赒”“相賓”便是典型的“鄉規”,只是沒有以“鄉規”或者“民約”的名稱命名而已,但其已實際存在。秦則將由來已久的鄉里制度進一步升級為鄉、亭、里三級制,并明確“三老掌教化,嗇夫掌訴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漢書·百官公卿表》),“教化”“禁賊盜”等職能描述便說明當時政府除了重視鄉村經濟問題之外,更有專門人員負責鄉村的風俗建設。即,這些文獻資料足可以證明,漢前的鄉規民約形式上雖不叫做鄉規,卻實際存在,而且是在官方嚴格控制下運作的,因此此時鄉規民約的重點是自上而下的“鄉規”,而不是平等約定的“民約”。
這種狀況及漢時出現了變化,“秦漢以降,直至明清,封建國家一直在基層社會實行一定程度的鄉村自治,在保證賦役的征收和地方的安靖之外,絕少干預民間的生活秩序。”[7]“各種民間的組織和團體,在政府之外獨立地發展起來,它們形成自己的組織,追求自己的目標,制訂自己的規章,以自己的方式約束和管理自己。”[8]也就是說這一階段官方對鄉規民約的管控不是很苛刻,真正意義上的“民約”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例如河南偃師出土的石刻《漢侍廷里父老們 (亻單)買田約束石券》,實際上就是名為“‘父老亻單的非官方組織訂立的一份協議”[9],這是典型的“民約”而不是“鄉規”,也就是說這一時期(漢至明)的鄉規民約重點是“民約”。
但是明洪武三十年(1398)“圣訓六諭”出現之后,開始強調所有“民約”必須在朝廷“圣諭”指導之下進行,鄉規民約又逐步向最初的“鄉規”形式回歸,明成祖朱棣更是首次以國法形式頒布鄉規條例,“民約”徹底演變為“鄉規”,“到了明朝中后期,鄉約已經由宋朝基層民眾自發的教化組織演變為官方倡導的,集教化、軍事、管理為一體的基層組織。”[10]這一趨勢在清朝時期達到巔峰,“圣諭十六條”“圣諭廣訓”等綱領性文件是清朝鄉規民約必須統一的模板和內容,鄉規民約中再無“民約”,只剩“鄉規”。
由上可知,中國歷史上鄉規民約的演繹變遷是經歷了“鄉規(漢前)→民約(漢至明)→鄉規(明清)”三個階段的,這并不是一種偶然現象,這種表象變化背后是有著深刻的內在邏輯線索的:“社會形態”動蕩期重鄉規,“社會形態”穩定期則重民約。
漢之前和明之后的鄉規民約實質上之所以都是“鄉規”,是因為這兩個階段是中國社會形態的變動、整合期。漢之前雖有秦皇一統天下,但實際上中華民族大一統局面并未出現,穩固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也并未形成,社會或處于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型階段或處于封建社會最初的形成階段,社會形態并沒有固化;明之后中國社會已經開始逐步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社會發展再次具有了突破舊有樊籠的潛質,社會形態開始不再固化。這種社會內在的動態變化如果調控不當勢必會造成社會外在體系的混亂,所以在鄉村治理方面這兩個階段都需要官方的直接“把脈”和指導,就鄉規民約而言就直接表現為側重“鄉規”建設而不是“民約”建設。而漢后明前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則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并成熟階段,雖然朝代更迭、戰亂不斷,但人們爭奪、更迭的是政權,封建性質的社會文化和社會心理相對穩定,封建社會基本形態也十分穩固,所以現實生活中體現社會心理文化的鄉規民約,即便不用刻意疏導也不會出現悖亂,所以這一階段的“民約”便遠遠多于“鄉規”。
由此可見,“‘社會形態動蕩期重鄉規,‘社會形態穩定期重民約”是道德視域下鄉規民約建設的基本規律。當前中國也正處于社會轉型的關鍵期,傳統社會從形式到內容、從器物到文化正在經歷著全面解構,現代社會同時也處于全面的建構過程中,這也是一次非常標準的社會體系全方位的大變革。但是這種變革是社會主義體系內部的結構變革,社會心理和社會文化仍隸屬于社會主義體系框架,雖然社會處于轉型期,但是社會形態、社會結構依舊穩固,是社會主義這一穩固社會形態之下的變革,所以在鄉規民約建設方面不能像漢前和明清那樣過于極端,仍然要以“民約”為主。至此,我們可以確定這樣的一個結論:十八屆四中全會言及的鄉規民約建設實質上是在強調民約建設,目的是希望通過民約建設來實現社會道德風尚的改善,并不是希望通過鄉規民約建設來補充完善法律制度或經濟建設。基于這樣特殊的出發點,可以認定十八屆四中全會所強調的鄉規民約建設,并不是學界普遍認為的“鄉規民約建設就是村民自治章程建設”或習慣法法規建設張明新撰文《從鄉規民約到村民自治章程——鄉規民約的嬗變》,認為“村民自治章程是鄉規民約的當代表現形式”(《江蘇社會科學》2006年第4期);張洪波撰文《鄉規民約與新農村的法治建設》,認為當代鄉規民約已經轉化為了習慣法(《長白學刊》2009年第1期)。筆者認為此觀點有待進一步商榷,因為村民自治章程屬于“鄉規”,并不是“民約”,因此只能說“村民自治章程是‘鄉規的當代表現形式”,不能說成“村民自治章程是‘鄉規民約的當代表現形式”。,而是村俗民規建設。
三、有效規避鄉規民約的建設誤區
如上述,當今言及的鄉規民約建設,實質上是個道德建設問題,是針對當代道德建設乏力提出的一種道德建設新思路:通過鄉規民約建設來純化風俗,凈化社會道德。這是我國當代道德建設的一個重大變革,以往在進行道德建設時往往都強調高、大、上,卻遠離百姓的日常生活,因此往往具有空中樓閣效應,卻不具有現實的道德約束作用。強調“民約”建設實際上就是將道德建設方式和手段做了調整,將“民約”這個非高大上的道德內容和方式作為社會道德風尚建設的突破口,這一道德治理思路與以往存在著差別,因此在建設路徑上也應與以往有所區別。
(一)摒棄道德思想,樹立倫理意識
在本質上而言,道德與倫理是不同的:“倫理與道德雖有共性、交集但卻不可等同視之,道德是社會發展過程中‘有意識形成的意識形態體系,是可以通過外力帶有目的性的培養和塑造的,體現出明顯的階級性和歷史性,而倫理則是原生態的‘自發產物,它的形成和發展雖受外在因素影響,但更多的是在體現人性,不具備階級性和目的性,而且受外力和時空影響較小,是人們在生活過程中形成的自然意識系統。”[11]也就是說道德具有工具意識,而倫理只是人們生活的原始樣本展示,這種原生態的存在樣本是不能用理性來解讀和規范的。比如父子之親的倫理事實是不能用理性思維來解讀的,它就是一種客觀的血緣倫理親情,但是助人為樂的社會公德卻是可以用理性思維解讀的,它是一種秩序需求卻不是天然倫理。
民約是一種協商公約,它的服務范圍很小眾化,甚至會有些非理性的內容,也就是說“民約”來自于人們內心中沒有經過加工和處理的自發層面的倫理內容,并不是來自于外在的自覺層面道德內容。民約是一方民眾根據自己的情感、愛好、喜惡,制定的約束自己道德行為的制度性規范,這種道德規范制定過程和建設方式或許會導致“民約”些許內容不符合所謂的邏輯判斷和理論考量其實歷史上鄉規民約的制定能夠像《呂氏鄉約》那樣純粹由民眾制定的還是比較少見的,大多數鄉規民約的制定并沒有遠離鄉里組織的參與和監督,但是這并不等于說鄉規民約就是由政府組織制定、規定的,鄉里只是監督以防鄉規民約違背國家大義,并不干涉具體內容,具體內容由會社、宗族等民眾組織自行制定。
,但是不要忘記的是“民約”本身就是針對風俗習慣而定的,風俗習慣又怎能用理性去判斷和衡量。“民約”只是一種小眾化的倫理習慣規定,并不是國家層面的道德意識判斷,即“民約”內容在法的宏觀框架之下可以不存在著理論上的對錯之分,只存在著當地民眾的認可與否問題,當然前提是不能突破法的規范。
換言之,鄉規民約建設不能一刀切,要本著從鄉村倫理實際出發的原則,真正體現民俗和倫理的多樣性,體現“因地制宜”的正確方法論視角,不能從國家層面統一的道德意識角度來規范,需要給鄉規民約留出“自留地”和生存空間,只有這樣各地才能制定出真實有效的鄉規民約規范,鄉規民約才能在社會風尚建設中發揮實際作用。
(二)淡化道德功利目的、突出本源功能
鄉規民約是作為道德建設手段在本文論域中出現的,這樣就不能不談及道德。道德是什么?關于道德的界定,從不同視角會有不同的答案,但是無論如何界定都不得不承認道德是衡量人們行為對錯或者善惡的一個準則。也正是如此,道德往往被賦予了社會控制的功能:用道德來規范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借以維護和鞏固社會秩序。這種理解當然無可厚非,這也是“道德建制”說法的依據和來源,但問題是道德還有著其他的更為重要的作用——使人成為人,賦予人生以意義。“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圣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12]人與動物的區別便是在于人擁有“親”“義”“信”等社會性的倫理道德,而且“幸福是靈魂的一種合于完滿德性的實現活動” [13]。只有擁有了德性人才能稱之為人,人生也才能有意義,這是道德的本質性訴求和功能,較其社會控制功能更為根本。換言之,道德的本源性功能在于塑造人性,控制功能只是其外延性、輔助性功能,這要求我們在審視道德時必須超越功利層面去考量,專注本源性功能之后附屬功能自然就會彰顯無疑,所謂的“無為無不為”[14],“無為”才能到達“無不為”的目的,如果舍本取末,只是專注于道德控制功能建設,則恰恰是道德失效的開始。即,鄉規民約建設雖是道德的工具性、目的化建設,但是要取得真正的實效,必須將建設重點放在本源性功能建設上,不能一味的追求道德社會控制功能的建設。
概言之,鄉規民約本身就是一種關乎道德的制度,表面上似乎直接體現了“道德建制”,其實卻不然。鄉規民約體現的是倫理,是一種不能用理性思維衡量的情感尺度——鄉規民約的確是一種制度,也的確是在規范人們的行為,但它不是單一規范性質的制度,甚至不是一種理性思考范式之下的制度,它只是一種倫理制度,而不是道德制度,這個制度與道德的本源性功能一一對應,體現的是鄉村的“人倫要求”和“幸福德性”而不是某種功利,因此它雖然是制度卻不是“道德建制”所說的制度。在進行鄉規民約建設時,不要將鄉規民約建設定格在功利視角上,為了規范制度而制定鄉規民約,通過最為樸素的鄰里協商約定自然就會達成“無為無不為”[14]的功利效果。
當然,畢竟當今社會處于轉型期,鄉規民約建設不能任其隨意發展,必須給予一定規范和方向指引。區別于傳統社會的人治狀況,當代社會提倡的是法治精神,對當代鄉規民約的方向性引導和政治把脈自然也就是社會主義的法制了。鄉規民約特別是“民約”,由于具有倫理性、自治性特點,很容易在婚喪嫁娶、財產繼承、鄰里糾紛等方面受傳統民俗、習慣、世風影響,與以理性狀態展現出來的法律有所沖突,這時必須遵從法制,“民約”建設必須在社會主義法治精神的指引之下進行,受到社會主義法制的約束。但是法畢竟是與罪相對應的,對于那些非罪卻又不道德的行為只能由“鄉規民約”們來規范了,因此法的空間下還必須有“鄉規民約”的存在空間,即為真正踐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會主義社會核心價值觀,一方面“民約”不能違背社會主義法治,以體現“公正、法治”,同時國家相關職能部門也只能干預“鄉規”,不可左右“民約”,以體現“自由、平等”。
綜上,當今所言及的鄉規民約,更加側重的是強調“民約”建設,通過完善、豐富各地正當的“民約”,來解決各地生活上的差異性問題,借以達到醇化風俗、保護生態、促進社會和諧的目的。當然,從黨的十八屆四中全公告的文本表述中還能看到,鄉規民約是與“市民公約、行業規章、團體章程”并列表述的,這既是鄉規民約地位上的一種表征,也是對鄉規民約內容上的一種要求,要求今天所建設的鄉規民約必須是一種現代性的鄉規民約,與現代性的“市民公約、行業規章、團體章程”能夠完全匹配,從而成為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有力補充。
參考文獻:
[1]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十八屆四中全會公報全文[EB/OL].(2014-10-24)[2015-01-12].http:∥ www.js.xinhuanet.com/2014-10/24/c_1112969836_3.htm.
[2]張錫勤.中國傳統道德舉要[M].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09:322.
[3]梁漱溟.梁漱溟全集(二)[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168.
[4]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二十七條[EB/OL].(2010-10-28)[2015-01-12].http:∥ www.gov.cn/flfg/2010-10/28/content_1732986.htm.
[5]朱文運.水布寨布依族的鄉規民約[J].貴州民族研究,1988,(3):152-154.
[6]張中秋.鄉約的諸屬性及其文化原理認識[J].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科版,2004,(5):51.
[7]董建輝.“鄉約”不等于“鄉規民約”[J].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2):53.
[8]梁治平.清代習慣法:社會與國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28.
[9]寧可.關于《漢侍廷里父老們(亻單)買田約束石券》[J].文物,1982(12):21-27.
[10]吳曉玲,張揚.論鄉規民約的發展及其演變[J].廣西社會科學,2012,(8):77.
[11]鄭文寶.和諧社會倫理支撐的現實性考量[J].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3):388.
[12]趙岐,等.孟子注疏[M]∥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146.
[13]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M].廖申白,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32.
[14]朱謙之.老子校譯[M].新編諸子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00:146.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Local Rules-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Conscious Thought and Reality Problem
ZHENG WenBao1,JIANG DanDan2
(1.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partment,Heilongjiang engineering college ,Harbin 150050;2.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partment,Suihua college ,Suihua Heilongjaing,152061,China)
Key words: rule;local;rule→local→rule
Abstract: Rural construction with local rules is need today because of ethic society, multiethnic, wide geographical different customs, but it is not mean to simple restor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local rules, only to draw lessons from traditional society of rural construction with local rules this way,to governance and moral chaos. Local rules essentially contains the “provisions” and “convention” two meanings, not a single understanding it as a “rules”, or a single interpreted as “local”. Analyzes the focus of local rules in the history of experienced “rule→local→rule”, social form change period “ rules ” is importment, consolidation is “ local ”. With the corresponding, we should give priority to with “ convention ”, rather than the “ provisions ”, “Local rules is the construction of villagers autonomy charter” point of view is not entirely correct. The present local rules is not based on “institutional” purpose, instead of the “ethical” specification. Therefore, the way one should abandon the idea of “morality” sets up the concept of “ethics”, the other is to should downplay the moral utility function.
責任編輯:楊柏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