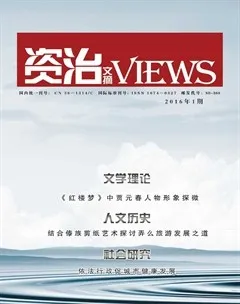論書法形式與文字內容的疏離與關聯
肖壽林
【摘要】書法作品的筆墨形式關聯著所書寫的文字內容,文字內容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書法的筆墨形式,但筆墨形式和文字內容的疏離又決定著書法筆墨形式的深度。本文通過對二者關系的闡釋來解讀書法藝術的審美精神。
【關鍵詞】書法形式;文字與文章;疏離與關聯
書法作品以筆墨線條構成的文字形態呈現出來,書寫形式與書寫的文字內容天生有著一種疏離與關聯的關系,對書與文的探討,是書法研究繞不開的話題。“文”可以有三個層面的理解:第一個層面是紋飾的紋,就是書法它本身也是一種線條的藝術形式,紋路也是書法藝術核心;第二個層面是文字之文,即書法它本身是依托于漢字的,與文字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第三個我認為是文章之文,書法作品通常都以文章的形式呈現,無論是書信、便條,還是詩作、散文都是文章的形式之一種。
文是一種紋樣,是一種紋飾。孔子是這樣說“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說文解字中文為“三丿”(三撇),意思是豹子身上的花紋。文就是裝飾,質就是本來的樣子,最簡潔的那個樣子,所以他說“文質彬彬,然后君子”,奠定了中國的審美傳統。但過分的紋飾就離開了本質。史就是人寫的文章;質勝文則野,一點修飾都沒有,沒有人文的東西,人文即經過人的加工之后產生的東西。沒有人文,就是原生態,自然的本來樣子。書法必須寫漢字,最初被定為一種書寫漢字的方法,后來為書寫具有特殊美感的漢字的方法,有漢字還要有對漢字的人文的修飾,才是書法之文。書法是范本學習,不可能直接從自然界或借助外物直接觀看而得來。
如果我們參觀中國畫和油畫的展覽,在想象中我們會書法應該更平靜,但事實上中國畫與油畫相比書法會給人很平靜感覺的,油畫的指向性更明確,也更平靜。當每個書家都想表現一種自我的風格時,書法反而給人很亂的感覺。
這是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按理來說書法是指向人的,最平靜的那一塊的,好像更有文人色彩,必然書寫文字,而無法和外界的自然與文字之變的紋區分。自然界的那種平靜,那種對生命的直接的體玩,可能更強烈指向人的視覺,直接就達到你所感受的,馬上勾起你平時對自然的記憶。油畫很多是具有寫實主義的作品,而不是純抽象的當代主義油畫。或者是其他中國畫也好,不管用符號,色彩還是筆墨,他都是指向于外物,那個外物勾起人對自然的生命狀態的回憶,人想到自然安靜,心情平靜。書法不一樣,書法本身是被人文化的,文字本身是人創造的,同時文字本身是一種紋飾,一種模仿自然與表示事件情感的符號。
一個象形的東西變成了文字,成為了被人為的紋飾過的。但是他帶來一個的問題:漢語是表意系統,其實書法作品的表意是非常模糊的,不知道指向哪里,沒有敞開,沒有指向,沒有暗示,而是純粹的線條。這是我的觀感,不知道這個理解是否準確。如果書法沒有經過個人沉淀,只是通過一種形式表達出來,那么它就會產生表意的模糊性。
書法本來成為一種形式,我們可以結合這兩個問題下去更深入的研究。漢字的表意性,意在哪里?表達人與自然,人與人的溝通,對事物的概念,看到文字能直觀達到的物象,直接達到溝通的目的,直接指向他背后的內涵和外延,他的能指所指是什么,都能達到他直觀的滿足,但書法變成了一種文字書寫形式,文字再重新被紋飾過,第一層是對外物的紋飾,變成一種符號;第二層是通過書法再對文字紋飾,他有兩層紋飾,實際上書法幾經脫離開了表象的直接的文字,他又向外物回歸。我今天早晨想到一篇文章就叫《自然的聲音》,讀書只能讀到知識,而寫文章是自我感受;他說寫什么呢?我說很簡單,寫你身邊所有你看見的事物,這事物是什么呢,可能就是你路邊的的一棵草,背后池塘的水,用詩意化的語言寫花是怎么開的,水是怎么流的。這些流和開都是在你身邊自然的綻放,自然的展開,那么人只有這樣對外物生命觀照,對時空觀照,你才能感受到生命的流逝,你才感受到生命的價值。同樣的,我們在書法上,你才感受到你下筆的那種形式,指向性是在哪里。差了這個時代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東西。比如今天我們花了一個小時,最重要的是我們那么一幫人愿意花這一個小時甚至兩個小時坐在這特殊的地方而度過我們這兩個小時的生命,這樣的一個歷程,這就是我們這個過程可能比我們的結果更重要,過程可能比內容更重要,它才是真正生命流逝的狀態。幾個人面對面談論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是什么有時候并不重要,我想魏晉人的那種風度,那種乘興而去,興盡而返的過程尤為重要。說了那么多,可能有點脫離原來的話題了。
但是,實際上文字最后到文章的時候,必然要接觸到這樣的問題,也就是文字的文是兩層紋飾然后產生的書法藝術形式,這樣的藝術形式一定反過來指向生命,又回歸到自然物象當中,那么才有了書論中的“萬歲枯藤,千里陣云”等意象。但現在的情況是,這個文字很難讓我們再回歸到自然。
但是它跟那個自然不同,第一個自然表達出來的是象形;第二個自然是一種感受,一種心理印象,它這里面產生了一種差距,經再度轉換以后得出的東西不一樣了,而書與文的這種關聯與疏離正好構成了書法審美精神的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