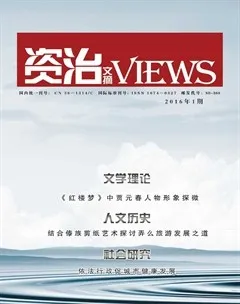淺談數字時代傳統出版社的盈利模式
李鵬
傳統出版單位是通過支付作者一定的稿酬,將其作品通過合法的渠道進行市場推廣和銷售,以此盈利。但隨著計算機技術的升級、智能手機的普及、用戶閱讀習慣的變化,我國出版行業也正經歷著從傳統行業向數字化轉型的過程。在這個轉型期中,出版社目前的盈利模式可以分為傳統和數字兩種。本文將對傳統盈利模式進行簡要介紹,并側重于介紹數字盈利模式。
一、傳統盈利模式
過去,出版社的主要產品就是紙質圖書或少許附帶光盤。圖書出版后,通過新華書店等各類實體書店,以批發、零售的形式進行銷售。每年定期參加全國各大類型的圖書訂貨會、圖書館配會等,攜帶圖書書目、樣書展品在各大展會、賣場設立展位,在特定的時間、特定的區域,對本版圖書進行有針對性、集中性的推銷。曾經輝煌、卓有成效的傳統訂貨會隨著這幾年互聯網、數字出版的飛速發展已逐漸黯淡,成交量大不如從前。雖然現在的訂貨會更具象征意義,其銷售功能被弱化,更多的是在發揮品牌宣傳、行業交流的作用。
二、數字盈利模式
隨著數字出版時代的來臨,傳統盈利模式的很多方面都發生了改變,有的改變是重構,有的改變是顛覆的。主要表現在:1.內容形式的變化。過去,我們作為傳統出版企業一直說內容為王,但現在內容已經逐漸向著實時化、視覺化轉變;2.讀者群體的變化。身為網絡原住民的90后和00后正在取代身為網絡移民的70后和80后成為消費主體;3.圖書產品的變化。圖書已不限于紙質形式存在,正向流媒體等衍生產品快速發展。比如有聲讀物、電子書、增項現實、虛擬現實等產品,實現了圖文到富媒體、2D到3D的過渡;4.銷售渠道的變化。從傳統的下線實體店,到線上的電商平臺;5.數字出版中出現的專業出版、教育出版、大眾出版等細分市場。
可以說,數字出版中的每一個細分領域的盈利模式都不盡相同。比如,專業出版由于內容“獨家”優勢,而且有效結合各種行業考試和用戶“剛性”需求,因此能夠建立“內容盈利”模式,迅速實現數字轉型;教育出版必須與技術商深度融合,一手抓學校數字產品市場布局,一手抓教育政府資源行政支持,在教育信息化新秩序建立過程中構建可行的盈利模式;大眾出版的盈利模式是有效“盤活”能被市場消費的“存量資源”及深度開發“增量資源”,通過內容的關聯、整理、挖掘等工作開發出符合用戶需求的產品和服務。
據權威機構統計,2015年我國數字出版收入突破3300億元,并且繼續保持強勁增長勢頭,但對整個傳統出版業來說,數字出版盈利模式仍然是一個需要不斷探討的大問題,各出版企業在如何實現數字出版盈利,都正經歷著不斷摸索、不斷嘗試、不斷前進的過程。本文從資金來源分為兩個方面介紹一下目前數字出版方面的主要盈利模式。
一是通過“外在輸血”探索的盈利模式,也就是通過大項目帶動數字化營銷體系的建設。近年來,國家各級政府部門不斷加大文化產業支持力度,拿出大量專項資金對傳統出版業進行數字轉型的流程再造、數字印刷、平臺建設等多個領域予以支持。如何抓住并把握好大項目的機會是企業今后數字化轉型能否成功,能否盈利的關鍵所在。我社通過承擔國家、省部級大項目,獲得了千萬級資金的支持,通過大項目帶動了自身數字化轉型,引進人才,鍛煉隊伍,以此實現找到用戶、滿足需求、提供服務,借助大項目推進適合自身發展切實可行的數字盈利途徑,這包括了對用戶的數據分析、內容服務、精準投放、收益來源等的探索和嘗試。
二是通過“自身造血”探索的盈利模式。這是一種通過自籌資金,找準自身定位,建立引導用戶消費的服務盈利模式。每家出版社應以其最擅長的專業出版領域為主戰場,通過其傳統優勢圖書在全國出版領域占有的重要地位,相繼推出配套衍生產品,如今年來火爆的VR、AR、數據庫、在線教育、電子書、有聲讀物等。有了好產品,還需要好渠道。出版社應投入資金打造基于互聯網、移動互聯網渠道的數字營銷體系。比如,在互聯網方面,應借助當當、亞馬遜、京東等大型電商平臺,或者自建門戶商務網站進行自營產品營銷;在移動互聯網方面,應建立微信、微博、APP、WAP商城等,采取線上線下相結合的立體式營銷。
近年來,隨著文化產業的快速發展,人民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精神層次的消費需求也不斷增長。未來將是文化消費的時代,傳統出版和數字出版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共存。出版社應在現有盈利模式的基礎上,主動借助新媒體技術,通過搭建平臺進行精準投送,借助多元渠道、提供文化產品融合服務等營銷策略,建立用戶至上、內容為本、產品為體、服務為王的營銷體系,形成以傳統出版主導的數字出版業務主線,以及多形式、多渠道發布的品牌產品。為用戶提供高質量的產品,以及可靠的、長期穩定的服務作為保障,最終實現具有出版社自身特色的數字化盈利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