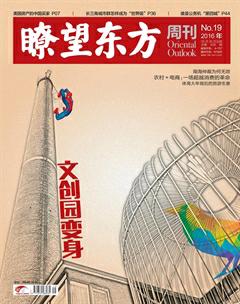“荒野”匠人
蔡瑜盛++楊卓琦
以25年的工作年限計,一個皮雕師一生的產量不到2000件
從表面看,李榮宗的手工坊一派繁榮。這個名為“酷貓”的皮雕作坊成立于2016年初,在四月天迎來了它生意的第一春。
“我的那間房被‘征用了。”李榮宗對本刊記者說,他的眼神越過因人流而顯得促狹的店面。
手工坊草創之時,李榮宗的想法是“前店后廠”:四分之三的面積給顧客,或欣賞皮雕,或體驗手工,剩下的面積留給自己“敲敲打打”。但在試運營的三個月里,登門拜師的學員絡繹不絕。僅本刊記者在店里采訪的短短時間里,就有兩名顧客要求“見一見李老師”。其中有一名不會中文的澳大利亞男子,想應征為手工坊店員,學習皮雕工藝。
然而,這家手工坊卻是以一個與手工無甚關系的名字注冊成立的:上海唐奇皮具有限公司。
“我找不到‘皮雕的選項,只能把它掛靠在‘皮具的類目下。”李榮宗說。
名不正的結果是,皮雕工藝無法借個人以外的平臺進行推廣。李榮宗舉了策展的例子。“辦一個活動需要申報(進而審核),而我的手藝,連名字都沒有,更別說審核了。”他至今未獲準過獨立辦展的機會。
李榮宗所經受的,是新生領域匠人生態的一個側面。在這個生態里,見木不見林的荒野地帶并不鮮見。
一次豪賭
“皮雕由日本引進臺灣,后傳入大陸,這個過程就發生在30年之內。”某品牌設計師、皮雕師王嘉慶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他的同齡人、現在天津從事皮雕教學的李曉漫認為,皮雕沒有形成一個穩定的氣候,只是這兩年剛剛起來。“國內的市場并不是很成熟,國內沒有評獎,沒有機構,沒有類似比賽。”
為此,在向職業皮雕師李曉漫求學的人當中,很多被他打消了積極性。
“很多人是想用這個賺錢的,但是我很明確地告訴他們并不是那么容易。如果能接受皮雕作為一個純愛好,去投入很多錢和時間,那再來找我學。”李曉漫說。他從事皮雕業近5年,僅工具和皮材的花費就已過10萬元人民幣。
這也是李榮宗在回憶過去30年時,將皮雕比作“豪賭”的原因。
1984年,17歲的李榮宗就讀于臺灣長榮中學美工科。“老爸是木匠,(他讓我)去學美工是為了學室內設計,出來和他做木工。”
那時的他時常溜去做皮雕的班上,看皮材是如何歷經拓圖、刀線設計,再到雕刻、繪色等工序。在木工家庭出身的少年看來,這些程序遙不可及。
皮雕的耗材遠非木料所能比。李榮宗只能向皮雕班上的同學要廢料,照著碎皮依樣畫葫蘆。
李榮宗來大陸推廣皮雕時,正值王嘉慶的畢業皮雕作品《穿幫》參加中國美術學院80周年畢業展之時。皮雕對于這個年輕人而言,是幸和不幸。
彼時的王嘉慶,就讀于中國美術學院城市雕塑專業。大二那年,女朋友發給他一組皮雕作品圖。
“當天,我就找各種中外網站買了一堆工具和教材。”王嘉慶說。
他告訴本刊記者,他的母校中國美術學院至今沒有開設針對皮雕的課程。整個大學生涯,王嘉慶是班里出勤最低的,他窩在宿舍,沒日沒夜地做一件皮雕作品。這最終成了他的畢業作品《穿幫》——一款浮于手包之上的槍形雕塑。
一位皮雕師一生的產量不到2000件
李曉漫和本刊記者算了一筆帳。
他以每月20天、每天10小時的工作時間計,做一個錢夾耗時4天半。如果再多加些工時,一個月或能產出5到6個錢夾;如果全年無休假地從事皮雕,一年或能產出72個。以25年的工作年限計,一個皮雕師一生的產量不到2000件。
“我一生親歷親為的長夾不會超過這個數,這意味著每賣一件,我的工作生命就少了二千分之一,所以我珍惜我的每一件作品。”李曉漫說。
他目前只做朋友介紹的訂單。即便如此,深信慢工出細活的他大部分時候處于“欠訂單”的狀態。
李榮宗告訴記者,臺灣有句俗語,“戲棚子底下站久了,就是你。”擱在皮雕這行的意思是,只要還有人欣賞你的工藝,就有希望。
初到大陸的李榮宗走開班教學的路線。早期他在天津辦班,共招了10名學員,6天的連續課程,每天8小時的授課時間。
那段時期,“累”是他最大的感受。“但也有學生給了我鼓舞。”李榮宗舉了黃文利的例子。
來學皮雕時,黃文利已年近40,經營著一家皮鞋店,在一次進購皮材時聽聞“皮雕”這個詞。他感到十分好奇,輾轉聯系到了李榮宗,專程從湖北老家趕往天津。
“37歲那年,我把來大陸推廣皮雕的想法告訴我臺灣的朋友,他們就笑我,大陸那么大,等你推廣完,你就真的老了。”李榮宗說,“朋友反問我,皮雕是什么?我說,皮雕是太陽,我是夸父。”
后期,李榮宗行走沈陽、杭州、寧波、蘇州、上海等地,教授皮雕工藝。
類別規范的缺失
在傳授皮雕工藝過程中,李榮宗曾數次尋求與相關機構合作,未果,得到的解釋包括:成立協會的前提是得有一定數量的企業團體提出申請,個別自然人不可;機構方缺少皮雕專業人員鑒定其作品。
上海工藝美術研究所負責人陳毓其告訴《瞭望東方周刊》,“皮雕的概念很模糊。”
他以木雕為例,“雕是把原來的木頭去掉,雕刻是減法。”陳毓其觀感中的皮雕是“燙”出來的——給模子凹好了造型,印壓在皮材上,既沒“加”也沒“減”。
自2015年起,李榮宗以兩屆世界皮雕大賽(美國)冠軍的身份,手捧美國、日本兩國皮雕大師Bob Park和岡田明子的推薦信,接連向幾個地區的工藝美術協會提出了入會申請,均未成功。 陳毓其說,“各地的工藝美術行業協會入會標準不同,但大體上差不多,主要看一個工藝,在這個地方是否形成了產業化,如果形成了,它會列入進去。”
至于工藝美術精品的鑒定,陳毓其則表示,“評審人員是專家委員會抽取的,有專家庫,被抽到的評審人員不可能全部在某一方面很專業。”
上海工藝美術行業協會秘書長朱建中補充道,“評審有很多輪,如果抽取結果不合理,我們可以另外請專家。”但朱建中表示,“我們對有爭議的東西,不讓它進入評審程序,讓爭議基本上達到共識,才讓它進入評審程序。”
“皮雕最大最傳統的類別是唐草紋路,這種紋路最早在中國古代建筑還有衣服上出現。”李曉漫說。然而,“工商并沒有皮雕這個類目的注冊服務。”王嘉慶表示。
李曉漫覺得,類別規范的缺失對進入人們視野的匠人群體會有消極影響。
新的探索
如何真正進入大眾視野?李榮宗的答案是:“讓年輕人加入進來”。
李榮宗的兒子李建鴻已跟隨父親學習皮雕近10年。
但最初李建鴻對皮雕并無好感。在他13歲生日的時候,父親李榮宗提出要送他一個皮雕的卡片夾,遭到回絕。
那時正值電影《頭文字D》熱播,李建鴻開始對跑車著迷。李榮宗便投其所好,雕了一個“馬自達RX7”的卡片夾送給兒子。
正是這個卡片夾,改變了李建鴻日后的人生軌跡。
他先是要求父親多做幾件皮雕作品送人,“班上同學、老師都很羨慕我的卡片夾。”李建鴻說。有一天他得知,班主任因為他送了皮雕的手機套,特意買了一部新手機,這把他樂壞了。回家后,李建鴻興奮地說,“爸,我想學皮雕。”
2015年5月,李建鴻獲得了第22屆世界皮雕大賽季軍,成為繼李榮宗之后第二位贏得該比賽的華人。
王嘉慶認為,“皮雕應該適應人們的審美,形成不同的風格。”他更傾向做實用的皮雕作品,使皮雕成為服務于生活的藝術。
2015年,王嘉慶萌生了一個大膽的想法——與國產包包品牌保蘭德合作。
王嘉慶以保蘭德的圖騰為藍本,設計了一系列的立體圖形,每一個都配上了皮雕小樣,并且拍攝了制作過程。這打動了保蘭德,對方決定,在新一季系列品里面加入這個年輕人的皮雕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