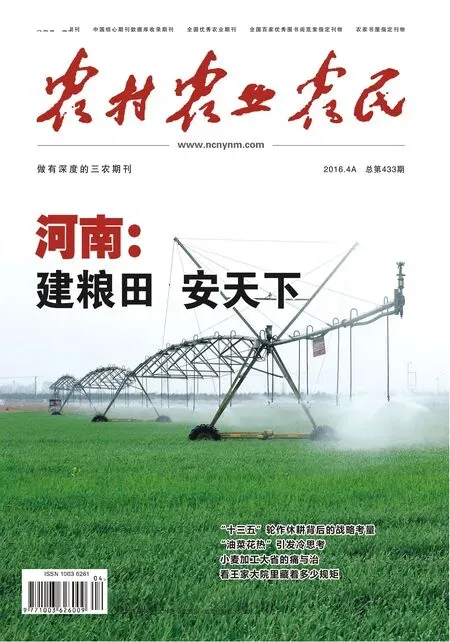別讓撂荒土地傷了“農”之“芯”
——農村土地撂荒現狀的背后
趙允
別讓撂荒土地傷了“農”之“芯”
——農村土地撂荒現狀的背后
趙允
1978年,安徽鳳陽縣小崗村的18戶農民冒著政治風險按下紅手印,將村集體土地“分田到戶”,這一舉動拉開了我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序幕,土地的分田到戶極大地調動了人們生產的積極性。在以地過活、以土為生的那個年代,土里掘金成為每個農村家庭的美好夙愿,也成為家庭生活品質提高的堅實依靠。
可近年來,受農業種植經濟效益低下、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城市等因素的影響,土地撂荒在一些地區愈演愈烈。據國土資源部調查,我國每年撂荒的耕地有近3000萬畝。土地撂荒已成為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一大病灶。
效益不佳和勞力輸出為土地撂荒主要根源
“現在種地除了規模化種植外,否則很難靠單家獨戶的幾畝地掙到錢,這也是絕大多數年輕人不愿意種地,進城打工的一個重要原因。”談及農村目前的土地撂荒情況,陜西省周至縣終南鎮新村的高明英說。
“在農村種幾畝地忙活一年,還不如在城里打工兩三個月的收入。”說起農村中青年勞動力不愿意留村種地的原因,新村常年在陜西省西安市干著建筑裝修工作的趙育樓直言。
采訪中,筆者發現,對于不少經過努力打拼,在城里買房有了安身立命之所的年輕人而言,老家的土地,能證明的僅僅是他們的根仍在農村。
“土地撂荒情況在我們這里比較嚴重,年輕人都進城打工了,即使留在家里的也都不愿意上坡種地,因為忙活一年也掙不了幾個錢,而老一輩人年齡大了,根本沒有精力管理土地。”在陜西省商洛市商州區麻街鎮肖源村,談及村上土地撂荒情況,村監委會主任王增強如是說。而筆者也發現,在商洛山區,和肖源村面臨同樣境況的村莊不在少數,坡地撂荒已成為普遍之景。
對于眾多在地里刨了一輩子的老農民而言,種地收入微薄導致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量轉移城市,而老弱病殘留守是造成如今農村“家有田地無人耕作”現狀的主因。

江西九江市都昌縣徐埠鎮高橋村農民在查看水稻攝影/新華社記者傅建斌
難以管理致山區土地成撂荒重災區
麻街鎮胡新村現年61歲的黨支部書記邵緒山告訴筆者,胡新村的640戶村民分布在直徑10公里左右的面積內,村上總人口約2180人,目前村上撂荒的土地面積占總面積的80%左右。
“這種情況在我們這里的山區尤為常見。”說起土地撂荒,商洛市洛南縣石門鎮副鎮長洪偉直言。
而除了進城務工無暇顧及導致土地撂荒外,筆者了解到,在山區,因土地自然條件影響而主動放棄耕種土地的人也不在少數。陜西省榆林市綏德縣田莊鎮的胡小利告訴筆者,在他們當地,土地種、收基本全部靠人工,機械化程度很低,加上種植收益差,農民種地的積極性并不是很高,而年輕人也吃不了種地的那份苦,這種種收兩難的情況,讓土地撂荒在當地并不少見。
舉家定居,工作在陜西楊凌,老家在陜西省寶雞市陳倉區天王鎮光明村的王先生談及土地撂荒深有感觸。他告訴筆者,現在自己老家就有二三畝坡地處于撂荒狀態,截至目前已有六七年沒有耕種,而類似的情況在他老家周圍還有不少,有的多年沒有作務的地里雜草長得比人還高。“年輕人進城了,留在家里的都是上了年紀的老年人,坡地本來就不如平地那么好管理,在自家土地自顧不暇的情況下,也很少有人有精力包地搞種植,這也是導致我們那里土地撂荒的一個主要原因。”王先生說。
遷人保地和盲目流轉加劇土地撂荒
昔日賴以為生的土地淪為無人耕種的荒地,除了年輕人進城,老弱病殘這些留守群體料理土地乏力的原因外,采訪中,邵緒山還向筆者道出了另一層原因。
他表示,在商洛當地,政府鼓勵住在山上的群眾外遷,這也是政府助力山區群眾脫貧的一個重要手段。可現實情況是,只有收入可觀的群眾才敢下定決心外遷,很多收入稍差的群眾根本不敢輕易搬遷,他們擔心遷出去后生活沒有保障,無以為繼。而有些群眾即使遷走了,仍不肯放棄農村戶口,怕自己在外生活不下去,也回不去。而農村戶口在,這些人的土地就在,給自己留條后路的這種想法加劇了當地土地閑置撂荒情況的發生。
對此,寶雞市陳倉區天王鎮光明村的王先生也表示,在天王鎮山區、半山區分布的一些村莊,因為群眾打工搬遷、移民搬遷而撂荒的土地不在少數。
而除了搬遷戶遷人保地帶來的后遺癥外,采訪中,筆者還發現,對于一些大面積流轉土地的農戶來說,流轉前沒有選好種植項目,土地到手后的盲目情緒也助長了部分農村地區土地撂荒狀況的發生。
陜西省楊凌現代農業科普示范基地主任楊靜濤告訴筆者,基地在2014年第21屆楊凌農高會上宣傳“大馬士革玫瑰”種植項目時,讓她十分驚訝的是,不少前去咨詢該項目的河南、山西等地的農戶手里都有流轉而來、卻因不知道種什么掙錢而撂荒的土地,少則幾畝,多則幾十畝,讓人倍感可惜。
專家支招:緩解土地撂荒要打好組合拳
本該是農民生活“命根子”的土地荒廢無人耕種,這讓不少自幼生活在基層的群眾深感疼惜。采訪中,陜西省乾縣姜村鎮田雙東村60歲的村民陳風虎表示,作為從靠土地過活的年代走過來的農民,看到現在農村可耕地被撂荒或者被不合理利用,自己深感不安。
土地乃食之根本,食則關乎民生。
如何緩解愈演愈烈的土地撂荒情況?近日,筆者就此采訪了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王征兵。王征兵認為,針對農村目前的土地撂荒情況,當地政府應在促進土地流轉上下大工夫,鼓勵農民將土地流轉到專業種植大戶、家庭農場主手里,使土地得到合理利用。“一般撂荒的都是面積比較小的土地,農戶覺得認真經營也掙不了多少錢,還不如打工、做生意。”王征兵說。
除了促進土地流轉外,他認為,農民可以加大力氣在農業上發展一些優質項目,尤其是一些高附加值、高產值的項目,以切實實現在面積不大的土地上獲得較高收益的夙愿。他告訴筆者,自己前段時間在陜西省渭南市蒲城縣龍池鎮調查發現,當地外出打工的人數非常少。在該鎮的埝城村,全村幾千人外出打工的村民僅十幾個,絕大部分群眾留在老家繼續種地,但該村的人均土地面積并不大,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埝城村家家戶戶都種植了一種新品種西瓜,畝產純利潤達一萬多到兩萬元,比很多人外出打工的收益好,這也是當地人不愿意撂荒土地,也不愿意外出打工的一個重要原因。
除此,王征兵認為,應該發展土地托管模式,讓外出打工、無暇照看土地、也不愿意流轉土地的農民將土地交給托管公司代為種、收,農民自己收獲土地里的產品,而他們只需付一些托管費用即可。他表示,這種模式能很好地照顧到一些外出打工隨時可能回到農村的群眾的后顧之憂。“之所以現在有的人寧愿撂荒也不愿意流轉,就是擔心自己打工回來還想種地,土地流轉出去年限太長要不回來,而土地托管則很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農民還能從土地中獲得一部分利潤。”王征兵說。
最后,他認為,針對土地撂荒,政府可以采取和針對工業征地在一定時間內不用給予沒收或罰款的強制措施一樣,對農民予以約束,以減少農村土地撂荒情況發生。
守住18億畝耕地的紅線,就守住了民生之基。在不斷加快的城市化進程中,我們希望新時代的農民在逐夢之余,仍能守好“農之根本”,確保老家田地有人耕作,耕則有所收獲。一切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宜糧則糧、宜林則林、宜果則果,用行動挑國計之大任,換百姓之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