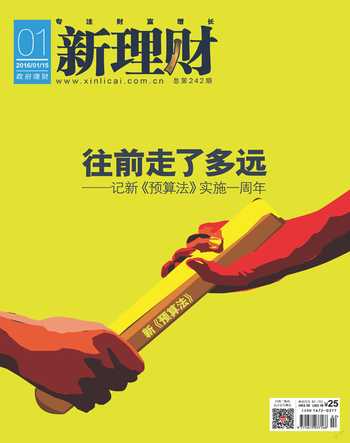艱難行進(jìn)
陳琴
郡縣治,天下安。自秦設(shè)縣以來,我國的基層組織管理都依靠縣治,縣級政府承擔(dān)著縣域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規(guī)劃及實施、社會服務(wù)和文化建設(shè)等職能。2015年,財政部財政科學(xué)研究所組織團(tuán)隊對我國縣級財政經(jīng)濟(jì)運行情況進(jìn)行了調(diào)研,基于調(diào)研和采訪,我們總結(jié)了這一年縣級財政經(jīng)濟(jì)運行的關(guān)鍵詞。
這些關(guān)鍵詞中,既有已然存在的老問題,又有許多在新常態(tài)下涌現(xiàn)的新情況,交織在一起,共同構(gòu)成了縣級財政經(jīng)濟(jì)現(xiàn)狀。要推動我國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升級、保持社會經(jīng)濟(jì)可持續(xù)發(fā)展,需要重視這些問題,找到解決這些問題的方式方法。
經(jīng)濟(jì)增速下行
經(jīng)濟(jì)增速下行是一個普遍現(xiàn)象,也是導(dǎo)致諸多問題出現(xiàn)的宏觀經(jīng)濟(jì)背景。總體而言,就如財政部財政科學(xué)研究所(以下簡稱“財科所”)所長劉尚希所言,結(jié)構(gòu)轉(zhuǎn)換過程中,舊的結(jié)構(gòu)支撐不了當(dāng)前經(jīng)濟(jì)的增長,新的結(jié)構(gòu)又沒形成,對經(jīng)濟(jì)和財政都有相當(dāng)明顯的影響。
資源型地區(qū)、工業(yè)基礎(chǔ)薄弱且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單一地區(qū)、稅源單一地區(qū)受到巨大沖擊。如山西、河南、廣西、內(nèi)蒙古、陜西等出產(chǎn)煤炭、石油、有色金屬等的市縣,曾經(jīng)的資源優(yōu)勢在宏觀經(jīng)濟(jì)形勢下反而變成劣勢,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不順利,經(jīng)濟(jì)增速下滑嚴(yán)重。據(jù)調(diào)查顯示,2011-2014年,山西省GDP增速從13%下降到4.9%,2015年第三季度更是下滑至2.8%。
比經(jīng)濟(jì)增速下滑更嚴(yán)重的,是經(jīng)濟(jì)發(fā)展質(zhì)量不高、效益下降、投資增長乏力、發(fā)展后勁堪憂。盡管近年來各級政府都在強(qiáng)調(diào)調(diào)結(jié)構(gòu)、轉(zhuǎn)方式,但真正實施的并不多,取得實效的少。傳統(tǒng)產(chǎn)業(yè)所占比例依然高,如在2014年山西全省規(guī)模以上工業(yè)行業(yè)中,傳統(tǒng)行業(yè)占比近80%,其中煤炭產(chǎn)業(yè)占比又超過50%,而地方184戶煤礦企業(yè)中130多戶虧損。相當(dāng)多的市縣工業(yè)投資增速持續(xù)放緩,且大項目減少、帶動不足。
相對而言,東部地區(qū)企業(yè)行業(yè)分化明顯。轉(zhuǎn)型早、轉(zhuǎn)型快的企業(yè)、行業(yè)、區(qū)域發(fā)展較好,軟件信息、生物醫(yī)藥、高端裝備制造等新興產(chǎn)業(yè)發(fā)展迅速;反之,鋼鐵、水泥、化工、機(jī)械等傳統(tǒng)行業(yè)產(chǎn)能利用率低,占主導(dǎo)的區(qū)域經(jīng)濟(jì)下滑嚴(yán)重。這種分化顯示出了我國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的調(diào)整和變化,以及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所帶來的發(fā)展動力。
財政收入下滑
經(jīng)濟(jì)增速下降,帶來財政收入迅速下滑。如從2011年到2015年7月的一般公共預(yù)算收入增速,貴州省從44.8%下降到5.3%;河南省從24.6%下降到8.4%;山西省從25.14%下降到-7.8%。山西省基層政府財稅收入下滑情況更為嚴(yán)重,2014年約有一半縣級政府公共財政收入為負(fù)增長;2015年上半年9市、86縣中,50個縣(市、區(qū))財政收入負(fù)增長超過20%。
不僅收入下滑嚴(yán)重,從整體看,收入質(zhì)量也不高,非稅收入占比居高不下。從調(diào)研情況看,從2014年到2015年,在調(diào)研的市縣中,非稅收入所占的比重幾乎都有提升。
依然存在稅收任務(wù)指標(biāo)。雖然現(xiàn)在強(qiáng)調(diào)以指導(dǎo)性指標(biāo)替代過去的執(zhí)行令指標(biāo),但名為“指導(dǎo)性”,在實際執(zhí)行過程中又帶有指令性色彩,地方政府和稅務(wù)部門年初逐級下達(dá)征稅任務(wù)指標(biāo),而且層層加碼。這項指標(biāo)還是稅收政績考核中的重要指標(biāo),有些地方甚至實行一票否決制,連續(xù)2年完成不了,一把手會被免職。
在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財經(jīng)戰(zhàn)略研究院研究員楊志勇看來,這種情況既不正常,也不可持續(xù)。調(diào)研也顯示,這一方面導(dǎo)致出現(xiàn)地方為完成任務(wù)而進(jìn)行稅收空轉(zhuǎn)、虛收等問題,局部地區(qū)稅收存在不同程度的水分;另一方面容易帶來稅收“順周期”問題,造成“過頭稅”,從而加大經(jīng)濟(jì)下行壓力。
如要解決縣級財力問題,楊志勇認(rèn)為,短期需要通過發(fā)債、變賣資產(chǎn)、采用PPP模式等方式多管齊下,綜合用力;長期看,根本性的解決方法還是要找到地方經(jīng)濟(jì)發(fā)展動力。
支出壓力加大
財政收入下滑導(dǎo)致縣級財政運行困難,直接影響了縣級治理和公共服務(wù)的提供。一個明顯的表現(xiàn)是拖欠機(jī)關(guān)單位事業(yè)人員工資,這在山西、遼寧、黑龍江等市縣均有發(fā)生。同時,在保障民生支出、投資建設(shè)以及防范地方債務(wù)風(fēng)險方面,縣級財政都要承擔(dān)更大壓力。
在財政供養(yǎng)人員方面,2014年,國務(wù)院出臺文件相繼上調(diào)了公務(wù)員和事業(yè)單位等財政供養(yǎng)人員的工資福利標(biāo)準(zhǔn),但到2015年,很多縣級層面都沒有完成執(zhí)行到位。這一是增資后人員經(jīng)費增加對支出的沖擊大,二是增資后帶來單位繳納的養(yǎng)老保險及所設(shè)立的職業(yè)年金部分對支出有影響。如,廣西壯族自治區(qū)全州縣僅上調(diào)工資一項支出就占到支出比重的22%。對于不享受轉(zhuǎn)移支付和財政補(bǔ)貼的縣來說,壓力更大。
民生支出逐年增加,大部分市縣民生支出的增速都超過了一般公共預(yù)算支出的同比增速。對中西部而言,一個特別之處在于,當(dāng)前國家出臺了大量交通等基礎(chǔ)設(shè)施投資規(guī)劃,西部地區(qū)也在大力開展交通、旅游、學(xué)校、醫(yī)院、土地治理等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即西部地區(qū)處于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的高峰期。但縣級層面一般公共預(yù)算基本無法安排足額的政府公共投資,之前倚重的土地出讓收入和債務(wù)收入,當(dāng)前也大幅下降。
解決這些問題,一方面需要國家在出臺政策性增資時,盡量考慮地方收支平衡壓力,對基層財政有統(tǒng)籌安排,適當(dāng)給予增資保障。另一方面,地方尤其是省級政府需轉(zhuǎn)變思路,改變財政資金使用方式,通過股權(quán)投資引導(dǎo)基金、產(chǎn)業(yè)引導(dǎo)基金、PPP等模式來支持地區(qū)建設(shè)和企業(yè)發(fā)展。
掛鉤、配套支出依舊
根據(jù)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關(guān)于重點支出一般不同財政收支增幅掛鉤的要求,新修改的預(yù)算法刪除了預(yù)算審查和執(zhí)行中涉及法定支出的規(guī)定,但由于部門法之間的優(yōu)先序沒有明確定位,其他相關(guān)法律沒有修改,如教育法對教育支出的考核仍在沿用掛鉤機(jī)制,基層財政不僅難以統(tǒng)籌財政資金,也給支出造成壓力。
同時,預(yù)算法明確規(guī)定“上級政府在安排專項轉(zhuǎn)移支付時,不得要求下級政府承擔(dān)配套資金”,實際上配套依舊。如2014年桂林市各區(qū)縣政府分擔(dān)中央專項項目投入資金,在項目資金總額中占比區(qū)間為9.61%-44.52%。全州縣本級人員支出已占該縣實際可用財力的78%,配套資金占比達(dá)19%,形成較大隱性缺口,致使當(dāng)?shù)貒蟾闹瓢仓玫戎С鲆煌显偻稀G以趯嶋H執(zhí)行中,如果不配套資金,政府拿不到項目。
劉尚希特別指出,即使現(xiàn)在名義上大配套取消了,小配套仍在。大配套指專項轉(zhuǎn)移支付配套,小配套則是現(xiàn)行體制下許多或明或暗的配套要求。如城鄉(xiāng)居民醫(yī)療保險、養(yǎng)老保險,中央、各級政府和個人分別承擔(dān)一部分,但只要中央出臺提高醫(yī)保標(biāo)準(zhǔn)的政策,地方政府就要進(jìn)行相應(yīng)配套。再如中央要求提高公務(wù)員工資標(biāo)準(zhǔn),地方不論經(jīng)濟(jì)狀況、財政狀況如何都要執(zhí)行。這同樣給地方帶來支出壓力,不僅使政策難以真正落實,也影響了地方財政的可預(yù)期性。但在當(dāng)前體制下無法做到誰出政策誰掏錢,從較長一段時間看,配套資金很難取消。
債務(wù)風(fēng)險不容忽視
財政收支失衡在不同層級政府間都有體現(xiàn),只是程度不一,政府層級越低財政脆弱性越大,這種脆弱性集中體現(xiàn)在政府債務(wù)風(fēng)險上。從調(diào)研情況看,縣級政府負(fù)有償還責(zé)任的債務(wù)比重高且增長快,如2014年,福建仙游縣達(dá)到73%,廣西全州縣在84%以上,貴州省息烽縣則高達(dá)99.55%;從2014年到2015年上半年,息烽縣債務(wù)增長了8.2%,廣西靈川縣則增長了138.46%。因此,還債壓力普遍較大。
2015年進(jìn)行的債務(wù)置換以及新增的債務(wù)額度,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基層政府融資壓力或償債壓力,但對需求來說還是太少,尤其對處于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高峰期的西部地區(qū)來說等于杯水車薪。在房地產(chǎn)市場進(jìn)入下行周期以及土地市場降溫的大背景下,推廣 PPP模式將經(jīng)受市場的檢驗,緩不濟(jì)急。若不能妥善籌劃,適當(dāng)擴(kuò)大政府債券發(fā)行規(guī)模,很可能會影響政府正常的融資需求。不過債務(wù)置換與債券發(fā)行涉及到資本市場建設(shè)問題,如地方債券市場是否真正形成、地方債券的流動性如何增強(qiáng)等,尚存一定的不確定性。
對于地方債務(wù)問題,楊志勇強(qiáng)調(diào)要區(qū)別存量和增量,存量債務(wù)通過置換等方式解決,不能讓存量拖住增量。劉尚希則認(rèn)為,要防止財政風(fēng)險擴(kuò)散、提高地方債務(wù)資金的使用效率,有必要在預(yù)算法框架內(nèi)建立“資本預(yù)算”。即“吃飯的錢”(經(jīng)常性預(yù)算)與“搞建設(shè)的錢”(建設(shè)性預(yù)算)分開,前者不不允許赤字,后者則可以負(fù)債,納入資本預(yù)算。如果不分開二者,經(jīng)常性預(yù)算也出現(xiàn)赤字,會帶來更大的財政風(fēng)險。
融資難、融資貴
調(diào)研顯示,盡管2015年中國人民銀行多次降準(zhǔn)降息,流動性總體充裕,但行業(yè)分布不均衡,流動資金貸款困難。由于商業(yè)銀行對企業(yè)特別是資源類企業(yè)采取限制融資政策,企業(yè)普遍面臨惜貸、限貸現(xiàn)象,這極易造成部分企業(yè)資金鏈斷裂。
從2013年開始,山西地方煤礦大部分到期貸款無法正常續(xù)貸;河南省一些基礎(chǔ)行業(yè)、重化工業(yè)貸款困難,煤炭、鋼鐵、造紙、建材等15個行業(yè)超過30%的企業(yè)流動資金存在很大缺口。這致使企業(yè)不得不通過其他渠道如農(nóng)村信用社、小額貸款公司貸款等融資,這些渠道利率達(dá)到11%-12%,河南省有些中小微企業(yè)實際融資成本在20%以上。融資成本高,企業(yè)不堪重負(fù)。
要解決這一問題,課題組建議,應(yīng)盡快完善金融信貸政策,給予中小企業(yè)和民營企業(yè)融資方面的國民待遇;通過財政支持擔(dān)保、貼息等支持民營企業(yè)融資;鼓勵各地設(shè)立小微企業(yè)融資擔(dān)保基金,成立專門服務(wù)小微企業(yè)的政策性擔(dān)保公司,支持小微企業(yè)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同時,中西部地區(qū)因其區(qū)域經(jīng)濟(jì)薄弱,金融生態(tài)環(huán)境不佳,以及政府財力有限等原因,在信用融資中往往處于弱勢地位,但中西部后發(fā)優(yōu)勢正需要通過必要的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為此,需要通過必要的政策性金融手段適度“逆向操作”,為中西部地區(qū)政府提供支持。
聯(lián)保互保風(fēng)險
融資難、融資貴是引發(fā)民間融資、非法集資以及企業(yè)互聯(lián)互保鏈等問題的重要原因,當(dāng)前這些金融風(fēng)險正在逐步顯現(xiàn),非正常融資和非法集資新發(fā)案件數(shù)量、涉及金額、參與人數(shù)等都在大幅增加。這在中西部、東部地區(qū)都有發(fā)生,相對而言,東部企業(yè)之間循環(huán)擔(dān)保、聯(lián)保互保又稱“擔(dān)保鏈”引發(fā)的金融風(fēng)險更為普遍。
目前出現(xiàn)的“擔(dān)保鏈”,已經(jīng)不再是同行業(yè)、同一商圈小微企業(yè)聯(lián)保互保,相當(dāng)一部分是以某一家或者幾家龍頭企業(yè)為核心,形成了上下游或關(guān)聯(lián)企業(yè)擔(dān)保鏈條。從風(fēng)險看,“擔(dān)保鏈”已經(jīng)超越了單純連帶責(zé)任擔(dān)保,隱藏著大量交叉聯(lián)保互保問題以及以此為名的騙貸行為。而且銀行為了規(guī)避責(zé)任風(fēng)險,在某種程度上助推這種聯(lián)保互保方式。政府為了讓更多企業(yè)獲得貸款,也起到了推動作用。
這樣一來,風(fēng)險更隱蔽,涉及面更廣,出現(xiàn)問題處置難度更大。一旦資金鏈斷裂,貸款企業(yè)和擔(dān)保企業(yè)都面臨破產(chǎn)危險,容易引發(fā)區(qū)域性公共風(fēng)險。近年來,“擔(dān)保鏈”引發(fā)的企業(yè)破產(chǎn)與金融風(fēng)險在溫州等地已多次發(fā)生,需要高度重視。
東北財政現(xiàn)象
東北財政經(jīng)濟(jì)問題近年來是各界關(guān)注的熱點,國家也出臺了多項政策。從調(diào)研情況看,東北財政經(jīng)濟(jì)情況與全國其他市縣相似。
GDP增速同比回落較快,但沒有出現(xiàn)負(fù)增長,2015年遼寧預(yù)計增速為3.5%,吉林前三季度達(dá)到6.3%,黑龍江前三季度達(dá)到5.5%。工業(yè)增加值下滑嚴(yán)重,2015年前三季度,吉林同比增長5.1%,黑龍江同比增長0.2%,遼寧同比下降5.4%;出口皆為負(fù)值。僅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較快,2015年前三季度,遼寧同比增長7.8%,黑龍江為8.7%,吉林為8.8%。
無論是從經(jīng)濟(jì)運行情況還是財政收入情況看,均未出現(xiàn)“斷崖式”下跌,之所以降幅大,一個重要原因是之前虛報比較大,從省到市到縣甚至到鄉(xiāng)都虛報數(shù)據(jù),有些地方水分高達(dá)40%,乃至出現(xiàn)一個縣的GDP超過香港這種怪事。
調(diào)研顯示,東北財政經(jīng)濟(jì)下行的重要根源在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東三省產(chǎn)業(yè)以能源、重工業(yè)為主,第二產(chǎn)業(yè)比重高,其中制造業(yè)和采礦業(yè)占比大。這些行業(yè)受全球經(jīng)濟(jì)不景氣影響大,且東北制造業(yè)又多處于中低端,導(dǎo)致出口下降嚴(yán)重;石油價格暴跌,使黑龍江稅收大減。由此可見,東北現(xiàn)象固然有其深層次問題,但并非個別現(xiàn)象,而是全國統(tǒng)一市場和世界經(jīng)濟(jì)一體化的一個綜合反映。
政府救市風(fēng)險
地方政府救市在東部地區(qū)表現(xiàn)明顯,這主要是因為東部經(jīng)濟(jì)發(fā)展較好,為了穩(wěn)定經(jīng)濟(jì)和和社會,條件允許的市縣采取了救市措施。救市情況五花八門,福建有的市縣通過稅收信息共享、設(shè)立助保金和風(fēng)險補(bǔ)償金的形式,政府增信,降低銀企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從而幫助企業(yè)貸款和銀行放款;山東設(shè)立股權(quán)引導(dǎo)投資基金,引導(dǎo)地方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升級,或者通過財政注資設(shè)立“過橋資金”幫助企業(yè)渡過難關(guān)。
總體而言,救市起到了一定的穩(wěn)定區(qū)域經(jīng)濟(jì)和金融的作用,有利于緩解結(jié)構(gòu)轉(zhuǎn)換中的陣痛,但很容易帶來副作用。比如,可能妨礙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決定性作用的發(fā)揮,減慢結(jié)構(gòu)轉(zhuǎn)換的速度,使該淘汰的企業(yè)不能及時淘汰,形成一些僵尸企業(yè)。僵尸企業(yè)成為目前中國經(jīng)濟(jì)的“癌癥”,與政府過去救市過度不無關(guān)系。同時,地方政府救市面臨著嚴(yán)重的不確定性風(fēng)險,在經(jīng)濟(jì)趨緩下行、財政收入下滑的環(huán)境下,救市會將企業(yè)的風(fēng)險轉(zhuǎn)移到政府身上,不但解決不了企業(yè)的問題,反而可能擴(kuò)大財政風(fēng)險。
因此,如何把握好救市的度,在穩(wěn)增長和調(diào)結(jié)構(gòu)之間找到平衡,發(fā)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是對地方政府能力的重大考驗。
財稅改革難題
事權(quán)與支出責(zé)任不適應(yīng)、財力與支出責(zé)任不匹配,是當(dāng)前縣級經(jīng)濟(jì)財政運行中出現(xiàn)各種問題的重要原因。
從整個支出看,全國85%的支出為地方支出,其中市、縣、鄉(xiāng)約占70%,越往下做的事越多。這與我國整個治理方式相關(guān),治理決策和政策的頂層設(shè)計在中央,執(zhí)行層主要在市、縣、鄉(xiāng)。這種治理結(jié)構(gòu)給基層財政帶來非常大的壓力,不僅很多支出超出了地方的財政能力,且在治理效率和風(fēng)險防范上都存在問題。
還使得基層財政面臨諸多不確定性,如基層財力很多來源于上級政府的轉(zhuǎn)移支付,導(dǎo)致基層不能及時掌握其可支配的財力規(guī)模,在制定發(fā)展規(guī)劃時處于被動。而且中央財政收入減少可以提前通過提高赤字率解決,基層收入減少只能通過舉債、變賣資產(chǎn)等方式解決。
財政體制上的層級化,即主要對本級財政負(fù)責(zé)、一級管一級,是導(dǎo)致財政越往下越脆弱的體制性根源。在當(dāng)前環(huán)境下,這種體制性的弊端越發(fā)呈現(xiàn)出來。上級政府權(quán)力大,一些支出責(zé)任可以下移,財政日子相對好過,越往下政府承擔(dān)的支出責(zé)任越多,權(quán)責(zé)不對等,會導(dǎo)致財政嚴(yán)重失衡。2005年之前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全國半數(shù)縣發(fā)不出工資,現(xiàn)在基層財政危機(jī)可能再次重演。
為此,劉尚希建議,應(yīng)該加快建立地方“轄區(qū)財政責(zé)任”。即每一級政府的權(quán)力與責(zé)任必須相匹配,除了對本級財政負(fù)責(zé),還應(yīng)當(dāng)對轄區(qū)內(nèi)的橫向財政平衡與縱向財政平衡負(fù)責(zé)。基層的一些困難應(yīng)該首先由省級政府解決,而不是直接由中央解決,這樣治理效率才能提高,真正防范財政風(fēng)險在上下級財政之間轉(zhuǎn)移并導(dǎo)致擴(kuò)散。
- 新理財·政府理財?shù)钠渌恼?/dt>
- 札記
- 國際財務(wù)報告準(zhǔn)則2015
- 四十描紅
- 向經(jīng)典致敬
- 羋八子財政傳奇
- 治霧霾,莫要等風(fēng)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