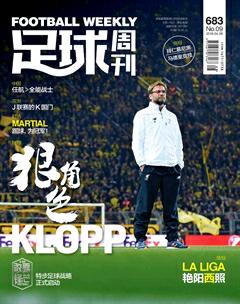一個人的精彩
阿諾·蒂利皮耶
講述這個故事,需要對遣詞造句仔細揣摩,賦予它足夠的優雅和華麗,讓這些詞語配得上那些神奇的時刻。發明一些新詞就更好了,讓贊揚和歌頌登峰造極,比如《法蘭西晚報》所做的那樣,在報紙頭版上配上普拉蒂尼的大幅照片,旁邊寫上“Pelenissime”,這就是一個憑空造出來的新詞,用來與足球歷史上最偉大的時代英雄相比。
或許最好還能從偉大的作家那里尋找一些靈感,把那些他們用來描述人類歷史上最偉大事件和人物的修辭,都照搬過來。
登峰造極
歐洲杯前幾個月,法國文壇女王弗朗索瓦茲·薩岡在其著作《我的美好回憶》中向已故的法國著名哲學家薩特致敬:“希望您能收到我在6月21日寫的這封信,這是對于法國來說非常重要的日子。您、我和普拉蒂尼,是3個在荒野中闖出一條道路、為法國帶來榮耀的人物,卻也遭受無法解釋的輕視乃至侮辱。”
沒錯,普拉蒂尼也沒法解釋人們對他的批評,他在1984年春天對《巴黎競賽》說過:“這個國家有這么多人不喜歡我,他們等著看我倒霉。”或許正是出于這個原因,1984年夏天,當整個法國在世界杯期間為他們的球隊取得一場又一場勝利而歡呼慶祝時,那個英雄卻有些冷漠。
在決賽前幾天的另一期《法國競賽》中,他甚至自己寫了一篇文章:“幾天來,我聽到和讀到了一些有關我的討人喜歡的事情,我不想去評價,也不是受虐狂,只想正確地去對待這些事情,比如強調我沒有自視為歐洲乃至世界頭號球員。因為當前,生活對我開了個大玩笑。”
普拉蒂尼顯然是唯一不這么看的人,或者強迫自己不去那么想的人。世界足球的看法與他正好相反,不論在哪塊大陸,比如《法國足球》就將他稱作“拿破侖”。法國隊中場核心,在每場比賽中都像一位渴望勝利的將軍,他親手用利劍將一個個對手刺倒。
1984年歐洲杯上,法國隊10號是無可爭議的No.1,他在僅僅5場比賽中打入9球:對陣丹麥1球,比利時3球,前南3球,葡萄牙1球,西班牙1球。這次歐洲杯為建隊80年的法國隊帶來了第一座大賽冠軍,同時也見證了一名球員如此強勢地統治一屆賽事。
5場比賽,普拉蒂尼場場進球,與此同時他還作為場上領袖,讓法國隊踢出了效率、風格和激情。意大利《米蘭體育報》著名記者安杰洛·羅韋利向《法國足球》表示:“在我們看來,普拉蒂尼已經站上了足球歷史的最高峰,與貝利、迪斯蒂法諾、普斯卡什、尤西比奧、查爾頓、迪迪比肩。”
永恒經典
在這些傳奇巨星中,只有查爾頓(1966年世界杯)、迪迪(1958年和1962年世界杯)、貝利(1958年、1962年和1970年世界杯)幫助他們的球隊奪得了大賽錦標。除了1970年的貝利,沒人能像普拉蒂尼剛做到的那樣,讓一屆賽事完全打上自己的烙印。
對陣比利時和前南斯拉夫,法國隊10號兩次上演帽子戲法,而且都是左右腳和頭球各進1球,這是某種意義上的非常完美。
盡管當屆賽事打入的最后兩個進球沒有那么漂亮,但幫助球隊先后贏下半決賽和決賽。對陣葡萄牙,他在加時賽最后時刻冷靜地破門(3比2),決賽對陣西班牙,他的任意球幸運地被對方門將漏進球門。
就此,普拉蒂尼成為歷史上第一位舉起大賽獎杯的法國隊長,他超越了前輩和同胞。揭幕戰對陣丹麥,他已經追平了法國隊歷史進球數紀錄(朱斯特·方丹的27球),到賽事結束時已大幅領先原紀錄。
1984年夏天,憑借35球坐穩歷史射手榜頭名的普拉蒂尼還和前輩方丹開起了玩笑:“重要的是能領先方丹,我們永遠都不知道他會不會回來繼續進球!”
不停進球的同時,他知道更重要的是贏球,這是方丹、科帕等前輩沒有做到的。每當賽前奏國歌時,他都會向隊友們高喊:“看著它!看著它!看著它!”它就是放置在主席看臺上的德勞內杯。這么做是為了不要轉移目標,也是幾周來他一成不變的話:“我看重的不是進球,而是晉級半決賽和決賽。”法國隊此前大賽從未闖過半決賽這一關,不論世界杯(1958和1982)還是歐洲杯(1960)。
這或許是因為普拉蒂尼心中的復仇怒火,2年前的世界杯半決賽,法國在同德國的那場史詩般的半決賽中點球大戰失利,讓他的世界杯決賽夢想破滅。因此在半決賽加時賽擊敗葡萄牙后,他表示有些事情變了:“沒有在塞維利亞的失利,就不會有今天在這里的勝利。”法國不再是輸家。
在王子公園手捧德勞內杯歡慶奪冠時,29歲的普拉蒂尼表示自己的國家隊生涯還有2年,作為上屆世界杯4強,新科歐洲杯冠軍,他已將目光投向2年后的墨西哥世界杯。當然他不會知道,傷病讓他沒能最終實現目標。
法國隊在墨西哥只奪得季軍,這樣的結果是令人沮喪而痛苦的。普拉蒂尼此后再也沒能找回1984年歐洲杯上的無敵狀態,那一次他成為法國和歐洲足球歷史上的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