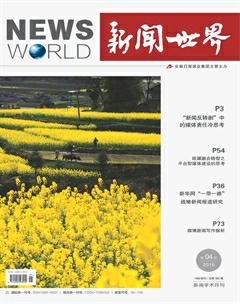轉基因話題微博謠言傳播的“回聲室效應”
康亞杰 彭光芒



[摘要]轉基因話題微博謠言的依附性和反復性根植于一種由信任危機導致的集體道德恐慌下,用戶運用相同的集體記憶框架,對所接收到的關于轉基因話題信息的一種處理方式;謠言的表現形式和敘事策略直接影響謠言擴散,傳播路徑梳理和討論的檢視表明回聲室效應的存在,對微博謠言的認識有待進一步深入。
[關鍵詞]轉基因;微博謠言;回聲室效應
一、研究緣起
傳播學中關于謠言的研究一直是一個常態話題。在當下新媒體迅猛發展的時代背景下,謠言的散布和傳播也開始轉移陣地,微博成為重災區,被人冠以“謠言制造機”的尷尬名稱。相關研究數據表明以微博為代表的新媒體成為網絡謠言的主要首曝媒體。
轉基因話題的討論涉及普通民眾最為關心的食品安全問題,爭議之激烈、參與之廣泛、持續時間之長都極為罕見。大眾媒體對此話題的報道較為慎重客觀,而在微博上有關轉基因話題的謠言卻是經久不息,其呈現出的情緒化和極端化的表達使得視新媒體為公共爭論理想載體的樂觀看法值得重新審視。
二、概念界定和研究對象
關于謠言定義的討論幾乎伴隨著整個謠言的研究歷史,社會學、心理學和傳播學視角下都有不同的解釋和界定。
胡泳結合澀谷保和卡普費雷的著述,深入探討了先前關于謠言定義的缺憾,認為用“虛假”“未經證實”為標準而確立的謠言定義存在很大問題,“反映了對謠言的偏見以及勸人為善的意愿”,結合謠言作為一種社會抗議的功用,重申了卡普費雷對于謠言定義特別強調“官方的公開證實”或“官方的辟謠”的深刻意義嘲。借鑒周裕瓊和郭小安關于網絡謠言研究的界定,結合本研究實際,將微博謠言界定為微博在其傳播過程中起到關鍵作用的謠言,其中謠言的定義沿用卡普費雷的說法,即微博平臺出現并流傳的未經官方證實或者已經被官方辟謠的信息。
相關研究表明,近年來有關轉基因謠言都歸屬于“科學證明轉基因不安全”“轉基因亡國滅種”母題,而后者以前者為暗設前提。2013年10月17日,農業部官網刊登文章,對關于轉基因方面的部分媒體報道進行澄清,稱其所報道的有關轉基因食品“致癌、影響生育、導致土地報廢”等信息為謠言。本研究選取“轉基因致癌”類微博謠言作為主要研究對象。
本研究采用新浪微博提供的“高級搜索”“微指數”,借助可視化微博數據分析軟件“數說風云微博版”,通過人工檢索的方式,以自然月為單位對新浪微博自試運行以來(截至2015年12月)包含“轉基因”“致癌”關鍵詞的微博進行篩選,共搜集612個樣本。通過對該話題的謠言進行歷時性考察,總結其爆發時間規律。選取典型個案剖析,考察微博謠言的生命周期,借助可視化微博分析工具分析傳播關鍵節點和路徑;以內容分析法分析微博謠言文本的主題、表現形式及敘事策略,對比總結其內容特征的共性及歷時性變化。
三、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轉基因致癌”類微博謠言的生命周期
本研究數據顯示,關于轉基因話題的討論與關于該話題的謠言相伴隨,表現出對于熱點事件的依附眭:在通常情況下,涉及轉基因話題的微博謠言并不多,一旦有相關事件進入公眾視野成為議論熱點,相應謠言就會立刻沉渣泛起。
從圖1中能直觀看出,四個較高頂點所對應的日期分別為:2012年9月、2013年3月、2013年6月和2013年8月,起伏變化劇烈,表現為迅速高漲后短時間回落。這種時間一數量走勢所呈現出來的謠言的生命周期并不是嚴格遵循“形成一高潮一衰退一拖尾”四個階段的演變規律,卻更契合“減速”的脈沖傳播的疊加。除此之外還表現出新的生命周期特征:
1、依附性
主要表現在時間和內容上,即不僅時間跟某熱點事件或新聞同步,內容上也是對該事件或新聞的個人引申、猜想。如上述提到的4個時間點對應的熱點分別為:2012年9月19日,塞拉利尼在《食品與化學毒理學》發表文章稱,使用抗除草劑的NK603轉基因玉米喂養的試驗鼠出現高致癌率,21日,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新聞直播問》以“研究指孟山都轉基因玉米或致癌”為標題進行報道;2013年3月13日,孟山都回應轉基因玉米致癌,“兩會”期間轉基因食品話題受代表們關注;2013年6月21日,黑龍江省大豆協會稱轉基因大豆與腫瘤高度相關,食用轉基因大豆油的消費者更容易患腫瘤、不孕不育;2013年8月21日,《環球時報》發表《八問主糧轉基因化》。在內容上,塞拉利尼實驗和央視新聞視頻截圖成為轉基因致癌謠言微博借用最多的理論支撐和證據依附。
2、反復性
表現為謠言微博雖經辟謠,依然反復出現。最典型的是@謠言粉碎機2013年8月18日所辟謠的:“[央視承認轉基因食物可致癌?這是月經謠言!]”。根據觀察,這條謠言最初出現在微博平臺是在2012年9月,在果殼網等平臺辟謠前近一年間亦陸續被多次辟謠,但在2015年12月仍有出現。如果引入集體記憶的研究視角,就比較容易理解這種尷尬的現實。謠言所表達出的對于食品安全的擔憂、對專家的不信任、對政府監管的不滿意,恰使得每當轉基因致癌謠言興起,立即進入集體道德恐慌狀態。景軍認為這種集體道德恐慌的終結有三個出口:一是在其虛構或想象成分被揭露之后,生命力頓然消失,變為一場笑話;二是變為集體記憶的一部分,潛伏在公眾意識中,時刻可以卷土重來;三是經演變成為立法或社會政策,形成對其憤怒對象的司法制裁或政治迫害。央視的報道的截圖,加上食品安全問題層出不窮、“癌癥村”故事的媒體披露以及新科技帶來的種種不確定風險的屢屢曝光,共同構成了關于轉基因話題的集體記憶框架。
不論是其依附性還是反復性,實際上都是一種由信任危機導致的集體道德恐慌下,不同微博用戶運用相同的集體記憶框架,對所接收到的關于轉基因話題的信息的一種處理方式。
(二)“轉基因致癌”類微博謠言的內容特征
充分考慮研究實際需求,兼顧到微博獨特的文本特性,本研究將內容特征分為表現形式和敘事策略兩個方面考察。所謂表現形式是指謠言微博內容的直觀呈現方式,包括文字、圖片、視頻以及外鏈接。微博的形式與空間之上所承載的仍然是以特定符號系統為基礎的表意過程與活動,由此微博傳播仍可被界定為一種敘事行為。敘事策略是借用敘事學的視角,將微博內容視為敘事文本,從而抽象出覆蓋各種敘事文體的敘事策略模式。
1、“轉基因致癌”類微博謠言的表現形式
具體而言,微博的表現形式有文字、圖片、視(音)頻、外鏈接(長微博),微博謠言的表現形式無出其右,只是在組合上更加豐富,多采用“文字+圖片”、“文字+視(音)頻”、“文字+圖片+相關鏈接”的形式。
考慮到用戶在通過微博分享發布視頻或者長微博鏈接時通常會生成一張縮略圖,實際上微博謠言的表現形式更多的是包含外鏈接的簡單文字評論。這些外鏈接多指向某一特定群體的個人博客、某些用戶在視頻網站分享上傳的視頻作品以及新聞片段的拼接和節錄、某些論壇的用戶發言和跟帖。一般來說,微博的圖片和視頻占據較多的屏幕空間,能夠迅速吸引讀者注意,并兼具多義性和趣味性,能夠引發讀者共鳴。而外鏈接多需要跳轉網頁、加載播放器、內容多為枯燥冗長的文字,在碎片化閱讀時代很難被讀者關注。
筆者認為,“轉基因致癌”類微博謠言的這種表現形式的呈現,恰恰說明微博用戶的使用偏好和微博自身的表達局限在面對轉基因爭議性話題的討論上捉襟見肘:難以形成深度理性的討論空間,信息源多來自于未經把關的道聽途說或片面之詞,往往帶有煽情色彩,先入為主的觀念、偏信和盲從使得用戶未經考證即對所分享的內容做出即時回應或情緒表達。這種表現形式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微博謠言的泛濫成因:雖不能簡單歸咎于微博分享發布的快捷,但一定程度上能夠說明,相對于發布個人原創觀點以啟發質疑討論,即時分享使得用戶理性思維處于一種惰性狀態,極易接受恐懼或憤怒的情感動員,從而在有意無意問助長了微博謠言的擴散。
2、“轉基因致癌”類微博謠言的敘事策略
現代敘事學理論認為敘事的本質在于它是話語,敘述的話語行為特征表現敘述什么以及怎么敘述。敘述向來不是純粹客觀的個體行為,而是蘊涵著敘述人一定的價值取向。筆者認為,通過對該話題微博謠言敘事策略的考察,有利于認清微博謠言本質、預防微博謠言擴散并針對性辟謠,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謠言的鑒別。分析認為,多種敘事策略往往出現在同一條謠言微博中,從而增加了其影響力。該話題微博謠言的敘事策略主要有:假借權威、拼接新聞、故意曲解和夸大煽情等四種。
(1)假借權威
這種敘事策略多通過冒用官方媒介的名義、假借非專業領域專家、已被廣泛批評或證偽的實驗結果,甚至捏造科研機構作為消息來源或事實證據,如“央視終于承認了,轉基因食物致癌”、“郎咸平:轉基因的泛濫將會是陽光下的謀殺”、“法國科學家塞拉利尼試驗證明轉基因玉米致癌”、“美國環境醫學科學研究院宣布轉基因食品嚴重危害身體健康”。毋庸贅言,這種敘事策略通過給消息來源或事實證據以“專業”“權威”的信任背書,試圖增加信息的可信性。
(2)拼接新聞
這種敘事策略往往將某新聞事件拼接到無關聯的事情上,并強調或暗示因果關系。如“轉基因大豆導致癌癥高發”“轉基因玉米致廣西大學生精液異常”等。這種敘事策略將毫不相干的新聞事件拼接,而選用的故事多迎合受眾獵奇、窺探心態,從而使得接收者過分關注故事忽略了對兩者相關性的質疑和考證。
(3)故意曲解
這種敘事策略常從身邊事物、現象人手,將一些鮮見食物稱為轉基因食品、正常現象稱為“轉基因異象”,繼而聯系上“致癌”“危險”等字眼。如將報道塞拉利尼實驗結果的新聞標題“研究指孟山都轉基因玉米或致癌”、“可能致癌”曲解成“轉基因食品可以致癌”,或聲稱“圣女果、小黃瓜、甜玉米都是轉基因會致癌”“轉基因土豆削皮不變色、大豆不發芽,還敢吃嗎?”“通過外形六招鑒別轉基因毒食”等。這種敘事策略試圖通過將接收者注意力轉移到異象、鑒別方法的“知識”上,而在有意無意中接受其轉基因致癌、危險的預設前提。然而實際上其所謂的異象、鑒別方法往往都是沒有科學根據的。
(4)夸大煽情
這種敘事策略往往以美帝陰謀論為背景,上升到家國大義、種族存亡的高度,繼而號召擴散周知。如“費爾蒙特飯店秘密會議:用轉基因消滅垃圾人口”“轉基因豆油致癌絕育,請擴散周知,為了下一代拒絕轉基因”等。該策略往往指責官員、專家腐敗無能,表達對其憤怒與不信任,以及對食品安全和醫療現狀的普遍恐慌與擔憂。這種情感動員往往能激發讀者普遍共鳴,從而使接收者在移情和情緒感染機制下,未經考證即對謠言微博進行轉發和擴散。
(三)“轉基因致癌”類微博謠言的傳播路徑
微博的傳播路徑是指微博發布后,通過轉發在微博平臺上所形成的具體傳播路線。其中每個轉發用戶即構成一個節點。研究選取“轉基因致癌”類謠言傳播最多的一條(圖2),借助可視化數據分析軟件討論微博謠言的傳播路徑。(實際上相似內容的微博謠言有數不清的版本,此處基于樣本可操作性選擇在抽樣期間能獲得的傳播最多的謠言微博。)
這條典型的微博謠言運用了多種敘事策略:借用央視的權威,將新聞圖片拼接到敘事中,并將實驗結果故意曲解,同時渲染恐懼情緒,短時間內即引起較大規模轉發和評論。借助可視化分析工具,研究獲得了這條謠言微博的傳播路徑(圖3)和關鍵節點(圖4)。
通過對關鍵傳播節點微博內容的檢視,可以看出這些認證用戶并不是直接轉發用戶“@左小祖咒粉絲團”的原微博而是通過三次以上的間接轉發。整體的數據與這一結論保持一致,在所有轉發中三次轉發(16%)和四次轉發(49%)占據了大多數。由此看來,傳播關鍵節點作為擁有大量粉絲的認證用戶(大V),其轉發行為使得謠言微博獲得某種信任背書而在不同的粉絲群體之間開枝散葉。審視這種大V的轉發,內容缺乏對原微博的質疑,追根溯源,其直接消息來自于同樣為認證用戶并具有相同身份特質的用戶(如周云蓬和左小祖咒同為藝術工作者,韓仁均、北村和程永新皆是作家),其呈現出“粉絲-大V(互動)-粉絲”的具有明顯的圈子色彩。
(四)“轉基因致癌”類微博謠言傳播的“回聲室效應”
微博作為虛擬社區的一種,通常以同樣價值觀、興趣和關注點的人群為基礎建立,即用戶接收到的內容往往來自于具有相同或相似屬性的已關注用戶。從而使得微博討論存在“自我指認”的陷阱,即只在用戶自我設計的交流空間內傳播。用戶可以設置限制評論轉發權限、屏蔽消息等手段,也可以對異議信息采取無視、偏執曲解等方式回應。研究選取了3個有代表性的個案進行分析。
認證為某教育機構銷售經理的微博用戶“@備忘簿”發布原創配長圖微博稱央視報道承認轉基因致癌腫瘤大面積爆發與轉基因食品有關,在其收到的176條評論中,質疑和諷刺的評論如“麻煩先去科普下什么是轉基因,高中生物沒好好學嗎”“你這么造謠,央視造嗎”“看到大家都在罵你我就放心了”卻未見博主回復;在其546條的轉發中,卻未有異議者對信息內容質疑,而是添加上“條形碼以8開頭的是轉基因品”“緊急擴散,讓你的親友都知曉”等信息進一步擴散。比較活躍的微博用戶“@冰凍3千尺”發布原創配知網鏈接微博稱美國某馬鈴薯品種為轉基因品種,“這玩意致癌還導致肝腎衰竭和糖尿病等”。此條微博先是受到認證為某現代農業科技服務有限公司董事長的用戶“@土豆姐姐馮小燕”的評論回復引用中國農科院的馬鈴薯專家康玉林教授觀點稱中國沒有轉基因土豆,受到博主回復質疑專家稱其“忽悠”“騙子撒謊”。在受到認證為共青團陜西省委農工部部長的用戶“@陜西魏延安”的批駁后,回復質疑稱“土豆是不是轉基因的,要等咨詢了有良知敢說真話的專家”,而在“@陜西魏延安”表明身份稱自己“農業院校出身,曾研究馬鈴薯8年之久,有專著,還有成果獎,似乎有說話的資格吧?”之后,改口稱其專業學術資格作為能掙錢的資格,不是捍衛真理的不掙錢的資質,進一步稱官員撒謊沒底線。至此,微博評論已經喪失原有討論焦點。
認證為某知名醫院眼科主任的用戶“@眼科超人崔紅平醫生”發布原創配圖微博稱央視終于公開報道,轉基因食物可致癌。此微博受到教育信息為醫學背景的用戶“@干細胞超人”的熱心指正,并附有詳細的科普資料鏈接,并稱“無論是轉基因食品還是非轉基因食品都和我沒有直接利害關系,我只是在捍衛科學的尊嚴。您在您的專業上很權威,不過對轉基因還沒有正確認識”,這種行為和態度得到了其他用戶的支持和贊揚。博主回復質疑對方身份是否為醫生或轉基因食品從業者,稱“你特別喜歡轉基因食品?沒問題,我不反對你多吃點”“讓時間來證明”“人類的食物是經過幾萬年選擇的結果,隨意改變食物的蛋白分子結構,對人類的潛在危險是不言而喻的!”,在這里的討論,提供了充分的信息以及多樣化的選擇,卻并未出現理想的“真正的辯論和思想的交換”。
如果引入“回聲室效應”(echo chamber effect)這一理論概念,能夠很好地解釋以上現象。即個人總是傾向于接受協調性的信息而避免那些會帶來不協調認知的信息,使得信息或想法在一個封閉的小圈子里得到加強,從而扭曲對一般共識的認識。在關于微博謠言的討論中,發布者拒絕接收來自于其他用戶的質疑和討論,堅持自己的想法和判斷,否認科學界關于轉基因食品安全性的共識,而謠言微博經過持有相同觀念的用戶的轉發擴散,造成一種信息和觀念得到認可的假象,進一步強化了發布者的這種認識,好似回聲室里的回聲讓發言者自以為聲音得到了放大。
四、結論與討論
通過對一定時限內該話題的微博謠言的統計分析,研究發現微博謠言表現出的與熱點事件的時間上的依附性和反復性,與微博用戶在由信任危機導致的集體道德恐慌下運用相同的集體記憶框架處理信息的方式有關。謠言微博有限的信息容量和多樣的敘事策略一定程度上局囿用戶參與深度討論和批判質疑的可能。而“回聲室效應”在微博謠言傳播中的存在,使得在微博上實現“真正的辯論和思想的交換”,進而借助新媒體實現公共領域構建的樂觀期待值得重新審視。
值得欣慰的是,研究注意到辟謠微博賬戶對相關謠言所做努力,其盡職盡責和嚴謹客觀態度值得尊敬,諸如“@謠言粉碎機”“@科學松鼠會”等,以自身網站為依托,吸納相關專業背景的人發布文章,同時鼓勵公眾廣泛參與討論和互動,這將給公眾參與模式的科學對話提供良好契機。據悉,繼推特宣布放開發文限制后,微博也將取消140字發文限制。文本信息容量的增加,是否有助于遏制微博平臺上謠言傳播,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對此我們保持謹慎樂觀。
(作者:康亞杰,華中農業大學文法學院研究生;彭光芒,華中農業大學文法學院教授)
責編: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