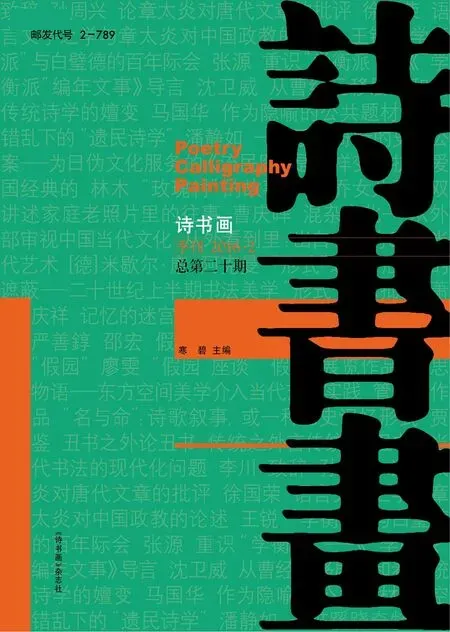假園記─現實體驗與當代藝術的“假園”
廖 雯
?
假園記─現實體驗與當代藝術的“假園”
廖 雯
就“人為建造”而言,園都是“假園”。
中國“園”字外面這個大“囗(音圍)”,透露了“園”有史以來就是人為圈圍的,早期還有細分,“園”植花木,“圃”種菜蔬,“囿”養獸禽。西方“Garden”是古希伯萊語“Gen”和“Eden”的結合,前者是“籬墻”,后者是“樂園”。
就“人心需求”而言,園都是“真園”。
“囗”出一塊領地─除了“占有”的欲望,人性中是否還有一種超越實用的心靈渴望,不能完全在“大自然”中獲得慰籍?一旦為“人”,猶如從母體分離,母子相連卻不能等同,人性的某些要素與大自然息息相關,但不能完全納入大自然的秩序。“園”的“邊界”滿足了人對護佑和內聚的心理需求,讓人可以在大自然的懷抱中,建造自己的秩序,凝神聚氣,寧心養性。
因此,“園”亦真亦假。總而言之,“園”最直接地體現了人與自然的關系,人的生活方式變,園的理念也會隨之而變。
漢代的“上林苑”,本是司馬相如《上林賦》臆造出來的。司馬相如極盡想象,描繪了一個邊界無限大,奇葩異木、珍禽怪獸齊聚的“假園”。司馬相如的本意是諷諫奢靡亡國,認為圍園打獵,荒廢土地,耗費庫財,勞神苦形,獨樂不顧百姓,是“亡國家之政”,希望當時的漢武帝以秦楚為前車之鑒。不曾想漢武帝正值盛氣十足,不僅沒理會諷諫之意,反而大口一開:寫得好,就照這個造一個上林苑吧。嗚呼!直接把文學描寫當規劃方案了,而且是文學最鋪陳的“賦”的形式。于是,在秦的舊苑址上大肆擴建的上林苑,據記載,地跨五縣,縱橫三百里,八水出入其中,離宮七十所,容千騎萬乘,各地群臣爭相進貢的奇葩異木兩千馀種,珍禽怪獸百馀種。上林苑如今已經無存,但據說,那片地域留下來一些奇特的外來物種,就是當年上林苑引進的。
《紅樓夢》中的“大觀園”,從始至終就是紙上談兵的“假園”,然而大觀園完整地體現了文人園林的建造理念,即所謂“天然圖畫”。第十七回,賈政領著門下清客和寶玉游大觀園,走到一處見泥墻土井,紙窗木榻(稻香村),賈政不無做作地說:“倒是此處有些道理。固然系人力穿鑿,此時一見,未免勾引起我歸農之意。”不料被寶玉當眾揭穿:“此處置一田莊,分明見得人力穿鑿扭捏而成。遠無鄰村,近不負郭,背山山無脈,臨水水無源,高無隱寺之塔,下無通市之橋,峭然孤出,似非大觀。爭似先處正畏非其地而強為地,非其山而強為山,雖百般精而終不相宜。”曹雪芹借賈寶玉之口說出了文人建園的根本─雖然是處處造景,如畫如詩,但最根本的依據是那個園所在地原有的自然環境,“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氣,雖種竹引泉,亦不傷于穿鑿”。
至今還“在”的“拙政園”,想來大家都游過,誰也不敢說它是“假園”。當年建園的王獻臣,因官場失意而還鄉,一則“閑居”出于不得已,所以取晉代潘岳《閑居賦》中“灌園鬻蔬,以供朝夕之膳……拙者之為政”明心,二則不敢張揚,“低調”低價地購得一大片水地,一處廢棄的寺院,請當時著名的文人文征明設計。前一年,蘇州曾發大水,所以這片水地并不平整,“中亙積水,浚治成池,望若湖泊”。文征明按照王獻臣“回歸鄉野”的立意,借“園多隙地”,綴為花圃、竹叢、果園、桃林,建筑物則稀疏錯落。從現存的文征明的《王氏拙政園記》、《拙政園圖詠》,以及《拙政園圖》看,當初的拙政園二百馀畝,水域廣袤,三十一景,疏朗平淡,近乎天然野趣,自然風光。據說,王獻臣在此居住的十幾年間,還一直不斷保存和完善這種意趣。
然而王獻臣一死,他的兒子一夜豪賭,就將園輸給了一個叫徐少泉的人。徐氏接手后,“以己意增損而失其真”,拙政園從此淪落,開始了頻繁易主,任人改造的命運。五百年間,拙政園不僅姓過王、陳、張、蔣等,近現代還多次充公,做過時疫醫院、戒煙所、區公所、校舍、兒童樂園等,最后變成現在的“公園”。現在每日游客人頭簇動,拍個照就匆匆離去,這樣的心境也不可能體會園的意境,拙政園真的還“在”嗎?
拙政園雖“在”,其實早已失魂落魄,我們也只能從文獻里尋覓拙政園的本意。園本就是脆弱而不能經久之作。從這個意義上說,拙政園以及所有曾經在某時某地“存在”過的園,也都是名存實亡的“假園”。
陶淵明的“桃花源”,被認為是最虛幻的樂園,不可不謂“假園”。然而,桃花源的避世,并不如隱居者那般逃避現實,陶淵明的人生哲學也不同于“隱居者”。當時隱居在廬山的劉柴桑,曾多次招陶淵明進山,都被陶淵明以“直為親舊故,未忍言索居”婉拒。陶淵明基于親耕親種的關懷之情體會到的互助、親切等等快樂,“不以妻子為心”的隱居的劉柴桑并不能理解。“平和的心境”也如田園,也需要親耕親種,沒有不間斷的關愛,一樣會荒蕪。如果只有逃避現實黑暗的能力,而無感受人性美好的能力,被傷害的心靈一樣得不到休憩,也就得不到最終的平靜。
同是以心靈休憩為目的,“桃花源”也不同于文人刻意修建的“園”。大部分園的建造和擁有者并不是園丁,花草樹木水石(乃至后世園林以及“后花園”中的女人),只是他們造景的審美“元素”,縱然有關懷之情,也是居高臨下的“主人”姿態。他們壘起高墻,自我封閉,自欺欺人地以為自己平靜了,而事實上仍與原有的社會身份依然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遇風吹草動,他們的平靜如同園林本身一樣脆弱,園林一旦易主便面目全非,文人付諸于園林多少有點兒“病態”的情調也就跟著掃地了。桃花源則不同,因為切斷了與文人社會身份的傳統聯系,心情便從根本上不再為“治國平天下”而糾結,而只為感受人性而“快樂”,而“快樂”一旦與社會身份分離,被亂世踐踏的人性,方能如桃花林一般“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而要摧毀桃花源的理想,除非自然秩序被徹底破壞,人類不再有“耕種”的可能。親耕親種的桃花源不僅不虛幻,而且是真正的、真實的心靈憩息園。
古典園林真真假假、虛虛實實,但有一點是肯定和統一的,那就是與“自然”的親和關系。中國傳統生活方式和審美理念以“天人合一”為根本,人與自然萬物同命運,尊重甚至敬畏自然,看重甚至依賴對自然的感受。而現代的生活方式和審美理念,以為“人定勝天”為根本,人凌駕在萬物之上,強調自我意識和人為創造,加之“科學技術”開發迅猛,對大自然的索取遠遠超過給與。西方國家開發早,有識之士很早就意識到這個問題,逐漸回到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開發有“度”。中國正處在開發的勢頭上,尤其是一些歷史和體制造成的傳統文化和審美的斷裂,開發的盲目和無度造成很多問題。
我們當下隨處可見的人造景觀─移栽各處古樹堆砌者有之,湖邊鋪沙灘、陸地植蘆葦、紅樹林者有之,拆掉真古跡成片蓋假古董商業街者有之,當街堆奇石甚至水泥石者有之,以奇花異草塑造花地甚至卡通形象者有之,將園林和建筑格局擴大無數倍,代之以水泥斗拱、廊橋、鋁合金雕花門窗者有之……這些“現代假園”從根本上無視自然秩序,徹底切斷了人與自然的聯系。生活在一個處處是“花園”但又沒有花園的時代,我們從材料、景觀到審美、感知,幾乎都是“假性體驗”,喪失了對自然的“關愛”之情,也就喪失了“心靈的目光”,我們的心靈無法獲得真正的安寧。
這樣的“假性體驗”,我想生活在當下的“每一個人”應該都有所體會,只是我們因為“習慣”而忽略了其深層的意味。當代藝術家作為生活在同樣環境的人,以他們的敏感和態度表達他們的體驗,以藝術的方式提示問題,就是這個展覽的意義所在。因此,這個展覽所謂的“假”,并非道德意義上的“虛假”,而是出文化和審美層面的討論。
整個“假園”展覽,從我的策劃理念到藝術家的創作,使用了“假借”的藝術方式。中國園林以家族姓氏題名者很多,“假園”,假借“賈園”之聲,聽上去幾乎是一個私家園林,其實是一場當代藝術的展場和游戲場,在整體觀念的表達統領下,每個藝術的作品又是獨立的、個人化的。你可以看到─灰塵打磨成鏡面的“影壁”(張震宇),原石拓制的不銹鋼假“假山石”(展望),建筑扎帶栽種在水泥上的“白草地”(余加),手機軟件走出來的北海湖“碧水”(楊千),結構造型塑造的“鉛山(張偉)”,一秒一針扎出來的“圓窗”(何成瑤),被現代方直概念切割的、失去傳統審美瘦漏透的太湖石(王長明),真樹鑄銅的松樹、椅子組合的“文人畫”(史金淞),化纖兒童服裝綴飾手工縫制的“花圃”(楊帆),木板繪制和銅樹組成的“欲望花園”(陳春木),不銹鋼、玻璃鋼等廢棄材料長在一起的“新盆景”(楊光),意象多彩的“陶瓷花園”(沈岳),金屬絲編織、燒毀至鏤空的門扇、條屏、古琴(師進滇),透視解剖園林的絲面繪畫(洪磊),鉛筆完全涂蓋的官帽椅、幾、梅瓶、樹枝、梅蘭竹菊條幅,電腦鍵盤“鍵”像素化馬賽克拼貼的《千里江山圖》(孟柏伸),手工縫制的補花屏風(靳衛紅),金屬絲編制的鏡子、裙子、昆蟲、花朵的“私密花園”(蘇亞碧),無限到有限到“花窗”(廖建華),非傳統方式繪制的“透窗”(謝帆);另有兩個“無形”作品,一個是“嗅覺體驗”,采集展覽當地(北京)、當時(春天)原料(槐花)制作的香(歐陽文東),一個是“聽覺體驗”,以現代觀念改造的中國傳統樂器和中國音樂的自創曲目(李博)。最后,還有一個“視覺體驗”作品,舞臺化的短片《假園真夢》(廖雯)。
觀眾可以在熟悉又陌生,習慣又新奇的感覺中,走進當代藝術的“假園”一游,調動視覺、嗅覺、聽覺全方位地體驗,近距離地接觸當代藝術,進而思考傳統和當代文化的血脈關系。在古代向現代轉換的進程中,沒有哪個民族像中國人這樣,面對如此多難和復雜的文化局面,尋找中國的、當代文化態度,不僅在當下重要和復雜的,也是百年來中國有識之士最艱難的命題。這個展覽只是一個具體的開始。
藝術無古今。每一個時代好的藝術都是那個時代的“當代藝術”。

張震宇 dust160223


楊千 無題


靳衛紅 梅竹石四屏

楊光 勝利

史金淞 脫胎換骨·雙松圖

洪磊 茉莉香片

洪磊 中國的第四堵墻

孟柏伸 這是什么

(前圖)余加 白草地(左圖)張偉 一座山(右圖)何成瑤 51小時27分01秒(左) 40小時33分07秒(右)


楊帆 春天

展望 假園

管懷賓“過園”展覽現場


管懷賓 光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