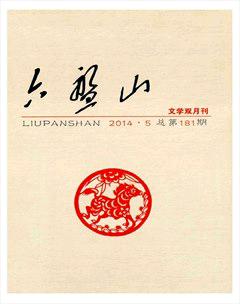千紙鶴
常越
白紙,在我的手中折來折去。媽媽問我還折這些有什么用?我沒回答,繼續(xù)折折疊疊。想你的時候,我就選白色的紙,折千紙鶴。每每聽那嘩啦嘩啦的紙張在手中摩擦著發(fā)出聲響,折出了白色羽翼的小巧靈動,我就閉上眼,它似乎就可以飛翔了。把它握在手心,握得久紙張潮熱了起來,一展開,它就冷了。
兩年前的初冬,下了雪,地上結滿了冰,路很滑。大舅打電話哭著說,表弟夫妻倆遭遇車禍去世了。雪花旋轉著密密層層地包裹住我的身體,如同飄落在寒風中孤單的雪人,四周是冷的,我的眼淚和著雪花飄落了一路。“親愛的表弟,我知道你走了。”“去世”這個詞太生硬,說不出口。我愿意說“你走了。”或許是因為:走了可以回來。就像小時候,你站在村口路邊,怯怯地看那些下車的人里有沒有我。
每逢假期,我從石嘴山坐上班車,回到鄉(xiāng)村的姥姥家待一陣。大舅家和姥姥家在同一個四合院。只要我來,你就靠在門框邊上,離我不遠不近地站著,搓弄著衣角,有時候還踢踢門檻邊的土坷垃。我就俯下身來看你躲閃的眼睛,刮刮你的鼻子,直到你笑了,才放了你。其他的表弟表妹們圍攏起來問長問短,我總是等他們跑遠了,再給你的口袋里多塞一塊糖。那時候,大舅家條件不好,土炕上嬉戲著高高低低的孩子們。他盼著孩子們里能有個城市戶口的,唯有你長得俊俏是大舅的心尖子。老遠,看見我來,大舅就對表弟說:“看,那才是你姐,親姐!你大姑媽才是你親媽。”其他的表弟妹叫我二姐,你叫我小姐姐,我就爽快地答應。后來,大舅舍不得你,沒有把你過繼給我們家,你還是叫我小姐姐,那稚氣的聲音我聽著心里暖。
秋收農(nóng)忙的季節(jié),我就成了孩子王。大人們顧不上給半大孩子們做飯,我們就到瓜田里摘些熟透的西瓜,在田埂上一摔兩半,用柳枝當筷子吃得香甜。沒多久,聽到肚皮餓得咕嚕嚕地響,我就讓幾個表弟妹過來,坐在土坷垃砌成的瓜棚里講故事。講過兩遍,你就惟妙惟肖地模仿我的語氣復述這個故事。看我站起身點燃干麥草桿,驅除黃昏里密密麻麻的蚊蟲,你就小心地把那些在七十年代視為珍寶的小人書,用大大的向日葵葉子包了幾本,似乎是給它們包了碧綠的書皮。當我轉過身,發(fā)現(xiàn)有的小人書上沾染了黏糊糊的綠色葉漿,不由得惱了,看你認真的樣子越發(fā)氣了,就把那些包了向日葵葉子的小人書往你懷里一推,讓你先回家去。
天色越發(fā)暗了,我獨自抱著一摞子小人書,在田埂間流水旁不敢快走,生怕把書掉在了癩蛤蟆的身上,臟得惡心。或許是看我面生,別村的男孩子們會尾隨而來爭搶。你以最快的速度出現(xiàn)在我面前,奪回那些撕扯壞了的小人書。好在鄉(xiāng)下的孩子們大多質樸,慢慢熟悉了,相安無事。
過了些年,大舅家賣了騾子購置了拖拉機,又過些年賣了拖拉機又買了汽車,拆掉舊土坯房蓋了嶄新的磚瓦房。大舅的年齡大了,嗓門也越來越大。舅媽說現(xiàn)如今不興做花布鞋穿……大舅在一旁聽了說:“往后,鞋樣沒啥用,扔了干凈。”舅媽年輕時做布鞋的手藝是村子里數(shù)一數(shù)二的,鞋樣也精致耐看。那些發(fā)黃的舊紙張,多是給我和姐姐做布鞋時用的。我覺得好看,問舅媽要來畫著玩兒。舅媽笑笑不說話,把那些鞋樣塞進了床墊最里面。你知道我喜歡,就偷偷拿給了我,惹得舅媽一頓打罵。聽著你哭,嚇得我好久不敢去大舅屋里轉悠。沒多久我發(fā)現(xiàn),在你家屋檐下的燕子們陸續(xù)飛到姥姥家舊房子的屋檐下筑巢,生蛋,經(jīng)常會從燕子巢里跌落下嘴巴還嫩黃的雛燕,掉在地上唧唧叫喚。你比我長得快,個子高出我一頭還多。我就小聲喚你把它們放回巢里。大舅看見了,呵斥你去給羊兒多喂些草,我會緊跟著去,聽著小羊羔的叫聲,你滿眼都是歡喜。
鄉(xiāng)下的孩子最盼過年。農(nóng)村的慣例是家家戶戶要宰殺幾只成年的羊,一大家子人過年慢慢享用。可是羊兒們凄凄慘慘的呼救聲,我倆聽得難受,就相互悶著不說話。大舅對你說:“喂羊兒你出的力最多,應該多吃羊肉。”你卻說:“羊肉膻,不想吃。”大舅問:“你小時候,大姑媽買來的羊肉,你咋吃得那么歡?”你一臉凄楚,低頭不語,轉身就跑去喂羊,來來回回地溜達了好久。
成年后,你成為地道的莊稼漢,結婚生子,生活得平穩(wěn)快樂,聽說你依然不吃羊肉。我從石嘴山搬遷到了大武口,成了家有了女兒。慢慢地,我很少回姥姥家,難得見到你。見了面,卻生分得不知道說些什么好。你走后,大舅不再大聲說話,總是沉默,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一頭黑發(fā)全白了。老遠地看見我來了,就顫著聲,讓你兩歲的女兒叫我“干媽”,神情和語氣就像小時候他讓你叫我姐似的……
今年,村莊拆遷了修路,大舅搬進了城里的樓房。我離大舅家近了很多,可你卻不在了。過了年,姥姥去世了。我知道,那個小鄉(xiāng)村和姥姥家都沒了。那一晚,我夢見雪后的鄉(xiāng)村天氣很冷,我剛要拉你的手,不知怎地就醒了,淚水滴濕了枕頭,我把枕頭慢慢地翻過去,再也無法入眠。
我想:你是行走在大千世界的普通人,但你有一顆真摯善良的心和一雙溫暖的手。我相信:天堂里會有彩霞映照的海水,會有繁星點點的夜色,也會有我為你放飛的千紙鶴。你會看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