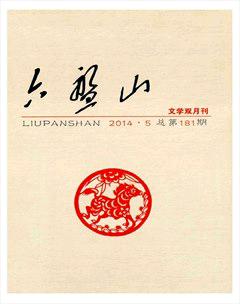忠魂縈繞北坡堂
火仲舫
老朋友成福去世了!就在他離世前五天,我去醫院探望他,一進病房,疲憊的他便掙扎著要起來。兒子和女婿扶著他坐了起來,伸手緊緊握住我的手說:“你精神這么好,我卻成了這個樣子……”。雖然臉上努力溢著笑,但傷感之情不言而語。我輕輕拍打著他的脊背,力求讓他喘得慢一些,并言不由衷地安慰著他:“這是你的一點災難,精心醫治,是會康復的。”他的病情不宜多說話,聊了一會兒我就離開了。沒想到,他去得如此匆忙。
為成福吊唁送葬后,我靜下心來閱讀他的《北坡堂存稿》一書,與他當年相處的往事歷歷在目。上世紀80年代,我在西吉縣工作,他已經在固原地區文聯工作,并擔任《六盤山》雜志編輯。我當時的寫作水平很差,連什么是小說,什么是散文都把握不準,鬧了許多笑話。是成福同志幫了我不少忙,指出了稿子中的不足,也提出了如何寫好作品的建議。他當年的散文《院墻春秋》對我影響很大。他能由一堵不起眼的院墻舉一反三、左右逢源,寫出大西北農村風情,折射時代烙印,對我的寫作啟示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從那以后,我們便成了無話不說的朋友,每次來到固原,我便與他促膝長談,吃他親手做的洋芋面和炒的土豆絲,吃了飯便一同到街頭觀賞秦腔自樂班。因為共同喜愛秦腔,觀賞之時,我們也不時評頭論足。之后回到他的單身宿舍兼辦公室,與他抵足而臥,談天說地,十分融洽。上世紀90年代末,我有幸調也到固原地區文聯,反而成了成福的直接領導,然而,我們并沒有那種生澀的上下級感覺,而仍然以朋友相處。因此,我建議上報地委宣傳部,將他提任為《六盤山》雜志副主編,由他全權負責辦刊。他的文字功夫,不僅在固原地區是一流的,在全區甚至全國范圍內,也不會遜色的。而且他的政策水平高,處事嚴謹,刊物交給他把關,我放心,領導也放心。在他的影響下,我糾正了許多是似而非的字詞用法。如,“平心而論”,我原來常用“憑心而論”,“不言而語”,我以前用“不言而喻”,“的、地、得”的用法,我也是從他那里得到準確答案的。與他相處,我在文字上,文學方面受益匪淺——我能勝任刊物主編,后來創作了那么多文學作品,與他的潛移默化影響不無關系。
就是在那些日子里,我們同共努力,在每年僅有一萬元的財政撥款情況下,將《六盤山》雜志由黑白印刷的56頁碼變成了與國際接軌的80頁碼的四封彩色印刷品。每期刊發的稿件,總會有作品被《人民文學》《十月》《小說選刊》《中國作家》等重要刊物選登,我們舉辦了頗有影響的“西部潮——第二屆西海固文學研討會”“西海固詩會”,評選了“西海固小說、詩歌創作雙十星”活動,舉辦了“老龍潭筆會”和“火石寨筆會”,編輯出版了第一輯、第二輯《西海固文學叢書》,還在年頭節下舉辦每年一度的“全市文藝界迎春團拜會”,爭取中國作家協會支持,在固原創建了“中國作家生活創作基地”,有效地實施了“朝霞工程”,使155名貧困少年兒童受到了中國文聯的資助。“西海固文學”的影響力也由此蜚聲海內外。2000年8月的《文學報》在頭版頭條以《寧夏六盤山區崛起一支青年作家隊伍》進行了報道,當年年底,美國《僑報》和香港《成報》也分別以《寧夏西海固鄉土作家多》和《寧夏西海固作家高產》為題給予了報道評價。在這些工作中,身為辦公室主任(之前還兼任秘書長)的他,無疑做了大量繁雜的組織工作,所形成的各類文件材料大都是他起草或者過目修改的。
作為成福的老朋友,我覺得他的文學創作與他的文字功底以及文學功力相比,還是沒能相輔相成。他的文字功夫扎實,社會閱歷豐富,悟性好,文學創作起步又早,他的創作成就應該遠遠不至于《存稿》內容,而應該更加豐富多采。究其原因,是他看重編輯工作,將大量時間用在編校作者稿件和培養文學新人方面,全心全意為人做嫁衣。
一切,都成為過往。忠魂一縷繞北坡。成福先生,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