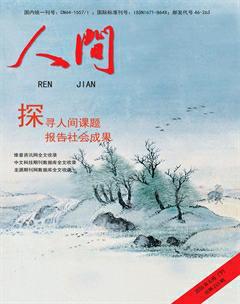黑暗中的光暈
——哥特電影的美學淺談
蔡留言
(南京藝術學院,江蘇 南京 210013)
黑暗中的光暈
——哥特電影的美學淺談
蔡留言
(南京藝術學院,江蘇 南京210013)
摘要:本文通過對哥特電影的分析,展示出哥特電影以其獨特的奇觀化的語境及形象塑造,用帶有“魔幻、壓抑、痛苦、反叛、異化”的情緒表達,為我們展現了其對黑暗壓抑、死亡美學、宗教情結和唯美主義的追求。
關鍵詞:哥特電影;美學;追求
一、哥特電影的概述
“哥特”一詞最早起源于北歐的“Gothic”部族,是歷史上首批劫掠羅馬城的蠻族勢力,從而對西方古典時代的秩序產生了巨大沖擊。因此,哥特一詞也被冠以“野蠻、恐怖、愚昧、無知”等頭銜。時光荏苒,歲月變遷,“哥特”一詞的內涵也隨著時間發生著轉變,在建筑、文學、音樂等文藝領域獨樹一幟,衍生出獨有的“哥特”美學風格。我們所指稱的“哥特電影”,實則是建立在“哥特”美學上的電影風格。與傳統的恐怖電影著重渲染“感官的恐怖”有所區別的是,由于哥特文化與中世紀的時代特質密不可分,所以“禁欲和死亡”是其亙古不變的主題。
二、哥特電影的美學造型
(一)晦暗色彩——紅與黑的詠嘆調。
在哥特電影中,我們所見的色彩多以晦暗的色調為主,色相以黑灰色和紅色的搭配為代表。象征晦暗陰郁的黑色會將紅色中的積極意義剝離,使其象征意義反轉化,從而強化哥特內涵的情感表達。《驚情四百年》《吸血狂魔》《范海辛》等和各種以吸血鬼“德庫拉”為題材的電影中,都會有看起來晦暗壓抑,森嚴神秘的古堡,導演用黑色為我們展現了一片黑云壓城城欲摧的中世紀景象。同時,鮮血作為吸血鬼題材電影中的重要表現,無論是出自于牲畜還是人類,都為這黑色陰郁的畫面內增添了一分強烈的視覺感官的沖擊,晦暗中裹挾著驚恐,驚恐中蘊含著痛苦,痛苦中飽含著邪魅的誘惑,產生一種欲望的訴求。如果說《剪刀手愛德華》用古堡的黑暗和小鎮現實的彩色做對比,那么《理發師陶德》更是將整個倫敦描摹成了一幅罪惡陰暗的哥特油畫,沒有半點彩色的點綴,除了那收割人頭的剃刀下奔涌的紅色血液以及那被絞肉機制成肉糜令人作嘔的暗紅,讓整個電影充斥著復仇的執念和罪惡的瘋狂。被稱為最哥特風的電影《烏鴉》系列則更為著重運用紅與黑的交替,用暗紅色將男女主角的情愛回憶進行雕琢,讓回憶線更加充滿“性”的感官刺激,同時也讓過去的美好染上沉重的暗紅,流露出男主復仇的執念和精神上的恍惚痛苦。導演還將哥特風格從遙遠的中世紀古堡遷移到了充滿罪惡的當代紐約城的街頭巷尾,在那骯臟且充滿危險的月夜下,用暗黑的色彩風格揭露出現實的黑暗與罪惡。
(二)光影勾勒——光與暗的協奏曲。
光影的地位在電影的影像表達上舉足輕重,尤其在哥特電影的影像上體現的更為集中。在光的質量上看,哥特電影偏愛硬光的表現手段,用不均勻的布光產生層疊的陰影,為影片增添神秘靜謐和罪惡驚悚的心理感受,同時也運用了多角度的光線方向進行人物塑造和場景渲染。在《范海辛》《人狼生死戀》《驚情四百年》《烏鴉》中,黑夜中的月光成了逆光呈現的最佳手段,不論是在月下長嘯的狼人,從天際俯沖而下的吸血鬼,亦或是懲治異端的吸血鬼獵人和墳墓里破土而出的活死人,在逆光的勾勒下無不展現出黑暗世界的神秘和驚悚。本來各具情態,驚悚萬分的種種形象在逆光的浸潤下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剪影,少了一分恐怖電影中直觀而強烈的恐怖沖擊,卻用一種近乎符號化的哥特語言為電影增添了一絲優雅的殘酷。除了逆光,側光在塑造哥特式人物的層面上也是不遑多讓。《理發師陶德》中,男主獨坐幽暗的座椅上,月光從房頂的側窗傾瀉而下,讓陶德的面部明暗分明,受眾的銀質剃刀也在明暗光影的交織中寒光閃爍,讓人不禁感受到陶德作為復仇者內心中的陰暗和沉重,儼然一尊披著人皮的惡魔塑像。《弗蘭肯斯坦》中,底光的效果又將一位醉心于發明和瘋狂的科學家形象躍然銀幕,讓人感受著違背倫常之理的邪惡和恐懼。《驚情四百年》的結尾,我們看到的是伊麗莎白懷抱著德庫拉,接受著上帝之光的洗禮,頂光從屋頂射下,如同審判了德庫拉作為吸血鬼一族的前世今生,異端的一生和對基督的仇恨,在柔和的光線下終為煙塵,感受到的不再是恐懼,更是對吸血鬼一族所背負的宿命和情感的肅然起敬。
(三)場景道具——詭異奇幻的奏鳴曲。
哥特式的場景和道具已經成了哥特電影的符號代表,例如象征著中世紀的古代城堡,幽閉的晦暗空間,將黑暗世界與現實世界與世隔絕,同樣也為他們披上黑夜中貴族的華裳,展現出哥特式的高貴冷艷的氣質。除古堡之外,哥特式建筑還有神職人員的修道院、教堂等具有尖頂、飛扶壁、傾斜屋頂、高聳消瘦的建筑景觀,巧奪天工的建筑工藝凸顯出神秘、哀婉、崇高的哥特內蘊,也展現出的是對抗傳統,對抗現世,對抗神明的叛逆姿態。除開哥特式建筑,渲染環境的還有諸多哥特式物象,例如在麥田里佇立著的稻草人,卻在影片中成為了頭戴邪惡南瓜,在荒蕪的大地上置于古堡前景的標志性景觀。枯木層疊的樹林,卻也在氤氳的霧氣中變得驚悚可怖,宛如惡魔招展的手臂,林間深處的墓園也隨意歪斜著風蝕的墓碑和搖搖欲墜、光韻不在的十字架,墳前枝頭赫然佇立的烏鴉,黑色眼眸洞悉著即將到來的噩夢,蝙蝠血紅的雙眼在暗夜里如紅寶石一般閃耀而誘惑,滿月如璧的天際也被如煙塵般飄忽的黑云所侵染。這些典型的場景和物象渲染的不只是單純的恐怖,而是哥特獨特的視覺語境,帶領觀眾走進的是一個充滿奇幻、詭異、充滿死亡和誘惑的黑暗世界,展現的是現世的對立面。
三、哥特電影的精神解構
被稱為“黑暗時代”的中世紀,科學思想的傳播被控制,教會的統治嚴厲非常。其設立宗教懲戒異端的同時,也大肆宣揚禁欲。同時,黑死病等疫病的傳播,也為中世紀蒙上了死亡的陰影。哥特文化與中世紀的時代內蘊密不可分,因此禁欲和死亡成為了哥特電影所探討的永恒主題,筆者將從這兩個方面進行精神內蘊的解構。
(一)“欲望”的纏綿與毀滅。
1.纏綿于神圣和墮落中的情欲。
哥特電影中對于欲望的解讀更加富有思辨和哲理的色彩。說起情欲的要素,無疑在吸血鬼題材的電影中有集中體現。吸血鬼們將微醺或沉醉的女子擁入懷中,或愛撫或舔舐或低吟,舉止曖昧,充滿“性”的神秘誘惑,同時亮出獠牙陷入潔白的脖頸,貪婪的吸吮著血液。相信這“吸血”的行為舉動便足以展現那非低俗色情卻又情欲朦朧的充滿誘惑的欲望表達。縱觀每一部“吸血鬼”電影,觀眾每每都會被這情欲綿綿的舉動所吸引,甚至迷戀。《驚情四百年》中露西受到黑暗的誘惑,與狼人交合的場景,最終淪為黑暗的妓女,放蕩而妖媚。德庫拉伯爵遠渡重洋,喚起米娜前世的記憶,在400年后的倫敦與愛人纏綿云雨。《范海辛》中,德庫拉伯爵與寵妃們撩人而又充滿情欲的愛撫親吻,《烏鴉》中,艾瑞克在復仇的路途中,閃回著和女友在暗紅色燈光下略帶沉重感的性愛片段……這種種哥特式的情欲畫面擯棄了低俗和色情,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近乎于儀式感的行為,這介乎墮落與神圣之間,低回徘徊。正是由于中世紀大肆宣揚著禁欲的特點,所以哥特的文化更崇尚高雅的情欲宣泄。禁欲所帶來的必然是孤獨和寂寥,永生的吸血鬼也飽獨自忍受著歲月的煎熬,所以內心的欲望往往追尋著突破桎梏的爽快。然而在情欲流露的同時,卻又飽含著束縛,正如同久旱逢甘露的沉醉但又有節制,瘋狂卻又暗含著理性,用有約束的放縱展現了這些存在于黑暗世界的“人們”對于愛的渴望。于是,我們才看到《夜訪吸血鬼》中,萊斯特誠然嗜血,卻會在死亡的臨界點前克制自己,及時停止,同時賜予路易和克勞迪婭鮮血,相依相伴,將他們視為最重要的愛人。《驚情四百年》末了,德庫拉伯爵在圣光的照耀下,看著彼此交融、情意綿綿的米拉,最后終于也明白了什么是永恒的愛,大徹大悟的他最終回歸了上帝的懷抱。我們在哥特式電影中看到的縱情者,仿佛是帶著鐐銬在起舞,在導演的渲染下將禁欲和愛的渴求彰顯而出。
2.蔓延在執念與理性中的復仇。
“復仇”是哥特電影常見的故事主線,充滿著仇恨的復仇劇帶來的是刺激和爽快的觀看體驗。《烏鴉》是復仇主題的代表作。艾瑞克在風雨交加,電閃雷鳴的深夜從風蝕的墳墓爬出,帶著前世所遺留的仇恨,帶著被象征著冥界引渡者的烏鴉,手刃自己的仇人。前文也講到在復仇的過程中,閃回著充滿暗紅色沉重的回憶,與女友的種種過去,碎片式的閃現讓他頭痛欲裂,痛不欲生。看著艾瑞克不斷以各種殘酷而朋克的方式殺死過去的仇人,但我們也不難發現在復仇的過程中,怒火沖天的主人公卻沒有喪失理智,與其說是來自地獄的復仇者更不如說是救贖者,在影片中他救贖了朋友的母親,幫她消除毒癮回歸家庭,更在最后一刻將自己的朋友從反派手中拯救。所以即便是復仇,但是哥特式的復仇除了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執念,還帶有一絲憐憫和救贖的理性混合其中。但是,在另外一部《理發師陶德》中,陶德卻用讓自己的仇恨占據了主動,混擾了內心的清明。手握剃刀,口中吟唱著惡魔的歌聲,無情而冷血地收割著生命,就如同死神一般冰冷而可怖。仇恨蒙蔽了自己的雙眼,最后的結局卻因為仇恨讓自己對自己的妻子痛下毒手,懊悔不已。仇恨的終點不是寧靜的天堂,而是一片痛苦的煉獄,讓自己被仇恨吞噬甚至是毀滅。在哥特電影的獨特語境下,我們看到的是對于仇恨的深度思考,而不只是流于B級片的感官刺激。哥特電影對于復仇的解讀是瘋狂而又理性的,創作者能從驚駭的形象與恐怖的復仇中挖掘到人類自身的欲望、罪惡乃至社會價值、人倫道德的淪陷和喪失,用復仇的欲望來承載著對于罪惡的審判和救贖。
(二)“死亡”的崇高與凈化。
中世紀時期,人們不堪蠻族的劫掠和疫病的侵襲,紛紛期盼著死亡的到來,認為死亡是一種痛苦的解脫。意大利的教會制度也誕生了一批覺悟甚高的主教,安布羅斯就是其中之一,他主張死亡是一種善,人們應當勇敢面對。也只有在中世紀的痛苦和折磨中,“死亡”才會有了崇高的定義。尼采由悲劇藝術引伸出來的悲劇世界觀則是“肯定生命,連同它必然包含的痛苦和毀滅,與痛苦相嬉戲,從人生的悲劇性中獲得審美快感”。尼采的悲劇理論是給悲劇和死亡賦予美的少數幾種悲劇理論之一,它把悲劇看成是燦爛輝煌的,一種“形而上的安慰的藝術”。哥特于死亡更多的是一種凈化,是一種向死而生的崇高精神境界。蒂姆伯頓便是操控死亡的魔術師,讓哥特電影對于死亡有了深刻的解讀。《僵尸新娘》為我們展現了一個光明的死亡世界和黑暗的現實世界,女主角艾米麗雖是死亡世界的居民,卻擁有著善良和正義的本心,和男主角一起揭露了現實世界的罪惡、貪婪和殘忍,最后懷揣著滿心的祝福,化成千萬只蝴蝶踏破月光飛向遠方,以死亡的離去換來愛情的升華與靈魂的凈化。哥特一族崇尚死亡,追求著陰郁、詭異,但那只是為了反叛現實社會的黑暗,用更加痛苦悲傷的方式來向現實世界進行痛訴和譴責。《烏鴉》中復仇者艾瑞克一個個手刃自己的仇人,雨夜中雷霆轟鳴,主人公用惡人的死亡宣泄著對于美國現代都市的絕望,但也充當著救世主,在最后殺死了邪惡勢力的頭目,凈化了世間的罪惡。因此,在哥特電影中“死亡”的內涵具有著雙重表意,一個是為了突出以死為善,向死而生的主題意蘊。另一個則是為了用死亡的美好揭露現實的黑暗,讓“死亡”的意義更加崇高而偉大。
四、哥特電影的時代意義
在大眾文化迅速發展的當代,傳媒行業的發展為哥特電影的流行奠定了基礎。大眾文化的產生,張揚了人的個性,加上其獨有的商品性特征,讓充滿暗黑系風格的哥特電影迅速崛起。在現代社會,物質富足的環境為青少年追求個性,渴求另類的行為創造了有利條件。由于哥特電影中大量的暗黑元素及反烏托邦的叛逆主題,使得當代觀眾們無論從感官和精神上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蝙蝠俠》等一系列超級英雄電影就運用暗黑系的哥特風格為觀眾締造出感官的愉悅和爽快。這類電影對于陰暗和罪惡的過分刻畫借由現代銀幕的表現形式得以放大,故事的陰暗,融入了社會中病態的元素,擁有瘋狂頭腦詭異邪魅的小丑,精神崩潰人格分裂的雙面人,外貌丑陋性格偏激的企鵝人,在現實社會無從發現的奇人和病態化的價值觀念,更是受到了當代社會部分人的強烈呼應,更成為了各種好萊塢大片的首選題材,具有較強的商業化特征。然而除開觀眾的獵奇心理以外,在當下激烈的社會競爭下,每個人處于時代的壓力,心中往往堆積和壓抑著許多負面的情緒。而哥特電影的產生,正是為了用極度陰郁和痛苦的表現形式,讓受眾得以找到情感的釋放和宣泄點,換句話而言劇情的輕描淡寫,畫面的光鮮亮麗,無法滿足觀眾們日益提升的審美需求和多元化的審美體驗,除了電影以外,哥特風格的文化還滲透在了文學、音樂、建筑、服裝等多樣化的領域之中,多樣化的文化與電影文化進行聯動和影像,對受眾的審美意識產生了深遠影響。因此,哥特式電影美學在當代大行其道也是時代的必然。
中圖分類號:G4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64X(2016)06-0213-02
作者簡介:蔡留言(1991.9-),男,漢,湖北,研究生,單位:南京藝術學院傳媒學院,影視編導專業研究生,研究方向:影視編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