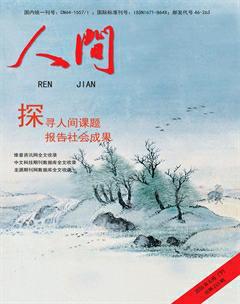唐傳奇《聶隱娘》體現的史傳性的研究
左思
(華南師范大學,廣東 廣州 510631)
唐傳奇《聶隱娘》體現的史傳性的研究
左思
(華南師范大學,廣東 廣州510631)
摘要:晚唐傳奇《聶隱娘》對聶隱娘女俠形象的描寫,不僅對當時及后世的創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還反映了當時時代的一些社會特征和社會心理,與歷史和史傳文學具有很密切的聯系。
關鍵詞:《聶隱娘》;史傳;俠客
《聶隱娘》是晚唐時期一部很重要的傳奇故事,后世的很多藝術創作,比如《西游記》等,都有著《聶隱娘》的影子。前人大多從歷史考證層面、文化意蘊層面來對《聶隱娘》進行研究,很少能聯系到其與史傳的關系。所以本文主要從史傳文學的角度,淺談《聶隱娘》中體現的史傳性。
一、題材的史傳性
題材的史傳性是指小說故事與歷史的某種事實相關。雖然《聶隱娘》是一部描寫女俠聶隱娘事跡的傳奇故事,并非是歷史題材小說,但是其中反映了一些可供考究的歷史事實。
首先,從人物和歷史事實的關系上來看,《聶隱娘》中的人物是在歷史上真實存在的或者映射到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比如說,文章中“陳許節度使劉昌裔”及其兒子劉縱,在歷史上就真實存在,姓名、官職都與歷史相同;據著名學者卞孝萱先生:“按照正史所記載的劉昌裔、田季安履歷,對照《聶隱娘》所云‘云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昌裔不協,使隱娘賊其首’之魏帥,應是田季安”①——唐朝藩鎮節度使、軍閥。所以文中“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昌裔不協”實際上反映了唐朝中期貞元年間,藩鎮割據中的斗爭情況,這是故事的背景,和真實歷史相呼應。
其次,《聶隱娘》中,聶隱娘不僅自己學得一身好武藝成為一代令人尊敬的女俠,而且在面對自己的婚姻時候有著不同尋常的表現:“忽值磨鏡少年及門,女曰:‘此人可與我為夫。’白父,父不敢不從,遂嫁之。”此外,聶隱娘為劉昌裔做出了貢獻之后,“乞一虛給與其夫。”實際上承擔了家庭生計的責任。這三個方面都多少可以看到唐代女性地位的提升。
唐代是我國封建王朝的鼎盛時期:對內而言,社會經濟、政治、社會、文化高度發達,統治者也采用開明的政治態度,所以唐朝人敢于并且樂于尋求自由的天性,婦女們也比較曠達不羈。女子著男裝是一個最好的例證:“婦女著男裝,是唐代比較特殊的一種社會風俗。……《新唐書》記載,玄宗天寶年間‘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內外一貫矣。’”②再者,唐代婦女接受文化教育者比較普遍,文化水平也相對較高;對外而言,唐朝與亞非各國經濟文化交流頻繁,這些異族習俗、北朝遺風沖擊著原有的封建禮教,所以也使唐代婦女形成了奔放、外向的精神面貌。所以,在傳奇《聶隱娘》中,作者可以表現出女性地位的提高,而讀者絲毫不會感到奇怪,這與當時的歷史背景和條件是相吻合的。
最后,《聶隱娘》中,神尼選擇了聶隱娘作為自己的弟子,將她送到一個“數十步寂無人居”的地方進行修煉,同時給她了仙丹,使聶隱娘能夠在山崖上攀援。這些都體現了仙道中“嚴擇弟子”③、遠離塵囂、服食成仙的色彩。可以說聶隱娘技藝的修煉與道教息息相關,側面反映出唐代對于道教的崇尚。
唐太宗在貞觀十一年明確規定:“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這樣子就將道教置于佛教之前。道教受到上層推崇之后,迅速在社會上傳播開來,僅僅《新唐書》記載的官方統計數字就有“天下觀一千六百八十七,道士七百七十六,女官九百八十八。”④道教在民間的盛行可見一斑,作者也將當時盛行的道教思想滲透在了傳奇的創作中。
二、思想觀念的史傳性
前文提到,卞孝萱先生已經考證出文中的“魏帥”就是田季安。根據《舊唐書》:“季安性忍酷,無所畏懼。有進士丘絳者,嘗為田緒從事,及季安為帥,絳與同職侯臧不協,相持爭權。季安怒,斥絳為下縣尉;使人召還,先掘坎于路左,既至坎所,活排而瘞之,其兇暴如此!”⑤在文中也提到聶隱娘認為“知魏帥之不及劉。”可知,聶隱娘從田季安轉投劉昌裔是棄暗投明,表現出的是忠義思想,這符合傳統的儒家思想。而范文瀾先生曾說:“史官文化的主要凝合體是儒學。”所以《聶隱娘》中體現的忠義儒家思想實際上是史官文化,與史傳中表現出的思想相一致。
三、小說藝術的史傳性
《聶隱娘》沿用了史傳的編年記事的敘事結構,運用了一系列表示時間的詞語,比如:“貞元中”、“數年后”、“如此又數年,至元和年間”、“自元和八年”、“后一年”,以時間為線索,描述了隱娘的主要事跡,讀這篇傳奇仿佛就是在看一篇聶隱娘的傳記。
四、《史記》對于《聶隱娘》創作的影響
《史記·游俠列傳》中提到:“今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太史公的這段描述完全寫出他理想中的游俠形象,而聶隱娘的形象也與太史公的描述很相似:雖然她殺人的行為有悖于常人認為的正義,但是她答應劉昌裔打敗精精兒和妙手空空兒,并且拼盡自己的全力做到了;她也并不是為了自身的利益反抗魏帥,而是為了正義;雖然有恩于劉昌裔,但是她也沒有過分所求,只是為了丈夫要了一個職位來養家;之后即使她四處云游,卻也在劉昌裔去世的時候現身送別;之后她還想辦法保護劉昌裔的兒子劉縱。這些行為都能看出聶隱娘是符合太史公說法的理想中的誠信、正直、勇敢而不求回報的游俠形象,所以很難說聶隱娘形象的塑造沒有受到《史記》的影響。
總之,聶隱娘這個生動的人物形象帶給了很多人聯想與想象,這也就是為什么后人在創作的時候會借用其中的元素以及熱衷于將這篇傳奇改編為電影等其他的藝術形式。同時,這個藝術形象的背后,與歷史和史傳又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為后人提供了研究歷史的線索。
注釋:
①卞孝萱,《<紅線>、<聶隱娘>初探》,《揚州大學學報》1997年第2期,第33頁。
②《中國風俗通史·隋唐五代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頁。
③劉娜,《<聶隱娘>的文化意蘊》,《保山師專學報》第24卷第3期,第44頁。
④《新唐書·卷四十八·百官志三》,中華書局2013年12月版
⑤《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一·列傳第九十》,中華書局2012年3月版
中圖分類號:I207.4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64X(2016)06-000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