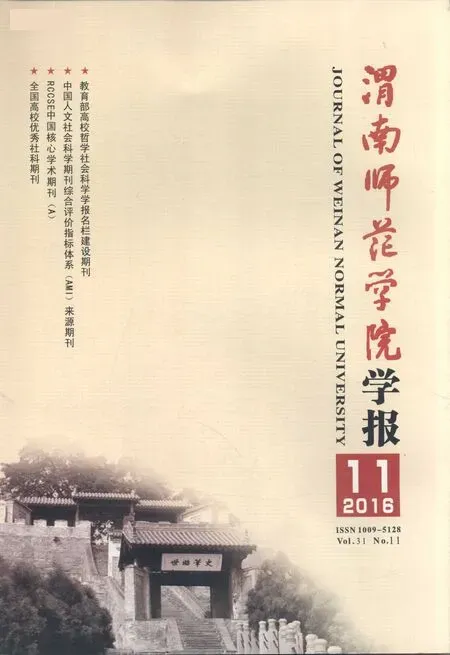維吾爾現代化詩歌的傳統溯源
王明科, 王 媛, 阿不都納·斯爾阿卜來提
(喀什大學 人文學院,新疆 喀什 844008)
維吾爾現代化詩歌的傳統溯源
王明科, 王媛, 阿不都納·斯爾阿卜來提
(喀什大學 人文學院,新疆 喀什 844008)
摘要:維吾爾現代化詩歌語義源于維吾爾語境,以“烏鴉”與“蛇”為例可以看出其意象語義的醞釀語境與草創源流在民族性方面體現出獨特的不同于漢語語義的溯源含義。維吾爾現代化詩歌起源的最早藝術因子存在于維吾爾傳統詩歌中,維吾爾新時期朦朧詩的最早藝術因子則起源于維吾爾族的民歌以及長期的詩歌發展變遷中。以維吾爾民歌《其曼迪故》與《十二木卡姆》為例可以看出從民歌到傳統詩再到現代詩包括朦朧詩,期間的藝術因子一直遺傳存在,并不是從漢語詩歌中嫁接過來或者借鑒過去。
關鍵詞:維吾爾詩歌;現代化;傳統;
一、維吾爾現代化詩歌語義源于維吾爾語境
維吾爾現代化詩歌的意象語義,特別是其醞釀語境與草創源流,與漢語現代化詩歌的意象語義起源,在民族性方面體現出獨特的不同的溯源語義。這些意象比如“樹林”“土地”“河橋”“黑夜”“太陽”“鳥獸”“祖國”“月亮”“花草”“山水”“天地”等等。在現代性的視界下,維吾爾詩歌意象的能指與所指,與漢語現代化詩歌意象的能指與所指相比,有時候兩者之間具有明顯的不同。
首先,以“烏鴉”意象作為一個典型術語來觀照。在漢語現代化的詩歌中,“烏鴉”意象一般很少出現,因為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中國內地高揚理想與塑造神圣的時候,絕大部分新時期詩歌的意象都是很陽光的,都是《一代人》中“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式的在苦難中對于未來的執著信念與樂觀理想的表達。并且,在現代漢語言文學的語境中,“烏鴉”意象一般隱含了不太好的預兆,是不太受歡迎的意象,甚至是令人不悅的意象,連漢語口語中都有“閉上你的烏鴉嘴”式的表達。即使在前120年前后“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提倡寫新詩、反對寫古詩”的詩歌現代化激烈革命中,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胡適寫的中國第一部白話新詩集《嘗試集》中關于“烏鴉”意象的詩歌《老鴉》,第一部分也寫了烏鴉意象的不吉利含義:“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的啼/人家討嫌我,說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1]
但是,在維吾爾現代化詩歌作品中,“烏鴉”意象特別普遍,而且沒有一種不祥預兆的暗示,也沒有一種不吉利的含義。
博格達·阿布都拉創作,蘇德新翻譯的發表于2005年12月20日《新疆日報》的維吾爾詩歌《烏鴉的傳說》[2]141:
烏鴉在秋天偷了玉米,
以影子作了一個標記。
他說埋起來日后好吃,
提前預備好免得擔憂。
一天它呱呱地飛來,
可落腳的地方沒有那影子。
以喙啄土,
早晚跺腳。
可是掌犁者時來運轉,
顆粒總是逃不脫犁耙。
麥場獲得雙倍的收成,
胡子扭來扭去地狂笑。
顯然,在博格達·阿布都拉創作的維吾爾現代化詩歌作品中,烏鴉不但不是什么不吉利的象征,反而是給播種者帶來了極大的豐收快樂,是豐收者之所以豐收的播種天使。
尼米希依提創作于1949年9月的《寫給旅途上的戀人》中第7節有這樣的詩句:“園丁啊今日我很高興/戀人要來,快把紅毯鋪上/把烏鴉弄成期貨/讓綠洲鮮花遍地。”[3]97第18節繼續這樣寫道:“烏鴉根本不懂春天/年輕懂不了愛戀/男人能識別男性/就算雙手被捆去。”[3]97顯然,尼米希依提創作的維吾爾現代化詩歌作品中,烏鴉不但不是什么不吉利的預兆,反而是迎接戀人的禮物,是高興心情的寄托,“烏鴉”是與“紅毯”“綠洲”“鮮花”等一起迎接心上人開心時刻的裝扮。
可見,在維吾爾現代化詩歌作品中,“烏鴉”意象不但沒有不祥與不吉利的含義,而且經常是作為飛鳥的意象普遍使用:“棲息在枝頭/身心勞頓/在疾速的飛翔中/卸下一身的疲憊。”[4]155
其次,以“蛇”意象作為一個典型術語來觀照。在漢語文化語境與漢語詩歌寫作中,“蛇”意象的含義一般指的是冰冷、冷血、冷漠、恐怖、狠毒、可怕、陰險等義項,很少有詩人把“蛇”意象用作正面或者愉悅感情的寄托,即使被魯迅稱為“中國最為杰出的抒情詩人”的馮至,出于比喻手法的創新,在《蛇》一詩中將“寂寞”比作“一條長蛇/冰冷地沒有言語”[5],勸說自己心愛的苦苦相思著的姑娘“萬一夢到它時/千萬啊,莫要悚懼!”[5]但也僅僅是為了強調相思之苦與寂寞之苦,并沒有把“蛇”意象當作可愛與美好的象征。
但是,在維吾爾現代化詩歌作品中,“蛇”意象比較普遍,并不會強調冰冷、冷血、冷漠、恐怖、狠毒、可怕、陰險等義項,而且有時候還有一種正面或者愉悅感情的寄托。
在艾爾肯·努爾創作,鐵來客翻譯的朦朧詩組詩《夢幻島》的第四首,詩歌題目也是《蛇》,但詩歌內容中對于“蛇”意象的表達完全與馮至不一樣,詩人多次追問“蛇”是什么的問題,然后對這個問題試圖做出各種回答:“蛇的鼻祖原本是撒旦”,“蛇的鼻祖原本是仙女”,“蛇的鼻祖原本是翅鳥”,“蛇的鼻祖是無形的靈魂”,“蛇的鼻祖是有犄角的公牛”等等。令漢語讀者感到十分新奇的是詩人認為:“蛇是螢火蟲/它在我們黑暗籠罩的軀體深處透出熒光/像太陽的熠光將我們的心永恒地照亮”。特別令漢語讀者感到十分震驚的是詩人認為:“蛇是上帝/它會使我們復活”。
可見,在維吾爾現代化詩歌作品中,“蛇”意象不但很少作為表達冷漠、恐怖、陰險等感情的意象符號與象征含義,相反被比喻成了熠熠生輝光照人們肉體甚至靈魂的太陽,溫暖并能夠穿透我們的心靈,驅走黑暗并能夠照亮我們的軀體。甚至“蛇”成了拯救人們以及人類并且促使人們以及人類能夠復活的無所不能的全知全能的具有無比超力量的上帝。
二、維吾爾現代化詩歌風格源于維吾爾民歌
關于維吾爾現代化詩歌的起源問題,在許多維吾爾學者看來,維吾爾現代化詩歌是受漢語現代詩的啟發影響而形成。
可是,筆者認為:維吾爾現代化詩歌的產生與繁榮,除了受到外國詩歌特別是外國(具體來說是法國)象征主義詩歌以及中國古代詩歌、中國現代漢語詩歌的直接影響之外,維吾爾民族文學自身內在的發展訴求以及運演過程,維吾爾詩歌從古到今的民歌以及維吾爾族文人早期創作詩歌本身內在潛藏的藝術質素及其沖擊力,才是產生維吾爾現代化詩歌的核心動力與主要根源。
漢語現代詩的出現,只是讓維吾爾詩人對于現代詩的寫作實踐更加自覺,并有意形成了一個潮流與派別。但實際上,即使沒有漢語現代詩的出現,維吾爾現代詩也一定會產生。只是,對漢族現代詩的借鑒,加速了維吾爾現代詩潮的出現與成熟。
以維吾爾新時期朦朧詩為例,筆者認為,在這個復雜的接受與變異以及創化生成的過程中,首先最直接的就是中國新時期以舒婷、北島、顧城、江河、楊煉等為代表的漢語朦朧詩的影響,其次就是外國詩歌特別是外國象征主義詩歌的影響,此外,中國古代的詩歌以及中國現代的其他不是朦朧詩的詩歌,也對維吾爾朦朧詩有一定的間接影響。
但是,以上的這些影響都是很有限的,都是表面的現象,是局部的外圍的滲透與影響,根本不是從本質的內部的自身演繹中生根發芽的。什么力量才是最本質的最根本的最內在的最具有遺傳性呢?
如果說,維吾爾現代化詩歌起源的最早藝術因子存在于維吾爾族的傳統詩歌中,那么,維吾爾新時期朦朧詩的最早藝術因子則起源于維吾爾族的民歌以及長期的詩歌發展變遷中的朦朧因子。從民歌到傳統詩歌再到現代的新時期朦朧詩,期間的朦朧藝術風格的因子是一直遺傳并強力存在的,這并不是從漢語詩歌中嫁接過來的或者從外國詩歌拿來使用的。著名的維吾爾民歌《其曼迪故》就隱含了維吾爾朦朧詩的某種朦朧藝術因素的傳統遺傳因子。


木合塔爾·庫爾班將《其曼迪故》翻譯為:
遠看山嶺一片白,其曼迪姑
山上積雪融不開,其曼迪姑
我把心兒交給你,其曼迪姑
你卻對我不理睬,其曼迪姑
門前都是葡萄藤,其曼迪姑
纏纏繞繞理不清,其曼迪姑
我的心兒很沉重,其曼迪姑
一定對你說不明。其曼迪姑
田里禾苗綠油油,其曼迪姑
請你過來走一走,其曼迪姑
不要說我太年輕,其曼迪姑
愛你不必有理由。其曼迪姑!
在這首維吾爾民歌中,對少女其曼迪姑的暗戀與追求都是以一種很朦朧的含蓄的方式來表達,不像漢語現代化詩歌中的許多愛情詩,熱衷于直抒胸臆與直接表白,即使像胡適、汪靜之、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艾青等一批優秀詩人,也免不了詩歌的獨白與直露,至于殷夫、田間、柯仲平、臧克家等人的直白詩歌數量更多。到20世紀80年代,舒婷、北島、顧城、楊煉等人倡導漢語朦朧詩的時候,他們創作的許多朦朧詩的“朦朧”也還是很有限的,許多詩歌其實不算很“朦朧”。
維吾爾民歌“十二木卡姆”中“第一木卡姆”中“拉克木卡姆第1首”[6]1的原文如下:


譯文如下:
第三達斯坦
未曾遠途他鄉,便不明了那故鄉的連綿。
未曾遇見心眼兒壞的人,就不知那善良與真情的高貴。
不將你擁入我的懷里,我的情人!活下去,將毫無意義。
倘若沒有日月可鑒的溫柔,將無從知曉戀人的真情。
這世上的災難是那稻田的荒廢,
哈臺杯一定要看看,怎樣醫治那里的悲傷!
有了情人的心就感覺不到貼切的悲傷,
榮耀的死去也并非是失敗的離世!
沒有愛情火焰來炙烤這顆心啊!
怎能有面對面透明的心扉!
凌亂的頭發不曾垂到腰間,
就很難流露出乞討悲涼那般模樣。
不曾用生命來展露這世間愛情的人兒,
哪里會有癡情的綿綿語篇!
我阿巴斯坦不知曉,
也未曾輕問過端詳,
愛情的火焰啊!就不曾散落我的發梢,
然怎會明了愛情那平凡而震撼的力量!
存在于維吾爾傳統詩歌特別是民歌中的維吾爾現代化詩歌的最早藝術因子呈現于各個方面,比如詩歌的“像”“意”“言”“情”“境”“風格”“流派”“題材”“結構”等各個方面。就僅僅從朦朧詩的“朦朧”這一個視角來看,與20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產生的漢語朦朧詩的“朦朧”很相似的是,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產生的維吾爾朦朧詩,其朦朧的風格特色也體現在維吾爾民歌“十二木卡姆”中“第一木卡姆”中“拉克木卡姆的第2首”*阿布都肉蘇里·吾馬爾、李春華(編):《太孜》,出自于阿布都肉蘇里·吾馬爾、李春華(編):《維吾爾十二木卡姆[第一木卡姆:拉克木卡姆第2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頁。中 ,詩文如下:
太孜
我做了一件善事反而帶來了上百個煩惱,我未見成百個回報反而遭受數千次嘲笑。
為生活我已將生命完全置之度外,也未見千萬人用鋼針刺向我的心房。
一旦你心中的愛情被你心愛的人知曉,也未見對每一個愛回敬一百個煩惱的人受到惡報。
我不服的把白眼仁和黑眼珠投向八方,它們在這個世界上的作用能差多少。
啊,朋友,請不要對美人們抱任何希望,因為我從她們的美麗中什么也得不到。
在這兩首維吾爾民歌中,雖然第一首是對愛慕女子的愛的表達,第二首是對自己愛而不得受傷害的表達,但是都是以一種比較朦朧的方式來表達。
可見,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在維吾爾民歌《其曼迪姑》或者比《其曼迪姑》更早年代的一大批維吾爾民歌中,早就蘊含了維吾爾詩歌中的朦朧因子。所以,到了維吾爾新時期朦朧詩的繁榮期,許多維吾爾朦朧詩如《飛石》《喀什噶爾的地球》《流浪人》《群鳥》《無人》《鹽的頌歌》《五指》《平安》《愛的旅途》《無月的月光》《詩人與夜》《驛站》《在這里》《寬容的人》《孤獨的樹》《疲倦》《寫給姑娘的三首詩》《世紀之歌》《野蠻》《女人》《赤裸》《五和七之間》《父親》《光的傳說》《佳人的芳香》、《靈床》《我是牧羊娃手中的笛》《鄙棄》《獻給蒼天的詩》《真理》等等,都有著維吾爾民歌《其曼迪姑》或者更早時期傳唱的維吾爾民歌的某種遺傳因子。
實際上,維吾爾現代化詩歌對于維吾爾傳統民歌的繼承與延續,不僅僅體現在“朦朧”這個因子上,而是體現在維吾爾詩歌的各個方面,諸如意象、意境、語言、風格、格式、押韻、節奏、結構、修辭等。在維吾爾傳統民歌中,經常運用的藝術手法比如明喻、暗喻、隱喻、象征、暗示、通感、反諷、夸張、反復、蒙太奇等多種手法,都被維吾爾現代詩歌極大地放大與集中,從而形成了密集、多變、繁復的朦朧詩創作技巧。
僅就風格而言,維吾爾傳統民歌中,個體傷痕的傾訴,集體經驗的表達,內斂含蓄的抒情,莊嚴自持的情緒,甚至浪漫主義與象征主義的表現形式,都成為現代維吾爾朦朧詩的主要表達方式。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維吾爾新時期朦朧詩中存在的一種與漢語朦朧詩截然不同的異域性與神秘感,也是從維吾爾傳統詩歌特別是維吾爾民歌中一脈相傳下來的,那就是一種宗教情結與宗教氛圍,這種朦朧的帶有一種西域文化境界下的神圣的宗教感情與天山下的純凈自然靈性,根本不是從漢語詩歌中借鑒來的,而是源自于維吾爾民族自身與維吾爾詩歌自身。
綜上所述,維吾爾現代化詩歌的語義,可以溯源于維吾爾本民族語言的獨特語境中去,不能隨便以漢語的語境理解取而代之。維吾爾現代化詩歌的風格,可以溯源于維吾爾傳統詩歌特別是維吾爾族的民歌發展變遷中,并不是簡單地從漢語詩歌中嫁接移植。
參考文獻:
[1] 胡適.嘗試集[M].上海:上海亞東圖書館,1920.
[2] 博格達·阿布都拉.烏鴉的傳說[M]//蘇德新.一束光流過時間的痕跡.蘇德新,譯.北京:中國文化出版社,2010.
[3] 尼米希依提.尼米希依提詩歌精選[M].狄力木拉提·泰來提,譯.烏魯木齊: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11.
[4] 甫拉提·艾吾祖拉.鳥[M]//阿比布拉.飛石.安尼瓦爾,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5] 馮至.昨日之歌[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6] 阿布都肉蘇里·吾馬爾,李春華.第三達斯坦[M]//阿布都肉蘇里·吾馬爾,李春華.維吾爾十二木卡姆.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責任編輯馬俊】
Uyghur Traditional Roots of Modern Poetry
WANG Ming-ke, WANG Yuan, Abdunasir Ablat
(Humanities College, University of Kashgar, Kashgar 844008, China)
Abstract:The Uyghur modern poetry is rooted in Uyghur language and the semantic image brewing context and origin in terms of nationality reflects the unique roots of different Chinese semantic meaning. The origin of the Uyghur modern poetry art factors exist in the earliest Uyghur traditional poetry, Uyghur misty poetry in the new period factor is the earliest art originated in the Uyghur folk songs and poems for the long term development. From folk songs to traditional poetry to modern poetry includes the misty poetry, art factor during genetic exist, has been not grafting was borrowed or from the Chinese poetry.
Key words:Uyghur poetry; modernization; traditional
中圖分類號:I05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9-5128(2016)11-0063-05
收稿日期:2015-04-10
基金項目: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普通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喀什大學維吾爾優秀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研究中心重點項目:維吾爾傳統文化的現代化研究(XJEDU070215B03);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現代性語境下維吾爾詩歌研究新視野——以維吾爾新時期詩歌為例(2015BZW075)
作者簡介:王明科(1973—),男,甘肅莊浪人,喀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文學博士,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王媛(1985—),女,江蘇連云港人,喀什大學人文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研究;阿不都納·斯爾阿卜來提(1988—),男(維吾爾族),新疆喀什人,喀什大學人文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研究。
【語言文化與文學研究】
——評《中國現代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