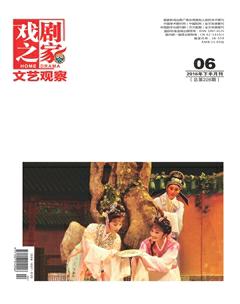日本的“曖昧”文化
肖征
【摘 要】美國語言哲學家格賴斯提出的語用學的合作原則,包括量、質、關系、方式四個方面。為了保證會話的順利進行,要求人們在日常交際中要遵循此原則。但實際上并不是所有語言、所有國家的人都能按照這一原則進行交際,日本便是其中的一個。他們在對話中往往采取一種含蓄、內斂的說話方式,雖然這一原則與格賴斯提出的原則背道而馳,但日本人這種獨特的表達方式形成了有日本特色的“曖昧”文化。 【關鍵詞】合作原則;日本人;委婉;曖昧;文化中圖分類號:H3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6)06-0278-03美國語言哲學家格賴斯認為:人們的言語交際要遵循某個一般原理,會話的開展有必要服從一些特定的準則和相應的次準則,它們分屬于量、質、關系、方式四個不同的范疇。量的準則就是要與應提供的信息量有關,其中包括所說的話應提供符合交談目的需求的信息和所說的話不應提供超出需要的信息;質的準則包括一個上位準則和一個下位準則。上位準則要求“說真話”,下位準則要求不說自知虛假的話和不說缺乏足夠證據的話;關系準則即所說的話應該是相關的;方式準則包括一個上位準則和一個下位準則,上位準則要求“說話要清楚明白”,下位準則要求說話避免晦澀、歧義,要簡練、有條理。但是,在實際交際中,受國家、文化、語言的影響,人們并不都能遵守合作原則,有時也會違反這一原則。日本人在這一方面表現的尤為明顯,在講話中就常常違反格賴斯的合作原則,而正是違反了這一原則,恰恰體現出日本獨特的“曖昧”文化。一、違反“量”的準則“量”的準則要求我們不說無用的話,不贅述。由于日本屬于單一民族國家,在語言溝通方面彼此之間沒有隔閡,所以他們可以在具體的語境中憑借推斷、猜測來準確理解對方的意圖。因此他們往往不必將話說的足夠透徹,而聽者卻能夠根據當時的情景和氛圍準確捕捉到對方的意思。例1:《東京愛情故事》中男主角完治剛剛到達東京,和女主角的對話。莉香:どうした?元気ないなあ、聲に。完治:そうですか。莉香:八月三十一日の小學生みたい。なんか東京にいやなことでもあるの?完治:それはやっぱ不安ですよ。愛媛から一人出てきて東京で何かあるか分からないし。——電視劇《東京ラブストーリ》在上述對話中,沒有出現過一處直接、正面回答的句子。莉香詢問完治“怎么了,聽你聲音好像沒有什么精神。”而完治并沒有直接說明自己沒有精神的理由,而是用日本人經常使用的附和語“そうですか”附和莉香說的話。而緊接著,莉香也沒有直接問“你到底怎么了”之類的問題,而是又含蓄地問道“難道在東京有什么令你討厭的事嗎”,這時候,完治還是沒有做出正面回答“是”或者“不是”,而是委婉的表達了自己內心的想法“愛媛から一人出てきて東京で何かあるか分からないし”。這幾句話中沒有一處是直接的、正面的回答,全都是用一種“兜圈子”的方式作出的回答。這種說話方式顯然是超出了聽者需要的信息的范圍,但聽話人卻準確地揣測到了說話人的意圖,即完治確實是有心事的。正是這一來一回的“拉鋸式對話”才使交流能夠按照日本人的方式順暢地進行下去,想必這種繞來繞去的對話只有日本人才能夠“獨享”,但正是這種獨特的表達方式才成就了日本人獨有的“曖昧”文化。例2:《東京愛情故事》中,完治剛剛安頓下來給高中同學三上打電話。完治:あのさ、三上、來るよね、同窓會。三上:あ。完治:あいつもくるか。三上:ええ?誰?完治:いや、ほら、あのう、安西とかさ、関口とか。三上:ああ、関口ね、來るんじゃないのかなあ。——電視劇《東京ラブストーリ》完治詢問三上“同學會上你會來的吧”,接著又吞吞吐吐的問“她來嗎”,這時不知所云的三上問“你說的是誰”。其實完治喜歡高中同學關口,所以他想問的是關口會不會來,但因為不好意思所以順便提了別人的名字“安西啊,關口啊,他們這些人”。作為高中同學的三上還是了解完治的用意的,所以在回答時只提到了關口的名字“啊,你說關口啊,不是會來嗎”。在這組對話中,雖然完治啰里啰唆的說了別人的名字,這種說話方式也是超出了聽話人需要的范疇,但三上還是能從對方的話語中,以及當時的語言環境中聽出來完治想要表達的意思。這種委婉的表達方式完美的詮釋了日本人的“曖昧”文化。二、違反“質”的準則“質”顧名思義即“質量”,格賴斯的“質”的原則要求不說自知虛假的話,不說缺乏足夠證據的話。但有時說話人為了使自己的語言更加委婉,達到自己交際的目的故意說一些自知虛假的話,違反這一原則。例3:黒:ところが御めえいざってえ段になると奴め最後っ屁をこきゃがった。臭え…の臭くねえのってそれからってえものはいたちを見ると胸が悪くならあ。吾輩:しかし鼠なら君に睨まれては百年目だろう。君はあまり鼠を捕るのが名人で鼠ばかり食うものだからそんなに肥って色つやが善いのだろう。「吾輩は貓である」夏目漱石——《我是貓》于雷譯當“我”聽到大黑講述他自己捕捉黃鼠狼時的情形時,“我”便奉承他“不過,老鼠嘛,只要仁兄瞪它一眼,它就小命玩完。您捕鼠可是個大大的名家,就因為凈吃老鼠,才胖的那么滿面紅光的吧”。其實這并不是“我”內心的真實想法,當時“我”為了和大黑混熟,故意奉承大黑說了謊話,目的就在于使自己的話讓大黑喜歡聽,達到奉承他的效果。這明顯違背了“質”的準則,卻達到了交際的目的。例4:完治給高中同學三上打電話時。三上:ああ、永尾。完治:今、こっちついたから。なんで今電話出たら。三上:貓だよ。完治:お前の內の貓、電話出るのか。あ、いや、あのさ…在三上家接電話的本來是一個女人,完治也聽到了是一個女人的聲音,然后問三上“為什么才接電話”,三上卻說謊回答說“剛剛是貓”。完治聽出來了對方搪塞的話,于是不再繼續追問下去,因為他從高中時候就知道三上每天過著夜夜笙歌的生活,為了不使對方太尷尬,完治故意將話題一轉,開始問三上同學聚會的事情。三上說了假話應付完治,而完治明知道三上在說謊,為了緩和氣氛也就順著三上的話。其實在完治心里已經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卻還是故意將話題岔開。兩個人都言不由衷,沒有把話說破,這違背了“質”的準則,但這種聊天方式恰恰符合日本的“曖昧”文化。格賴斯的“質”的準則還要求我們不說謊話,但有時候說話人為了對方著想,使自己說的話不至于給對方造成傷害,故意說謊話來使對方樂于接受,同時也表達自己恭敬的態度。例5:A:今夜は大したおもてなしもできませんが、日本の秋の味覚を楽しんで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して、和食をご用意いたしました。お口に合えばよろしいのですが。B:それはありがたいですね、いま中國でも、健康に良いということで和食は大変なブームになっています。今夜はぜひ本場の味をじっくり堪能したいものです。——《實用日語同聲傳譯教程》A這方準備了豐盛的晚宴來招待B這一方的人員,但是在講話時,故意將自己這方準備的晚宴說成“沒有準備什么豐盛的菜肴,只是為了讓大家品嘗一下日本秋季的風味”。其實A這一方肯定是非常用心地為B這一方準備菜肴,但是如果說成是“為大家準備了豐盛的晚宴”就會有一種施惠于人的感覺。日本人出于對對方的考慮,使對方樂于接受自己,也為了表達出自己這一方的禮貌、恭敬的態度,故意說假話,正是日本人這種違背“質”的準則的表達方式使交際更加圓滑,更加順暢。三、違反關系準則關系準則要求所說的話應該是相關的。而日本人有時會故意講一些和對話內容無關的話,還是以《東京愛情故事》中,莉香向完治表白為例。例6:《東京愛情故事》中,莉香向完治表白。莉香:完治。完治:何?莉香:完治。完治:なんだよ。莉香:完治。完治:だから何?莉香:完治、好き。言っちゃった、悔しやな。完治:な、何言ってるんだっけ?莉香:お休み。完治:ちょっと待ってよ。——電視劇《東京ラブストーリ》在此對話中,莉香連叫了幾聲完治的名字,直到叫到第三次的時候才說“完治,我喜歡你”。莉香并沒有單刀植入的告訴完治自己喜歡他,而是通過這種違反關系準則的方式緩沖自己的想法。而說完“喜歡”之后,當完治問她“你剛剛說什么”的時候,莉香避開剛才的話題不談,對完治說“晚安”來緩解自己尷尬的處境。而這時的完治其實早已經聽到了莉香對自己的表白,為了避免直接回答莉香的話,才問“你剛剛說什么”。兩個人的對話至始至終都在違背關系準則,一問一答的對話雖然聽上去關系并不大,但由于雙方都是在這種曖昧文化背景下成長的,所以,即使雙方都違背了關系準則,雙方也都能很好的理解對方真實的想法。四、違反方式準則方式原則要求我們在說話中要清楚明白,語言要簡練。但在日本人的表達習慣當中往往是“曖昧”的,含糊的,在談話中他們故意采用一種“啰嗦”的說話方式來緩和語氣,委婉又不生硬的表達自己的觀點。例8:A:週末に、一緒に映畫を見に行こう。B:いきたいんだけど、ちょっと。A邀請B一起去看電影,B沒有直截了當的拒絕A,而是含糊地說“我很想去,但是”。其實B心里已經決定不跟A去,但考慮到A的感受,沒有直接拒絕對方,而是通過違反方式準則的方法圓滑地表達了自己的意愿。這樣比起直接拒絕對方要更容易使對方接受這個事實,同時A也能夠理解對方的意思,心里落差不至于太大,通過這種“曖昧”的方式達到了融洽溝通的目的。但這種違反方式準則的做法在跨文化交際中會容易產生摩擦。例如,在20世紀80年代時,中國人想要去日本留學的話,需要日本人作保人,這時,如果日本人不愿意答應這件事,會委婉地說“ちょっと”,其實就是拒絕的意思。但在中國人看來,這句話的意思是還有商量的余地,于是,不停地請求日本人答應。而這時日本人會覺得這個中國人很沒有禮貌。其實,在這里兩種文化之間已經形成了誤解。五、結語綜上所述,得出的結論是,日本人違反語用學的合作原則有時是為了內斂、含蓄地表達自己的想法,有時是為了達到交際的目的、調節談話氛圍,有時則是為了表達自己恭敬的態度。無論出于何種目的,總的來看,日本人的言語中都透露著一種“曖昧”語氣,體現出一種“曖昧”文化。這種“曖昧”文化雖然違背了格賴斯的合作原則,但在語言單一、文化單一的日本社會,卻能夠使他們彼此之間沒有交流障礙,可以圓滑、順暢地達到交際的目的。但是,其它語言、文化不同的民族可能會對這種“曖昧”語言產生誤解,從而產生交流上的障礙。因此,作為我們外國學習者來說要了解、學習日本的這種“曖昧”文化,降低交流成本,融洽溝通。參考文獻:[1]孟瑾.日語語用學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2]翟東娜.日語語言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3]于雷.我是貓[M].江蘇:譯林出版社,2010.[4]夏目漱石.吾輩は貓である[M].日本:新潮社,2003.[5]塚本慶一.實用日語同聲傳譯教程[M].大連: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2005.[6]姚俊元.談談日語的曖昧性[J].日語學習與研究,1986(4).[7]孫秀秀.附和語そうですか的語用功能淺析[J].日語教學與日本研究,2005(00).作者簡介:肖 征(1990-),女,河北保定人,上海理工大學外語學院研究生,碩士,研究方向:日語筆譯、商務日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