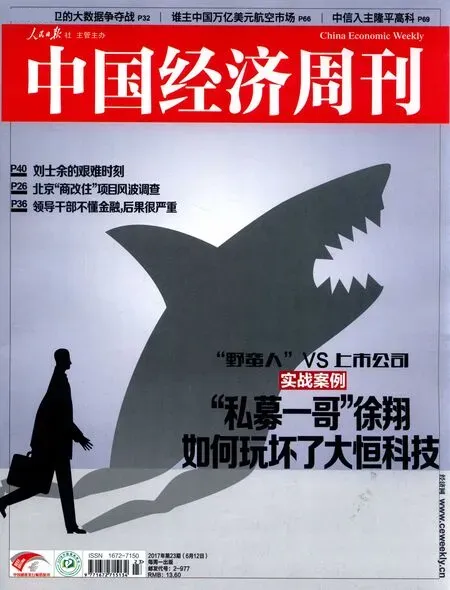不要給“濫用職權(quán)”蓋上“濫用強(qiáng)制手段”的遮羞布
沿著被撕褲管裸露的不僅是律師卑微的大腿,還有暴力執(zhí)法粗俗的胸肌及個(gè)別法院工作人員的隨心所欲。
新聞背景

2016年6月3日,廣西國(guó)海律師事務(wù)所吳良述律師到南寧市青秀區(qū)人民法院申請(qǐng)立案期間,與該院工作人員發(fā)生爭(zhēng)執(zhí),引起社會(huì)廣泛關(guān)注。吳良述律師穿戴整齊地走進(jìn)法院,最后破破爛爛地走出來(lái)。
事發(fā)后,南寧市有關(guān)部門高度重視并組成聯(lián)合調(diào)查組進(jìn)行事件調(diào)查。調(diào)查結(jié)果稱,這起事件系律師到法院立案過(guò)程中因法警濫用強(qiáng)制手段引發(fā)的事件。
對(duì)于這一事件的性質(zhì)及應(yīng)該如何處理,各界人士表達(dá)了不同觀點(diǎn)和建議。
近日,南寧官方公布“律師在法院信訪室被打”事件調(diào)查結(jié)果,確認(rèn)本起事件系律師到法院立案過(guò)程中因法警濫用強(qiáng)制手段引發(fā)的事件,并強(qiáng)調(diào)事件過(guò)程中不存在毆打吳良述律師行為。有關(guān)方面還指出,根據(jù)現(xiàn)場(chǎng)監(jiān)控視頻顯示,法警對(duì)吳良述律師所實(shí)施的搶奪手機(jī)(導(dǎo)致其褲子被扯爛)、背后控制、關(guān)門、放倒在地、腳踏胸口等動(dòng)作,發(fā)生在一分鐘之內(nèi),目的是為了強(qiáng)制檢查其手機(jī)內(nèi)有無(wú)未經(jīng)準(zhǔn)許的錄音錄像,且法警在拿到手機(jī)后立即松開對(duì)吳良述的控制,并沒(méi)有傷害的故意,不屬于毆打。
“毆打”一詞出現(xiàn)在《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規(guī)范用語(yǔ)中,是指行為人公然實(shí)施的損害他人身體健康的打人行為。行為方式一般采用拳打腳踢,或者使用棍棒等器具毆打他人。筆者沒(méi)有看到視頻資料,無(wú)法判斷法警在一分鐘內(nèi)實(shí)施的搶奪手機(jī)(導(dǎo)致其褲子被扯爛)、背后控制、關(guān)門、放倒在地、腳踏胸口等動(dòng)作是否符合這個(gè)特征。
但從另一個(gè)角度來(lái)看,毆打是指行為人以傷害他人身體為主觀故意,利用踢肢體或工具直接施加于受害人身體且即時(shí)發(fā)生作用力的行為。很明顯,南寧方面的解釋是很專業(yè)的,其精準(zhǔn)地從主觀性角度撇開了對(duì)吳良述律師“毆打”之嫌。不過(guò),我們也注意到公布內(nèi)容中還使用了這樣一個(gè) “濫用強(qiáng)制手段”的非法律術(shù)語(yǔ),如果按照有關(guān)學(xué)理解釋,強(qiáng)制手段可以解讀為人民警察在執(zhí)行職務(wù)過(guò)程中為制止違法犯罪所采取的各種制服措施,是警察的職務(wù)行為。
就這一解釋,有這樣幾個(gè)關(guān)鍵詞值得關(guān)注:“人民警察”“執(zhí)行職務(wù)”“制止違法犯罪”“職務(wù)行為”。
首先,司法警察也是人民警察的警種之一,其主體是符合以下條例的。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條例》第二條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人民警察的警種之一。
其次,本次事件中,涉事司法警察是在“執(zhí)行職務(wù)”嗎?
對(duì)于司法警察的職責(zé),《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條例》有極其嚴(yán)格的規(guī)定和完整的列舉。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條例》第七條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職責(zé):(一)維護(hù)審判秩序;(二)對(duì)進(jìn)入審判區(qū)域的人員進(jìn)行安全檢查;(三)刑事審判中押解、看管被告人或者罪犯,傳帶證人、鑒定人和傳遞證據(jù);(四)在生效法律文書的強(qiáng)制執(zhí)行中,配合實(shí)施執(zhí)行措施,必要時(shí)依法采取強(qiáng)制措施;(五)執(zhí)行死刑;(六)協(xié)助機(jī)關(guān)安全和涉訴信訪應(yīng)急處置工作;(七)執(zhí)行拘傳、拘留等強(qiáng)制措施;(八)法律、法規(guī)規(guī)定的其他職責(zé)。
可見,從本次事件發(fā)生的場(chǎng)景來(lái)看,涉事司法警察不屬于嚴(yán)格意義上的《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條例》第七條所列舉的執(zhí)行職務(wù)范疇。那么,涉事司法警察又是基于什么實(shí)施了涉事強(qiáng)制手段呢?從公布的內(nèi)容可知,其依據(jù)的是《最高院關(guān)于依法維護(hù)人民法院申訴信訪秩序的意見》(簡(jiǎn)稱 《意見》)。
《最高院關(guān)于依法維護(hù)人民法院申訴信訪秩序的意見》
人民法院申訴信訪場(chǎng)所由司法警察執(zhí)勤,負(fù)責(zé)維護(hù)秩序和安全。
第七條 申訴信訪場(chǎng)所應(yīng)當(dāng)配備物品寄存設(shè)施,申訴信訪人員,應(yīng)當(dāng)將所攜帶的具有拍照、錄音、錄像功能的設(shè)備予以寄存。未經(jīng)準(zhǔn)許拍照、錄音、錄像的,司法警察應(yīng)當(dāng)予以制止,刪除拍錄內(nèi)容,并可以對(duì)行為人予以訓(xùn)誡。
第十五條??人民法院訴訟服務(wù)中心工作秩序的維護(hù),適用本意見。
可以說(shuō),涉事司法警察在當(dāng)時(shí)涉事場(chǎng)所據(jù)以該《意見》規(guī)定,的確又屬于司法警察“執(zhí)行職務(wù)”的范疇。但問(wèn)題是,本事件涉事司法警察執(zhí)行職務(wù)的依據(jù)不是《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條例》而是《最高院關(guān)于依法維護(hù)人民法院申訴信訪秩序的意見》,這兩個(gè)規(guī)范又有什么不同呢?
我國(guó)的法律倫理是這樣的:一、憲法;二、全國(guó)人民代表大會(huì)制定的基本法律;三、全國(guó)人大常委制定的除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四、國(guó)務(wù)院制定的行政法規(guī);五、地方性法規(guī)和部門規(guī)章;六、地方政府規(guī)章。因此,從這一角度來(lái)看,上述《條例》和《意見》的效用是不同的。
所謂條例,是國(guó)家權(quán)力機(jī)關(guān)或行政機(jī)關(guān)依照政策和法令而制定并發(fā)布的,針對(duì)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等各個(gè)領(lǐng)域內(nèi)的某些具體事項(xiàng)而作出的,比較全面系統(tǒng)、具有長(zhǎng)期執(zhí)行效力的法規(guī)性公文。條例是法的表現(xiàn)形式之一。它具有法的效力,是根據(jù)憲法和法律制定的,是從屬于法律的規(guī)范性文件。
所謂意見,是上級(jí)領(lǐng)導(dǎo)機(jī)關(guān)對(duì)下級(jí)機(jī)關(guān)部署工作,指導(dǎo)下級(jí)機(jī)關(guān)工作活動(dòng)的原則、步驟和方法的一種文體。它不具有法的效力,意見的指導(dǎo)性很強(qiáng),有時(shí)是針對(duì)當(dāng)時(shí)帶有普遍性的問(wèn)題發(fā)布的,有時(shí)是針對(duì)局部性的問(wèn)題而發(fā)布的,意見往往在特定的時(shí)間內(nèi)發(fā)生效力。
然而,涉事司法警察卻根據(jù)該《意見》實(shí)施了“搶奪手機(jī)(導(dǎo)致其褲子被扯爛)、背后控制、關(guān)門、放倒在地、腳踏胸口等強(qiáng)制手段”,這些行為不僅侵犯了他人身體,還限制了其人身自由。我國(guó)《行政處罰法》《立法法》早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授權(quán),只能由法律設(shè)定”的規(guī)定。所以,該《意見》無(wú)權(quán)賦予司法警察實(shí)施上述行動(dòng)。
再次,涉事司法警察是不是在“制止違法犯罪”呢?明顯不是!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條例》第三條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任務(wù)是預(yù)防、制止和懲治妨礙審判活動(dòng)的違法犯罪行為,維護(hù)審判秩序,保障審判工作順利進(jìn)行。
首先我們知道了,事件發(fā)生在非審判區(qū)域的信訪辦公室,不是在審判活動(dòng)中進(jìn)行任何不當(dāng)行為。退一步講,即使該信訪人在該信訪辦公室發(fā)生了錄音錄像的行為,也絕不是法律意義上的違法犯罪行為。
最后,這一次事件中的司法警察所實(shí)施的行為是不是“職務(wù)行為”?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條例》第二十八條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必須執(zhí)行上級(jí)的決定和命令。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認(rèn)為決定和命令有錯(cuò)誤的,可以按照規(guī)定提出意見,但不得中止或者改變決定和命令的執(zhí)行;提出的意見不被采納時(shí),必須服從決定和命令;執(zhí)行決定和命令的后果由作出決定和命令的上級(jí)負(fù)責(zé)。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對(duì)超越法律、法規(guī)規(guī)定的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職責(zé)范圍的指令,有權(quán)拒絕執(zhí)行,并同時(shí)向上級(jí)機(jī)關(guān)報(bào)告。
對(duì)審判長(zhǎng)、獨(dú)任審判員指令的執(zhí)行,依照前款規(guī)定。
非常明顯,涉事司法警察是在法院的領(lǐng)導(dǎo)指揮下履行其職務(wù)。因?yàn)樯霞?jí)的“決定”和“命令”就是他的行動(dòng)驅(qū)使。但是,該條款同時(shí)又規(guī)定:“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對(duì)超越法律、法規(guī)規(guī)定的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職責(zé)范圍的指令,有權(quán)拒絕執(zhí)行,并同時(shí)向上級(jí)機(jī)關(guān)報(bào)告”。遺憾的是,涉事司法警察不僅沒(méi)有啟動(dòng)這一正義的救濟(jì)程序,反而肆無(wú)忌憚地加以發(fā)揮,直至造成惡劣后果。
顯然,涉事司法警察在這一事件中,所實(shí)施的并不能簡(jiǎn)單地歸結(jié)為“濫用強(qiáng)制手段”而一語(yǔ)以蔽之。在法律上,它是一種典型的濫用職權(quán)的違法行為。
從事件過(guò)程到結(jié)果,涉事司法警察明顯違反了法律規(guī)定的權(quán)限和程序,屬于濫用職權(quán)。雖然公布中為其辯解了沒(méi)有“毆打”他人的故意,但是,濫用職權(quán)的故意是明顯的。應(yīng)當(dāng)予以懲處。
不要誤會(huì)了自己,司法警察并不是公安警察
嚴(yán)格意義講,發(fā)生在法庭之外的違法犯罪活動(dòng),司法警察只具有約束權(quán),限于訓(xùn)誡、制止、控制等處置措施和保存相關(guān)證據(jù)范疇。其他權(quán)力應(yīng)歸于公安機(jī)關(guān)的人民警察管轄并行使。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條例》第十三條有明確的規(guī)定:對(duì)嚴(yán)重?cái)_亂人民法院工作秩序、危害人民法院工作人員人身安全及法院機(jī)關(guān)財(cái)產(chǎn)安全的,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應(yīng)當(dāng)采取訓(xùn)誡、制止、控制等處置措施,保存相關(guān)證據(jù),對(duì)涉嫌違法犯罪的,及時(shí)移送公安機(jī)關(guān)。
法院的司法警察和公安警察有著明顯區(qū)別和不同的分工。法院司法警察的主要職責(zé)是:1.警衛(wèi)法庭、維持審判秩序;2.負(fù)責(zé)傳帶證人、鑒定人、傳遞證據(jù)材料;3.送達(dá)法律文書;4.執(zhí)行傳喚、拘傳、拘留;5.提解、押送、看管被告人或者罪犯;6.參與對(duì)判決、裁定的財(cái)產(chǎn)查封、扣押、凍結(jié)或沒(méi)收;7.執(zhí)行死刑;8.法律、法規(guī)規(guī)定的其他職責(zé)。
公安機(jī)關(guān)的人民警察按照職責(zé)分工,主要職責(zé)是:1.預(yù)防、制止和偵查違法犯罪活動(dòng);2.維護(hù)社會(huì)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會(huì)治安秩序的行為;3.維護(hù)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處理交通事故;4.組織、實(shí)施消防工作,實(shí)行消防監(jiān)督;5.管理槍支彈藥、管制刀具和易燃易爆、劇毒、放射性等危險(xiǎn)物品;6.對(duì)法律、法規(guī)規(guī)定的特種行業(yè)進(jìn)行管理;7.警衛(wèi)國(guó)家規(guī)定的特定人員,守衛(wèi)重要的場(chǎng)所和設(shè)施;8.管理集會(huì)、游行、示威活動(dòng);9.管理戶政、國(guó)籍、入境出境事務(wù)和外國(guó)人在中國(guó)境內(nèi)居留、旅行的有關(guān)事務(wù);10.維護(hù)國(guó)(邊)境地區(qū)的治安秩序;11.對(duì)被判處管制、拘役、剝奪政治權(quán)利的罪犯和監(jiān)外執(zhí)行的罪犯執(zhí)行刑罰,對(duì)被宣告緩刑、假釋的罪犯實(shí)行監(jiān)督、考察;12.監(jiān)督管理計(jì)算機(jī)信息系統(tǒng)的安全保護(hù)工作;13.指導(dǎo)和監(jiān)督國(guó)家機(jī)關(guān)、社會(huì)團(tuán)體、企業(yè)事業(yè)組織和重點(diǎn)建設(shè)工程的治安保衛(wèi)工作,指導(dǎo)治安保衛(wèi)委員會(huì)等群眾性組織的治安防范工作;14.法律、法規(guī)規(guī)定的其他職責(zé)。
可往往在執(zhí)法活動(dòng)中,司法警察忽略了《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條例》職責(zé)限制,越權(quán)行使警察權(quán)力,造成了執(zhí)法錯(cuò)位、濫用職權(quán)的悲劇后果。因此,對(duì)于本次事件,筆者不認(rèn)為涉事司法警察具有任何正當(dāng)性可言。
立案給憑據(jù),法官你怕什么?
聯(lián)合調(diào)查組提出了5點(diǎn)處理意見:一是青秀區(qū)人民法院向吳良述律師公開賠禮道歉,并賠償損失。二是青秀區(qū)人民法院依法向吳良述律師出具接收立案材料的憑證,并依法及時(shí)告知立案審查結(jié)果。三是南寧市中級(jí)人民法院?jiǎn)?dòng)責(zé)任調(diào)查程序,依照有關(guān)規(guī)定追究相關(guān)人員責(zé)任,并向社會(huì)通報(bào)結(jié)果。四是青秀區(qū)人民法院嚴(yán)格落實(shí)立案登記制度,進(jìn)一步改進(jìn)工作作風(fēng)。五是青秀區(qū)人民法院依法保障律師執(zhí)業(yè)權(quán)利及合法權(quán)利。
特別是補(bǔ)開立案憑證,即老百姓通常理解的“收據(jù)”,是本次事件的根源,也是一個(gè)不容忽視的立案難的共性問(wèn)題。筆者認(rèn)為,立案法官收取立案材料后不出具憑證是嚴(yán)重瀆職行為,是在濫用司法權(quán)力,必須予以懲戒。
為保護(hù)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依法行使訴權(quán),實(shí)現(xiàn)人民法院依法、及時(shí)受理案件,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民事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行政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刑事訴訟法》等法律規(guī)定,2015年4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經(jīng)過(guò)其審判委員會(huì)第1647次會(huì)議,通過(guò)了《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人民法院登記立案若干問(wèn)題的規(guī)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人民法院登記立案若干問(wèn)題的規(guī)定》
第一條 人民法院對(duì)依法應(yīng)該受理的一審民事起訴、行政起訴和刑事自訴,實(shí)行立案登記制。
第二條 對(duì)起訴、自訴,人民法院應(yīng)當(dāng)一律接收訴狀,出具書面憑證并注明收到日期。
對(duì)符合法律規(guī)定的起訴、自訴,人民法院應(yīng)當(dāng)當(dāng)場(chǎng)予以登記立案。
對(duì)不符合法律規(guī)定的起訴、自訴,人民法院應(yīng)當(dāng)予以釋明。
第十三條 對(duì)立案工作中存在的不接收訴狀、接收訴狀后不出具書面憑證,不一次性告知當(dāng)事人補(bǔ)正訴狀內(nèi)容,以及有案不立、拖延立案、干擾立案、既不立案又不作出裁定或者決定等違法違紀(jì)情形,當(dāng)事人可以向受訴人民法院或者上級(jí)人民法院投訴。
人民法院應(yīng)當(dāng)在受理投訴之日起十五日內(nèi),查明事實(shí),并將情況反饋當(dāng)事人。發(fā)現(xiàn)違法違紀(jì)
行為的,依法依紀(jì)追究相關(guān)人員責(zé)任;構(gòu)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zé)任。
就在《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人民法院登記立案若干問(wèn)題的規(guī)定》公布實(shí)施兩個(gè)月后的2015年6月9日上午10:00 ,最高人民法院在其新聞發(fā)布廳,高調(diào)向媒體和社會(huì)通報(bào)了全國(guó)法院實(shí)施立案登記制度進(jìn)展情況和成果。那是多么振奮人心的一個(gè)時(shí)刻。可是,又有誰(shuí)知道,一些基層法院卻將這一規(guī)定執(zhí)行得如此詭異,讓律師及其委托人像無(wú)頭蒼蠅一樣到處亂撞,直撞得頭破血流,大腿裸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