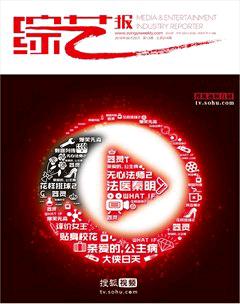編劇“痛并快樂著”
唐瀟霖
隨著近兩年影視行業投資熱興起、IP作品不斷被改編、網絡自制劇給行業帶來新活力等因素作用,編劇行業也日益受到重視。2016上海電視節舉辦多場編劇論壇,探討了編劇行業的生存現狀,以及如何深度開發、遴選優質版權IP。十余位著名編劇、投資方代表、影視策劃人參與討論,對編劇行業和IP作品改編提出了各自看法。
聚焦一:影視創作,改編好還是原創好
對于這一話題,眾多編劇看法不一。美國好萊塢高產編劇、派樂傳媒簽約編劇Steven(代表作《重擊者》《郵購新娘》《小鬼上路》)介紹,美國編劇更傾向原創作品,這樣擁有更多主動權。IP改編自由度小,必須嚴格按照原著中設定的角色與故事發展。“IP改編成功的關鍵在于制片人以及出品公司清楚地知道他們想要什么。改編最讓編劇抓狂的是,公司和出品方不清楚他們想要什么,買了一個IP后就像釣魚,改編完全碰運氣,可能喜歡也可能不喜歡,然后讓編劇不停地重新創作。”
編劇潘樸(代表作《武媚娘傳奇》《彼岸1945》)認為,創作者最大的樂趣仍然來自原創,構建了全新人物、故事后,會獲得巨大滿足感;編劇彭三源(《半路夫妻》《你是我兄弟》)也一直做原創,但她表示不拒絕改編,“編劇行業目前走到了史無前例的美好時代。不僅入行容易,而且行業有了空前的容量和寬容度。現在好像掀起了全民文化熱,微短片、網劇、大電影、電視劇、舞臺劇等,創作空間特別大,而且編劇的稿酬也提升了很多。現在對編劇的考量只有一個標準,那就是段位問題。”
編劇陳彤(代表作《離婚律師》《一仆二主》)把原創和改編比喻成生產和代孕,認為二者難度是一樣的;編劇陳文貴(代表作《鐵齒銅牙紀曉嵐》《小李飛刀》《趙氏孤兒案》)從自己的改編經驗得出結論,改編的創作難度不亞于原創;編劇李瀟(代表作《搭錯車 》《大丈夫》《小丈夫》)認為,能夠做好改編的編劇,需要擁有強大的自我喜好,要對作品有明確判斷。
聚集二:編劇如何看待反復修改劇本
李瀟認為,關鍵在于審稿意見是由誰提出,對于制片方、導演提出的修改意見,編劇一般愿意接受。但對于大牌演員自帶“門客編劇”提出的修改意見,編劇會非常抵觸。她奉勸年輕編劇不要去做這種工作,“影視劇是一個集體創作過程,無論如何不該本末倒置,把它變成為一個人量體裁衣,這種做法既害編劇又害演員。中國現在最缺的不是編劇和導演,而是好演員。在美國,某個角色想找名氣相近的演員,可能兩只手都數不過來,但中國好演員卻太少。我們的造星制度,全民追星的基礎,讓明星永遠只想演自己,其實是害了這個產業。”Steven補充說,美國確實也有“門客編劇”存在,但非常少見。
反復修改劇本更深層牽涉編劇話語權問題。彭三源認為,作為編劇,修改劇本是基本職業操守,一旦做到一流編劇,就會擁有更大話語權,會較少被要求修改劇本。有過制片人經歷的彭三源,對目前一些素質不高的編劇感觸頗深。她曾經遇到過拿出作品水平很差,又對修改意見無動于衷,并且不愿退還預付款的無良編劇。“編劇行業應該遵循公平交易原則,向這個方向靠攏后,整體水平才能上升一個臺階。”她表示。
聚焦三:為保持作品完整性,編劇是否轉行制作人
陳文貴表示,雖然編劇創作過程很痛苦,但也會快樂,比如突然想通一場戲后,那種興奮無可比擬。而制片人要做很多管理工作,所以不打算涉足。“編劇要從中尋找快樂,而不是為應付差事,這樣修改劇本才不會有抵觸心理。”
潘樸則希望嘗試制片人角色,他認為這是保護作品的最好方式。“在國內當制片人很辛苦,僅選演員就是件很可怕的事。我的性格也不是很適合做制片人,但我還是會嘗試往這個方向走。因為對畫面質感、色調等細節的追求,與其告訴別人如何修改,還不如親自動手。”沒有任何拍攝經驗的陳彤,談及自己入行時曾經鬧過笑話,她以為電視劇都是順拍,不知道是要打亂順序集中拍攝的。所以對于不懂的領域,她不會考慮涉足。
聚焦四:影視創作如何兼顧網臺聯動
隨著網劇快速發展,也給編劇行業帶來了諸多變化和沖擊。編劇、制片人白一驄(代表作《暗黑者 》《盜墓筆記》)認為,網劇讓編劇的創作生命延長了。“常規電視劇創作完成后,排檔需要等待很長時間。而網劇縮短了這種周期,使得等待時間縮短一半以上,這對于編劇創作非常利好。”
潘樸也認為,互聯網對創作帶來了良性促進,極大拓寬了影視作品類型,比如科幻劇、涉案劇等,讓編劇有更大的創作空間。而且年輕觀眾理解能力更強,對于多線索、交錯時空的情節很容易理解,這樣編劇在創作時更容易創新。
樂視網副總裁何鳳云表示,網劇使得電視劇產業開始去中心化,從而讓更多好作品得以露出,這也比較符合市場化的經濟規律。
克頓傳媒副總裁劉智表示,站在投資方角度看,項目投資首先考慮的是規避風險,IP作品是經歷過一次市場檢驗的,所以風險較低。“對于我們,80%以上的投資項目,會選擇IP作品為起點。”
聚焦五:影視作品是否需要強調網感
白一驄認為,“網感”其實是偽概念,它就是一些碎片化的點,精煉而觸動人心,能促使觀眾產生表達欲望。這在互聯網誕生之初,發帖、回評論時就存在了,十幾年來沒有改變過。“未來,當影視劇形成B2C模式后,作品直接面向受眾,那時的網感,會變得更加瑣碎、細致化。作品由受眾做出選擇,而不是由平臺來選擇。”
編劇饒俊(代表作《花千骨》《重生之巨星名流》)也表示反感“網感”一詞。“網感不是刻意添加的,其實就是尋找大眾的共鳴點。”潘樸稱,“網感一詞很虛幻,似乎存在但又很難抓住。我聽到網感,最容易聯想到的一個詞就是極致,另外就是互動性的用戶體驗。我覺得網感客觀存在,但盡量不要用這樣的思路指導創作,那樣會因為刻意迎合而失去用戶和作品靈魂。”
劉智認為,作品是否需要體現網感,取決于項目定位。“有些面向年輕觀眾的項目需要體現網感,但大多數時候投資方對項目的選擇還是看題材。首先考慮題材在政策上是否過關,不涉及民族問題、宗教信仰、色情、暴力等,這是公司負責人必須考慮的。其次看故事好不好,人物是否有突出特色。第三會考慮它的IP價值,能否做出爆品。什么能稱之為爆品?就是IP是否足夠大,引發的粉絲規模、熱議程度如何等,有一系列考察指標。所有對項目的選擇,都是在這三個維度指導下進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