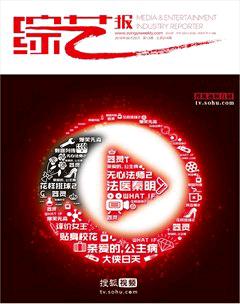《紙牌屋》不是算出來的,好故事是關鍵
趙國紅+陳丹

《綜藝報》:《紙牌屋》是由不同的編劇合作完成,創作過程中一共有幾位編劇,創作模式是什么樣的?不同編劇分工完成,如何能夠保證劇集風格的統一和劇情的緊密銜接?
John Mankiewicz:《紙牌屋》一共有五位編劇。創作每一季劇本的開始,大家都會聚在一起四五個月,將各個人物、話題、場景貼在黑板上,然后對它進行進一步討論。確定每季故事的大致走向和每集故事梗概之后,我們每人會輪流做執筆編劇把故事寫出來。每年我們都會創作大約9集的內容,在每一季工作結束后開啟下一季。
《綜藝報》:中國國內曾流傳一個說法,好萊塢編劇模式非常細化,有人專門負責情節、有人寫笑料、有人寫臺詞,所以這是一個謠傳嗎?
John Mankiewicz:據我所知,在電視劇的創作上并不存在這樣的情況。可能某位編劇會特別喜歡劇中的某一人物,那么他會著重進行這一人物的創作,但整一季劇集都是所有編劇相互協助完成的,并沒有某位編劇專職負責某一部分的創作模式。
《綜藝報》:《紙牌屋》令中國觀眾著迷的一點是,雖然故事虛構但卻讓人感覺非常真實,編劇在寫作劇本過程中,是怎樣把握真實和虛構邊界的?
John Mankiewicz:確實《紙牌屋》每一季發生的事件都跟現實生活非常接近,當然這些事件都是虛構的。編劇們在創作每一季故事時都會閱讀大量的新聞,咨詢很多專家以及政客。有很多真正參與政治生活的人是我們的劇集顧問。
《綜藝報》:《紙牌屋》生發于網絡,有一種說法,認為《紙牌屋》成功的原因是因為大數據的應用,你認可這種觀點嗎?
John Mankiewicz:我們對大數據并沒有特別關注。一部電視劇的走紅,關乎導演、演員,更關乎有創意、有深度的故事與講述故事的手法,但市場本身充滿了偶然性,并非數據能夠算出。
《綜藝報》:在中國,一些電視劇的生產和創作非常關注觀眾喜好,因此常出現題材跟風情況,美國編劇在創作中是否也有來自觀眾的壓力?
John Mankiewicz:當然,我們每部劇都試著讓觀眾喜歡,如果沒有觀眾的支持,劇集做出來也沒人看。但對一個創作者來說,你并不能真正找到觀眾喜歡看什么。Netflix會研究很多觀眾的行為和喜好,有時候Netflix會告訴我們觀眾喜歡劇中的哪個角色,觀眾喜歡的角色往往出乎我們的意料。
對于一個編劇來說,觀眾的喜好并不能帶來靈感,我們真正的創作動機只能是自己喜歡這個故事,同樣你也很難預測這個故事是否會受到市場歡迎。作為內容創作者,當有一個創意時,你只有盡全力做到最好。此外,觀眾能否喜歡一部劇跟劇中角色也很有關系。如果觀眾喜歡一個角色,那他對這部劇的好感度會上升。
《綜藝報》:中國的網絡劇發展非常迅速,你對中國網絡劇發展有沒有一些建議?
John Mankiewicz:大家都愛看好故事,如果你能講一個好故事,不管是在互聯網、電視、抑或是大屏幕上都能取得成功。現在美國電影敘述的故事并不好,都是類似《變形金剛》《星球大戰》的動作大片,很少有電影能呈現豐滿的人物,因此美國現在迎來了電視劇新的黃金時代。如果你能講述好故事,這種黃金時代也可能發生在互聯網。但好故事對創作者來說仍然是一個“秘密”,我也在通過各種渠道尋找好故事。不過,如果我找到了新的好故事,也許我就不來上海了(笑)。
《綜藝報》:美劇有很多制作優良的行業劇,如《傲骨賢妻》《廣告狂人》以及你參與的《豪斯醫生》等,人物命運與情節發展跟人物的職業聯系緊密;但中國的很多行業劇,人物職業更多是作為一個背景。在行業劇的創作上,你有何經驗?
John Mankiewicz:豪斯醫生每一集中必須解決一個病例,不管是醫療劇、律政劇還是其他職業題材,案子(case)是推動故事發展的引擎。但是我認為這些劇吸引觀眾看下去的原因是劇中的角色,豪斯醫生非常瘋狂且濫用藥物,但不失為一個好醫生,這就是他性格的迷人之處。大家都知道醫生能夠救治病人,警察能夠抓住壞人,這些警察和醫生角色才是吸引觀眾看下去的原因。
《綜藝報》:目前美國市場上最貴的電視劇投資規模在什么區間?編劇所占的成本比例是多少?
John Mankiewicz:《豪斯醫生》非常貴,制作成本達到了600萬美元一集。《豪斯醫生》的編劇同樣由一個團隊負責,每位編劇的薪酬都是一樣的——大概每人每集3.8萬美元。隨著電視劇的播出,編劇還能拿到一些其他收益,如海外版權分成,大概一部劇在10年內能給一位編劇帶來幾百萬美元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