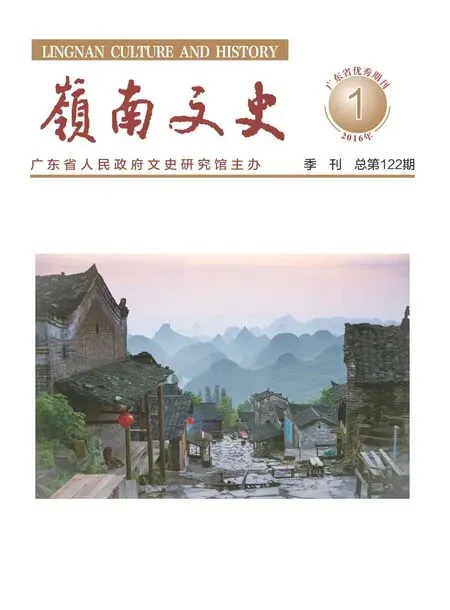18-19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女性
——以珠江疍家女為例
陳 曦
?
18-19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女性
——以珠江疍家女為例
陳 曦
18-19世紀,正值西方國家拓寬海外市場,進行資本積累之際,清政府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頒布“一口通商”政策,廣州成為唯一的對外開放港口。西方人聚集在廣州十三行經商,活動范圍主要在廣州河南一帶和珠江航道上。故此,他們最先遇到也最為熟悉的女性群體,便是被視作珠江沿岸女性象征的疍家女。18-19世紀西方人記錄與描繪的疍家女形象,較為真實地還原了當時疍家女性的生存狀況,對于了解和掌握清中晚期中國底層婦女的生存狀況,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一、疍民與廣州
疍民又稱疍家人,亦稱蛋蠻、龍人、龍戶等。疍,同蜑、蜒、蛋,為東南沿海地區在船上生活居住,從事捕魚、采珠、挖蠔等水上作業的族群統稱;而在不同地區,這些居民則有不同的俗稱,如廣州、香港一帶稱為“疍家”、“艇家”,漳泉一帶稱為“白水郎”,福州一帶則稱為“曲蹄”。
關于其源與廣東關系,眾說紛紜。范曄《后漢書》、司馬光《資治通鑒》、常琚《華陽國志》、樂史《太平寰宇記》、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等書籍文獻中皆有關于“蜑”的記載,[1]“嶺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在其《廣東新語》中更多次提及疍家。[2]疍學泰斗陳序經教授把30多種疍民起源說按船型、生活習性等歸納成六類,其中,宋代疍民聚居之地在兩廣;歷史學者羅香林在《百越源流與文化》中論證古代蜑民居地經越南達兩粵,其疍民源起于古越族的論證為后世學者普遍認可;梁啟超觀點與之相仿:“蜑族昔固洞居,而與華人雜廁者也,其由陸入水,不知仿自何時,為我族所逼,不能自存于陸地,是以及此,抑亦其自入水后,與我無爭,故能閱數千年,傳其種以迄今日,古百粵之族,其留純粹之血統,以供我輩學術上研究之資料者,惟此而已。”[3]
疍民主要分布在廣東、廣西、福建、海南、港澳等地,尤以珠江流域為甚。鴉片戰爭前,廣州作為唯一的通商口岸,是西方人活動的主要地區,疍民是西方人外游時接觸最多的群體,對此,當時來華的西方人多有描述。法國旅行家奧古斯特·博爾熱(Auguste Borget,1808-1877)、法國公使隨員伊凡(DR.YVAN)、英國訪華使團成員威廉·亞歷山大(William Alexander,1767-1816)、常年寓居澳門的著名畫家喬治·錢納利 (George Chinnery,1774-1852)等,都用文字或圖畫進行過形象塑造。尤其是在廣州生活40多年的美國人威廉·C·亨特 (William C. Hunter,1812-1891)在自己的著作《舊中國雜記》中更有對疍家的專門注錄:“疍家,一個非常有用的階層,他們的艇仔常年提供搭載乘客過江,前往花地或到十三行的服務。疍家一詞,意為‘疍人家庭’,由上面提到的艇子組成,艙頂的中央用厚席子覆蓋,用著若干支槳和一支櫓行駛”。[4]
二、西方人眼中的疍家女
根據清政府當時的規定,來廣州通商的西方商人不可隨意出行,不可到鄉間任意游行,不可進入內地貿易,只能在清政府指定的地方游玩。[5]因而在春、秋季節,西方商人定期從澳門坐船至廣州十三行進行貿易經商,按例到附近游玩,海幢寺、花地灣等地成為西方人在廣州主要的消遣旅游之地,他們接觸到最多的中國女性,就是生活在珠江河道上的疍家女。
水上活動范圍廣、流動大,疍家女像男人一樣在從事水上運輸工作,吃苦耐勞,也給予她們密切接觸西方人的機會。法國公使隨員伊凡便在其《廣州城內——法國公使隨員1840年代廣州見聞錄》書中描述:“一個船婦坐在船的前面,用高超的技術掌控著輕便的船槳……兩個可愛的船家女隨心所欲來引導我們看每一樣東西”。[6]對于這些西方人,疍家女的形象就是她們這一階層中國女性的象征。在西方人的記錄與描繪中,疍家女主要有以下幾個特征:
1.具有嫻熟的掌舵技能
疍民常年棲息水上,視水如陸,以舟為室,浮生江海。疍家的男人以捕魚為生,漁業是家庭主要的經濟來源;疍家的女人(如圖1),則常年通過搭載乘客過江、前往花地或十三行謀利,疍家女的艇子,不僅接送外國人,而且還向他們出售橘子、香蕉等多種商品,與他們進行各種生意往來。

圖1:英國訪華使團成員威廉·亞歷山大1793年繪疍家女
伊凡認為選擇在河上居住的疍家女是花城居民中最謹慎和最有藝術氣質的:“當我參觀珠江人口稠密的河床時,這座城市的絕妙景象令我產生不可思議的印象,我充滿真摯的熱情,自覺這一印象是客觀的……當我們深入了解居住水上、自力更生的居民的生活細節是……我們開始對那些勤勞的人們產生興趣”,[7]英國訪華使團成員威廉·亞歷山大在1793年就曾贊譽過疍家女的劃船和掌舵技術:“中國所有河流和運河上,都有大量的水上人家。這些女人的劃船和掌舵技術,和男人一樣嫻熟。”。[8]奧古斯特·博爾熱則觀察到:“這些船都建得十分牢固,以為乘客提供最大舒適為原則,通常兩名婦女在撐船,一個劃船,另一個既劃船又掌舵。她們都長得非常漂亮,衣服整潔。”[9]不難發現,剛進廣州城的西方人,幾乎都被疍家女嫻熟精湛的駕船技術、疍家船內舒適環境所吸引,而勤勞勇敢,不懼生活艱苦的疍家女形象則讓西方人大加贊賞。
2.具有“自然美”的形態
在中國封建社會,女性“纏足”被視為重要的美德,畸形的“三寸金蓮”是一種特殊的審美標準(如圖2)。許多西方人的描述中,“纏足”這種嚴重摧殘女性身體和心理的陋習,就像附在中國女性身上的特殊標簽,向他們展示著中國女性被扭曲的身體特征。如格雷夫人所見:“中國的太太們有時會騎在保姆的背上,從一條村到另一條村拜訪朋友,有些太太即使在自己的大花園里游玩時也會讓人背著”,[10]中國人扭曲小腳的審美讓他們感到匪夷所思和難以理解。

圖2:佚名畫師繪纏足女人制絲通草畫(廣東省博物館藏)
加之東西方審美標準的不同,在他們眼中,中國中上層女性的體型缺乏曲線美,甚至被偏頗地描述為“兩塊肋骨簡單的拼湊”,而疍家女不僅有著健康自然的身段,甚至疍家女的衣著打扮在西方人眼中也是整潔大方的。如英國人格雷夫人所見,搖擼和劃槳的疍家女最常見,她們的服裝質地是藍黑的棉布,身穿束腰外衣,褲子寬而短,褲子長至小腿的一半,她們既不穿鞋子也不穿襪子。[11]英國1849年出版的瑟爾(Henry Charles Sirr,1807-1872)的《中國與中國人》一書中,就有這樣的描述:“地位低下的女性,包括疍家或船上的女性,她們的手和胳膊勻稱美麗。總體看來,作為中國的女性,她們的手、胳膊和腳是我們所看過的最美的,前提是腳處于未被扭曲的自然狀態。”為了方便水上生活,疍家女常年裸足,天足有著自然的美感。
疍家女的頭發不剪短而是任其生長,有時編成像男人一樣的辮子(如圖1),更多的疍家女子會在頭頂上挽一個發髻或頭巾,或者戴上帽子遮陽擋雨(如圖3),[12]錢納利畫作中的疍家女便是常常戴著紅色的頭巾。錢納利畫作中有多幅關于疍家女“阿來”的寫實人物肖像畫,在他的傳記中,也曾記載了他與疍家女“阿來”、“阿常”來往,為她們繪制肖像畫的事情。這些流傳下來的疍家女肖像畫(如圖4),不僅可以讓人們直觀地了解到疍家女的形象特征,更可以讓人們直接觀察疍家女與中國傳統女性形象之間的差異。作為中國女性中比較特殊的一群,終年裸足是疍家女最明顯的特征。她們不纏足、不束乳、不扎腰,擁有黝黑健康膚色,形體健壯,沒有過多矯揉造作的打扮,在西方人眼中,有著一種“自然美”。

圖3:疍家女孩

圖4:錢納利疍家女
3.具有較強的商業意識
18-19世紀,隨著廣州口岸對外貿易的發展和珠江航道的日益繁忙,疍民不可避免地受到商品經濟的影響,商業意識漸增,逐漸開始從事一些漁業之外的商業活動。有這樣的記載:“有一大批的船被放置在架空的樓房底層,可能不能再下水了,成了數戶人家的住房。它們的頂上蓋著席子和釘在一起的木版,都是可活動。有時候這些船用來開店,廣州市里生活在水邊的各個階層都可以在那買到大米、辣椒,以及一個貧窮的中國人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任何物質資料。”[13]
在這種環境下,作為家庭重要勞動力的疍家女,很多成為積極、精明的生意人。不用纏足的身體條件,使她們可以加入到當時正常的商業經營活動中去,在商業運輸、商品貿易和服務行業承擔著重要的勞動角色。在滿布船艇的珠江航道上,到處都有疍家女穿梭忙碌的身影,調船渡客、運送貨物以至招攬顧客,管理運營雜貨艇、柴米艇、蔬菜艇,向顧客兜售燒生蠔、魚生粥、艇仔粥、炒蜆炒螺、花生糖等,給那些遠道而來的西方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伊凡還記載了一位疍家小女孩向其推銷早餐的事:“突然,這個小女孩對我說了幾句難聽懂的話,并把她的早餐遞給我。”[14]在毫不猶豫地品嘗了小女孩遞給的早餐后,伊凡給了小女孩半個比索(piastre, 埃及、西班牙、墨西哥的硬幣單位)。從這位疍家小女孩身上,我們可以看到疍家女那種強烈的做生意的意識,以及她們那種積極主動尋找顧客的意識。
4.處于社會底層的中國女性
疍民歷代都被視為“賤民”,毫無政治地位可言,備受剝削、欺壓和凌辱。屈大均在《廣東新語》提到:“女為獺而男為龍,以其皆非人類也……然良家不與通姻,以其性兇善盜,多為水鄉禍患。”[15]而對于整個中國社會來說,疍家女是連岸都無法靠近的下等人。疍民的生活習慣,決定了男人外出、女人掌艇的家庭分工,而守著船艇的疍家女為了增加收入,不得不從事大量的勞動。“幾天來,我們從不少船上看到,這些船由婦女劃船或司舵,在我們是覺得奇異的。這實在不是一種異常的現象,你會看到一個女子在背上用布帶縛著一個小孩,懷中又喂著一個嬰兒,同時又在劃槳或司舵。我好幾次也觀察到岸上的婦女們把嬰兒縛在懷里而同時在干她們的很勞累的工作。這種不愉快的、可能引人深思的現象在使團所經過的韃靼地區和中國北部各省從未見過。”[16]在這些文字中,無論記錄者賦予這些疍家女多少同情和惋惜,都注定不會改變這些疍家女一輩子勞碌辛苦的底層命運。

法國奧古斯特·博爾熱19世紀繪疍家漁民在珠江岸上[17](廣東省博物館藏)
疍民被視為“賤民”除生活來源于岸上外,還有其特殊職業有關,疍民生死與江海相依,隨潮往來,艱辛的生活,使一些年輕疍家女無奈走上娼妓道路。《清稗類鈔》有載:“生女,則視貌之妍媸,或自留撫蓄,或賣之鄰舟,父母兄弟,仍時相過問。稍長,輒句眉敷紛,押管調絲,蓋習俗相沿,有不能不為娼之勢。”[18]親自到過疍民區、近距離觀察過花艇的伊凡曾這樣描述:“浮城從兩個不同的方面展現著自己:白天它像個工業蜂巢,移動的蜂巢被那些勤勞和智慧的群體占據著——他們永遠活躍、從不畏懼無休止勞動的嚴苛壓榨。同是這個城市,晚上卻像個富有、美麗的高級妓女,她頭戴花冠,全身珠光寶氣,用迷人的聲音、古怪的旋律,喃喃低唱著三色堇(love-in-idleness)愛情歌曲:在夜色的掩護下,毫無矜持地進行著它那撩人情欲的交易。”[19]這些操持皮肉生意的疍家女,被稱為“魚蛋妹”、“水雞”、“咸水妹”等,連作為女性的尊嚴都蕩然無存,更談不上有什么社會地位。
三、結語
目前,作為嶺南文化史的一個重要內容,疍民研究方興未艾,研究范疇逐漸從歷史學擴展到民族史、人類學、社會學、民俗學等,專家學者或從歷史角度探究疍民淵源與發展, 或從人類學、民族史、民俗學等角度研究疍民族群特殊性或人類學價值。疍家女作為疍民中特殊的一群,有著重要的歷史學、人類學、民俗學研究價值。尤其是在18-19世紀,疍家女作為西方人接觸和認識中國女性的一個重要渠道,她們勤勉、吃苦耐勞、樂觀開朗和積極進取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顛覆了西方人眼中處于深閨大院、裹著小腳蹣跚而行的中國傳統女性形象。因此,關注18-19世紀西方人眼中的疍家女形象,也就是關注當時西方社會對中國女性的認知與印象,從而可以讓人們從另一個側面、以一種異域文化視角,多維度地觀察和思考清中晚期中國女性的生存狀況和社會地位。在此基礎上,可以更進一步從中國女性的社會地位和生存狀況出發,去思索和衡量中國社會的文明進步與演變發展。

ConwayMordauntShipley1854年繪花舫圖(廣東省博物館藏)
注釋:
[1]南朝·范曄撰,唐·李賢注:《后漢書》卷86“南蠻傳”記載(后簡稱“載”):“稟君之先,故出巫誕。巴蜀南郡蠻,本有五姓。”;晉·常琚《華陽國志》卷一載:“屬有濮、寶、苴、共、奴、儴、夷、疍之蠻”;《隋書·地理志》卷三十一載:“長沙郡,又雜有夷疍”;《隋書》“南蠻傳”載:“南蠻雜類,與華人錯居,曰蜒、曰儴、曰俚、曰僚、曰伍”;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百六十八載:“蜑戶,縣所管,生在江海,居于舟船,隨潮來往,捕魚為業”;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載:“晉時,廣州南岸,周旋六十余里,不賓屬者五萬余戶。皆蠻、蜒雜居”。
[2][15][清] 屈大均《廣東新語》香港中華書局1974年印刷版本中,提及疍家相關的詞條有“蛋家賊”(卷7,第250頁),“舟語”(卷十八,第476頁)以及“蛋家艇”(卷十八,第485頁)。
[3]梁啟超:《飲冰室專集之四十一 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中華書局,民國25年(1936),第10-11頁。
[4][美]亨特著,沈正邦譯,章文欽校:《舊中國雜記》,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頁腳注2。
[5]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匯編·第一冊》,北京:三聯書店出版,1982年,第35頁。原文為:“英商或常川居住,或不時來往,均不可妄到鄉間任意游行,更不可遠入內地貿易,中華地方官應與英國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地勢,議定界址,不許逾越,以期永久彼此相安。凡系水手及船上人等,俟管事官與地方官先行立定禁約之后,方準上岸。倘有英人違背此條禁約,擅到內地遠游者,不論係何品級,即聽該地方民人捉拏,交英國管事官依情處罪”。
[6][7][14][19]分別見[法]伊凡:《廣州城內——法國公使隨員1840年代廣州見聞錄》,張小貴、楊向艷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4、96、98、115頁。
[8][英]吳芳思:《帝國掠影—英國訪華使團畫筆下的清代中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32頁。
[9][法]奧古斯特·博爾熱著,錢林森等譯:《奧古斯特·博爾熱的廣州散記》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第37頁。
[10][11][英]格雷夫人著,梅貝堅譯:《在廣州的十四個月》,香港:香港茉莉花出版社,2011年,第15、14頁。
[12]疍家女頭上戴的帽子通常用藤條編成,做工精細,涂上油漆防水,跟雨傘功能相同,而且不需要占用正在搖槳的雙手。
[13][法]奧古斯特·博爾熱著,錢林森等譯:《奧古斯特·博爾熱的廣州散記》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第37頁。
[16][英]愛尼斯·安德遜:《英國人眼中的大清王朝》,費振東譯,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第206頁。
[17]疍家人所居住的船屋,往往就地取材,把漁船拉上岸,用石頭或木椿架起而成。
[18]《清稗類鈔》娼妓類《潮嘉之妓》。
(作者單位:廣東省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