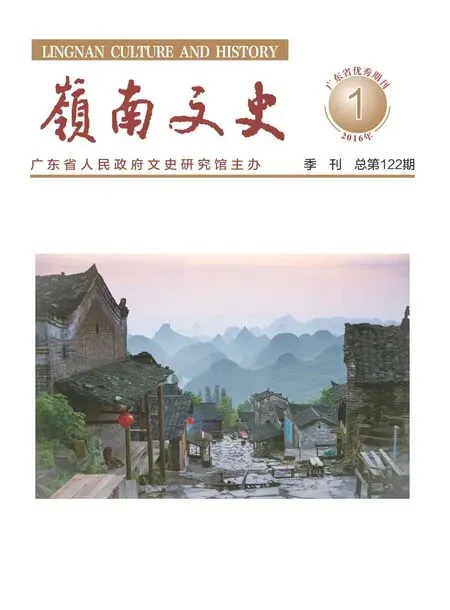潮劇源流新證
——兼與《潮劇史》一觀點商榷
陳 勃
?
潮劇源流新證
——兼與《潮劇史》一觀點商榷
陳 勃
潮劇與弋陽腔的關系,是潮劇史研究中爭議最大的問題,也是無法回避的問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觀點是逍遙天:“考高腔出于弋陽,潮音班的前身正音戲,也出于弋陽。”[1]持“出于弋陽”觀點的還有王起、流沙、張伯杰,持反對或商榷意見有筱三陽、李平。《潮劇史》則持“潮劇既非來自關戲童,也不是來自弋陽腔或正字戲”。[2]隨著近年戲曲研究的不斷深入和系統化,這謎一樣的難題已經揭開神秘的面紗,驚嘆逍遙天40多年前得出這一結論之不誣。在前人研究基礎上,結合近年的戲曲研究新進展,現加以論證并提出商榷意見。
一、潮劇源流探索歷程綜述
(一)研究述評
1.張伯杰:1959年論證“潮劇《掃窗會》劇目演出傳統,應脫胎自正音戲中曲戲類”

圖1:弋陽腔首本戲潮劇《掃窗會》
潮劇的曲牌分為頭板曲牌、二板曲牌、三板曲牌和散板曲牌。每一種曲牌都有特定的音樂結構、連接方式和鼓介、鑼經的運用規律。從研究潮劇弋陽腔“首本戲”(見20世紀60年代中國唱片公司潮劇唱片介紹)《掃窗會》入手,張伯杰通過實地調查潮劇、正字戲兩種戲劇音樂進行深入比較研究,論證小結如下:
(1)正字戲《百日緣》【小桃紅】頭版曲牌,與潮劇《掃窗會》【四朝元】頭板曲牌,從起三腳介散板到緩慢的4/4節奏、收句等以及對偶曲唱法,是同一胎形。這里曲調連接,和潮劇《掃窗會》介紹出場高文舉、王金真唱【四朝元】曲牌【下山虎】曲牌二曲段連接,正是同一形式。在音樂曲調上研究,其對字母句唱法,和潮劇尤為酷似。
(2)“十八板”為潮劇古曲調中一特殊曲句,其結構和正字《百日緣》中董永唱“十八板”同。《掃窗會》中王金真在愛恨交集,拋掃帚最突出動人一段是唱“十八板”。這二劇目中的“十八板”,均為同一傳統唱法,并在用法上似存古昔定規。
(3)正字戲董永唱“三板尾聲”(落尾)和潮劇唱“三板尾聲”一樣用法,尤類似《掃窗會》劇終落尾調曲調。除從曲牌分析研究之外,演出時運用幫腔也與潮劇相同,鑼鼓介鑼跟伴樂等,也聽出為潮劇大鑼戲前身雛形。
由于正字戲現在已經沒有《珍珠記》這一戲,“根據以上音樂腔調上的線索研究,證實潮劇《掃窗會》劇目演出傳統,應脫胎自正音戲中曲戲類。并非脫胎于正音戲昆戲類。就是說,少受昆曲唱法的影響。假如有足夠證據證實正音戲出自弋陽腔,那么,王起教授認為《掃窗會》劇目,源出自弋陽腔戲目,當為可信。”[3]對王起教授的結論另有兩點可以補充:(1)《曲海總目提要 卷三十六》:“珍珠記,一名珍珠米糷記,不知何人所作。……乃弋陽曲之最下者。”[4](2)清末江西僅存的弋陽腔的一支遺脈——饒河高腔的“十八本戲”中就有《高文舉》(《珍珠記》)。[5]

圖2:弋陽腔首本戲白字戲《珍珠記》
2.筱三陽:1960年對正字戲的可考性提出質疑
“正字戲的曲戲部分,與潮劇比較接近,彼此有血緣關系,是可以肯定的。但是,說今天的正字戲就是清代的潮州正音戲是缺乏根據的,因為它經歷了近百數十年的演變。至于說潮劇是蛻變于正音戲,也是缺乏可靠的材料。潮劇并不是三合班,如果說,正音戲對于潮劇的形成有過相當的影響,那會比較實際些。”[6]
這一質疑在當時的出土文物未發現的條件下提出是符合邏輯的。
3.李平:1982年提出質疑:“正字母”非弋陽腔
在研究兩個出土戲文以后,李平肯定潮劇老藝人和與梨園有過關系的長者皆謂之“正字母生白字仔”這一說法,提出:所謂正音戲,淵源應是南戲,是明代海鹽、余姚、弋、昆四大聲腔廣為傳播之前的南戲。[7]
(二)“正字母生白字仔”新證
1.正字戲淵源并非不可考
(1)溫潮一脈。
筱三陽對正字戲的可考性提出質疑。但是寶貴的戲文出土文物出現了,正如饒宗頤所說:“以前不知‘正音戲’起始于何時,現在從宣德抄本的正字劉希必(文龍)一名稱,可以看出南戲傳入潮州之早,分明是受到南戲的影響。”[8]明宣德時期(1426—1435)潮汕地區即出現以官話為主、雜有潮州方言的南戲演出活動。1975年潮州市鳳塘公社后隴山園地出土對折紙本《新編全相南北插科忠孝正字劉希必金釵記》,封面朱書“迎春集”,且標明“宣德六年六月十九日”、“宣德七年六月在勝寺梨園置”等重要信息,是中國目前所見最早的戲文寫本,早于上海成化(1465—1487)本30多年。而且還附有鑼鼓經,鄭孟津對其點板的考證,認為與琵琶記的明初臞仙本正是一脈相承。
饒宗頤、李平、張伯杰、陳歷明等均認為是正字戲,惟《潮劇史》認為“潮劇迄今已有580年歷史”,明顯從宣德七年(1432)算作潮劇起點,頗不可解,值得商榷。饒宗頤考證:“正音是與本地鄉音相對立的雅言(地方舊時稱曰“孔子正”,是指讀書諷誦的語音)”。[9]這里的雅言即當時的普通話,也是科舉考試、打官腔的“官話”。通俗說,正字戲正是用明時的“潮州普通話”唱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北曲是按照元周德清《中原音韻》的“平分陰陽,入派三聲”的實際語言來唱的,也就是北方方言入聲韻已經消失了;然而潮州出土宣德本《金釵記》這種用“正字”(雅言)來演唱的情況,實則保留了“宣和間已濫觴,其盛行則自南渡”(徐渭語)[10]的南戲的原貌。
當時“梨園”的盛況應該不難想象,現在潮州保留正字戲、大白字戲、潮劇三個南戲實例,這在戲曲史上也是罕見的,而這也成為研究這一問題的關鍵。
(2)正字戲至今能唱宣德本《金釵記》中的“哩啰漣”曲。
說正字戲源遠流長,還有一點:明宣德抄本《金釵記》和今天正字戲都有此曲。《金釵記》中既獨立成曲,亦有時用于曲尾。第四十出劉希必被逼招為番邦駙馬后,“番邦辦午”在“弄舞”時,唱“哩漣羅哩漣,哩羅哩羅羅哩漣羅哩漣羅漣哩漣羅哩漣羅羅哩漣羅哩漣”。這種“羅哩漣”曲,正字戲一直保留下來,名藝人陳寶壽等還能唱。陸豐縣民間小戲竹馬戲至今也唱這種曲調。白字戲也有“羅哩漣”曲,與正字戲相同;潮劇現已失傳。這也看出正字戲與宣德本《金釵記》的繼承關系和潮劇、白字戲之間的親緣和進化過程,在“世之腔調,每三十年一變”(王驥德語)[11]中,潮劇跑在了前面,把尾巴進化沒了。
(3)宣德本《金釵記》的三棒鼓、德勝鼓與正字戲如出一轍。
李平曾拿宣德本《金釵記》的三棒鼓、德勝鼓的鑼鼓詢查正字戲打鼓師陳春淮同志,他說,雖正字戲已不能全條打出,但冬征當、冬正貢的音響是同一條路道的。[12]
2.逍遙天論潮劇與正字戲的關系
(1)潮劇脫胎于正字戲的進化痕跡。
“看現在的潮音戲各班,其開鑼例戲,如唐明皇凈棚、八仙慶壽、仙姬送子及收鑼的團圓,這若干出都說“戲棚官話”,腳色中的凈則無論在任何劇本里面,都用假嗓子說官話,這是“老狐化人”,仍留一條尾巴不能掩藏,舊時正音的遺腔仍未泯滅呢。”[13]
“老狐化人”這一“‘凈’說‘戲棚官話’”現象,是又一個進化的遺痕,在明刊《重補摘錦潮調金花女大全》中“投江遇救”一出中,就有“凈扮判官”宣讀陰司的“玉皇圣旨”,此戲文特注明“正音”,可作一證據。另在“劉永祭江”一出中,“驛丞”的對白也是注明“正音”,說明當時的官話、雅言(普通話)就是正字(正音),即現在稱為中古音的體系,有別于元代以后入聲消失的北方語言。
(2)演出活動習俗方面的證據。
正音戲的做場,臺面中央掛三竹簾,潮音戲也循老規矩,掛三竹簾,這是祖肇元劇的遺制。再看潮州其他像外江、西秦各種戲劇的做場,臺中都掛紅帳幕,和正音戲、潮音戲迥異,顯得正音戲、潮音戲的標幟是相同的。
正音戲每唱詞的句末,曼聲折轉,或由臺后閑著的優伶幫腔,潮音戲亦然。
20世紀七八十年代前的潮音戲,演唱戲目中頗多摘錦,都淵源于正音戲。
現在的潮音戲,仍稱其腳色曰生、旦、丑、花面;戲劇專用術語如科、白、介、出、關目、妝扮、起套、煞尾;劇中人稱謂如員外、安人、梅香、小姐、老漢、老身、奴家、小人;口語如則個、怎生、少待、知道、打睡;助詞如呵、了、生、的、呢、嗎,一切都沿用正音戲的慣辭,和潮州的方言回不相侔。所有行頭,純為明代衣冠,網巾尤為特征。這可說是正音戲原貨承接,連半點混化現象都沒有。[14]
(3)潮劇鼓介來自正字戲的證據。
據逍遙天考證:《網魚》是正字戲《杏元和番》里陳春生遇盜投水,適漁家女網魚獲救的一節,現仍保存在潮安鑼鼓樂中。這是潮音戲劇與音樂的一個重要文獻,現在潮音戲的鼓介“火炮”、“累累金”、“拗槌”、“紗帽頭”、“水底魚”、“五千箭”,原來是正音戲的鼓介。[15]
(4)潮劇大牌子鼓點以正字戲鼓樂為標準。
“又聞自老樂工,舊時之正音戲,亦為吹笛鑼鼓之導師,潮州鑼鼓樂如銅旗、五關、拋魚、追舟、鬧港、封相是大牌子,大鼓點,皆以正音戲之鼓樂為標準。”[16]
3.潮劇與正字戲同屬一調式體系:古老的“二四”絕譜
陳蕾士說:“二四譜”不但為潮州音樂長期使用之譜式,潮州戲劇音樂生命之所系,而且亦是今日潮州樂調之依據。[17]
唱腔音樂的用調,是表達、襯托唱腔感情和增添色彩的不可缺少的藝術形式。潮劇唱腔音樂和潮州民間音樂一樣,有輕三六調、重三六調、活三五調、反線調、輕三重六調等之分。由于用音的主次和音的進行不同,演唱和演奏技巧的變化,故而產生了不同色彩的音調和不同感情傾向,是潮劇唱腔音樂色彩表現的另一手法。

圖3:潮劇《槐蔭別》與正字戲如出一轍
潮劇各調式名稱出自潮州古樂譜“二四譜”的記譜方式和演奏方法。二四譜記音為二()三()四(1)五(2)六(3 4)七(5)八(6),輕奏三六得3,重奏三六得4,故把無4者定為輕三六調,簡稱輕六;有4者為重三六調,簡稱重六;所謂活五,就是就是逢五(2)活奏,成為滑音。在音程、音高方面,與其他聲腔也有差異。根據陳蕾士的考證,“二四譜”是伴奏彈詞的箏譜,潮州“二四”樂譜與日本箏譜同源及二四譜與唐箏定弦吻合。[18]
看南戲的發展,戲文不少地方保留了唐宋大曲的遺存,如【推拍】、【滾遍】、【賺】。從唐宋大曲后來發展出諸宮調(不同宮調的曲子合成一曲),到南宋出現賺(同一宮調南北曲合成一曲),再到南戲的南北合套,自然被稱作“不協宮調”。
再從潮劇的領奏樂器“二弦”(也是潮州弦詩的領奏樂器)的演奏技巧看,演奏時坐姿保存唐樂伎趺坐特色。今泉州開元寺大殿木雕中有拉二弦伎樂飛天。

圖4:泉州開元寺大殿拉二弦伎樂飛天
“唐宋大曲(有慢板、中板、快板),至今仍保留于潮州音樂大套曲中。唐宋一些術語(散序、入破、虛催、實催、歇拍、煞滾)目前仍在潮州音樂中應用,如變奏稱‘催’,樂曲結束稱‘煞’,每首弦絲樂譜都要注明多少‘板拍’,樂曲進入板后起音部分稱拷拍。拉弦樂器千斤稱‘徽’,把位稱‘上徽’、‘下徽’。樂曲反復稱‘踏纏’、節奏旋律稱‘繚舵’,等等。”[19]“變奏是潮州弦詩樂一大特色,特別是體現在弦詩的催奏上,催的變化可謂出神入化、層出不窮、風格獨特。潮樂變奏雖說能演變幾十種,但一般常用的是十多種,基本催奏手法是單催、雙催、雙疊催,變化催法有跑馬催、雞啄粟、劃船催、板后催、企六催、雞仔跳催等常用催法。”[20]
既然潮劇與正字同屬一種調式體系,因此李平認為,甚至可以將兩者看作同一劇種,進而也認為不可歸入弋陽腔的原因。
4.正字戲與弋陽腔歷史淵源的幾個證據
(1)正字戲保留中元節演出弋陽腔連臺戲、三國戲等古老戲目的習俗。
在今天知名的傳統戲中,三公戲和目連戲是明代碣石衛軍戲的演出劇目。保留中元節演出弋陽腔連臺戲、三國戲等古老戲目的習俗。陳守繼有這樣的記述:“碣石衛玄武山戲臺最為典型。乾隆年間開始的雙班合演,實際上就是為了演《三國》,《三國》作為‘正出’戲,除合演的第一天,因為上半天演開臺例戲《搬大仙》(乾隆碣石總兵吳本漢編撰,故藝人亦稱《吳本漢仙》),是玄武山獨有的劇目),推到下午演出以外,每一天,它都從上午八時演起,中午略事休息,下午接著演至二時許才結束。其它劇目只作為‘團圓戲’,從下午二時許演至五時左右。”[21]
三國戲可惜大部分已經演變為科白戲,仍然保留古老唱腔的,正字戲只存《斬雄虎》、《闖轅門》、《曹公賜馬》、《霸陵橋別》、《千里獨行》、《過五關》、《古城會》、《單刀會》等10出。清末江西僅存的弋陽腔的一支遺脈——饒河高腔的“十八本戲”中也有《古城會》。
(2)正字戲保留了原始的弋陽腔。
魏良輔所謂“自徽州、江西、福建俱作弋陽腔。永樂間,云、貴二省皆作之,會唱者頗入耳。”[22]既然明初弋陽腔已流傳到云南、貴州等邊陲之地,那么它在元末已產生,這是毋庸置疑的了。“明初永樂年間進入云南、貴州的弋陽腔,按照以上這些情況來看,只能是目連戲階段所唱的高腔,這種高腔因其有江西地方特點,所以才被后人稱為弋陽腔。”[23]所以正字戲演弋陽腔目連戲、連臺戲、三國戲,正是保留了弋陽腔貴老的一層。
二、潮劇源流新證
既然說潮劇可能源于先于四大聲腔的南戲,又有越來越多證據揭示與弋陽腔的淵源,這不是矛盾嗎?問題出在一般的縱向溯源和橫向比較是有局限性的。因為戲曲源流復雜,戲劇雖然為群眾甚至官府喜聞樂見,但是正統觀點認為是不登大雅之堂,所以資料呈碎片化,非文化人類學難以勝任。舉個明了的例子:《詩經·野有死麕》都說是愛情詩,但誰也不知道“死麕”跟愛情有什么關系,鄉賢溫丹銘先生運用人類學方法,考證出殺死鹿是上古求婚的儀式,后改成以儷皮為禮:
“《野有死麕》,《毛傳》以為‘兇荒殺禮’,實則太古昏禮之僅存者。英人泰勒氏之《進化論》曰:美洲尼加拉圭河之打牲族人,凡男悅女而欲娶之,必先獵于田間,殺一鹿,拾薪至女家門首,疊成堆,至鹿其上,以為聘禮。即《詩》所謂‘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也。麕、鹿為一類,故二者得通用也。自伏羲出,以死鹿為不文,乃改用儷皮為禮。然草野之間,荒遠之地,猶有沿用太古之俗。南方諸國被化獨遲,其出此也,蓋無足怪。豈為兇荒之殺哉?大抵先古遺文,后人所不解者,往往藉今日環球之交通,群學之發明,得以剖其疑難而正其謬誤。彼說經家之憑一己臆見,紛紛致辨者,亦可以息矣。”[24]
這種“禮失求諸野”的方法,溫丹銘先生認為是止息“臆見”的利器。
王國維是以戲劇人類學方法,研究《宋元戲曲史》的第一人,逍遙天是繼承此方法研究潮劇的第一人,他的《戲劇音樂志》也是首次編入地方史志的戲劇志。
同樣,以戲劇人類學的方法,可以找到潮劇史失落的一環。包含三層內涵:
第一層:基因層,原始宗教階段。
第二層:孵化層,宗教階段。
第三層:表現層,南戲階段。
(一)潮劇起源“關戲童”的文化內涵
1.潮劇關戲童同祀田元帥
“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左傳》語)這是人類學的規律,逍遙天論述:“歷來各種戲班所崇祀的戲神,形形色色,全不一樣,如京劇祀老郎神,越劇祀華光大帝,我們頗可從此而知其流派之異同。”[25]
第一,潮劇與關戲童同祀田元帥。“凡潮音戲開班,必祀此神。初就田野間拾取田土一枚,歸盛香爐中,奉牲果香燭虔誠禱祭,這叫做‘請元帥’。按此神是關戲童所祀的神,故關戲童一稱關田元帥,后來潮州的秧歌戲也同樣祀它,我以我的觀察,必由關戲童傳給秧歌戲,再傳給潮音戲,一脈相承,可以看清楚同出一源的跡象。”[26]
第二,潮州的關戲童,乃承接古代侏儒倡優的舊規,潮音戲的鼻祖便是關戲童;潮音戲以土語唱平喉入曲,也肇自關戲童。
第三,關戲童是青蛙圖騰崇拜。田元帥是戲師,祖傳是最初的教戲者,教曲甫成,化為青蛙而隱,潮州民間更有這種青蛙圖騰崇拜的淫祀,青蛙圖騰崇拜與西南的銅鼓文化有關系。又,據老一輩樂師敘述,潮劇中的椰胡原來不是用椰子殼做的,而是用葫蘆作的,所以原稱“瓠弦”,與西南納西族的“葫蘆琴”相似。
最后,經調查,江西弋陽腔戲班的戲神,除了湯顯祖故鄉宜黃的戲班祀清源師,其他地區大多數戲班皆供田元帥(田師傅,田府正堂)。
2.潮劇起源于“關戲童”垂傳甚古之巫術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早就用戲劇人類學對南戲進行研究,即引證了“后世戲劇,當自巫、優二者出”,“巫以樂神,而優以樂人”。潮劇則源于巫優兼備的“關戲童”。逍遙天《潮州戲劇志》上有詳細記載:“潮州農村,中秋前后有關戲童之舉,秋夜散步田壟間,月白風清,傳來婉孌歌聲,頌咒聲,按聲詢問,則關戲童也。憶昔鄉居,習見不鮮。此類關戲童,為垂傳甚古之巫術,演時先由主其事者,赴田間奉田土一枚歸,安置香爐中,陳瓜果香燭膜拜之,曰請田元帥。于是復邀集童子十余,推出一二人為角色,拈香閉目,蹲坐中央。群童四周圍繞,并各執香火一柱,上下左右搖蕩,若魚貫飛螢,火光縷縷閃爍,凝視目為之眩。”。群童復齊聲奉咒,其詞各地差異。“豪姑像,豪姑唔在處,豪仔氣到無禾和,姨姑姨,姨姑唔在處,姨仔氣到偷吃請飯。”[27]
《呂氏春秋·異寶》:“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名甚惡。荊人畏鬼,而越人信機。”《淮南子·人間訓》云:“荊人鬼,越人魕”。今潮俗呼巫覡為“童魕”、“童鬾”、“童身”(童讀如當,上古東陽同韻),可見猶存上古苗瑤族巫覡原童男童女的遺存,馬王堆漢墓出土有楚人巫醫書《五十二病方》中有逐鬾之方:“鬾,禹步三,取取桃中枳,中別為□□□之倡而笄門戶上各一。祝曰:墳者鬾父鬾母,毋慝□□□北□巫婦求若固得。□若四體,編若十指,投若□水。人殹人毆而比鬼。每行□,以采蠡為車。以敞箕為輿。乘人黑豬。行人室家。”此逐鬾之方,兼記祝辭,皆為有韻之文。“鬾”,饒宗頤考證為“小兒鬼”,逐鬾方法就是用“禹步”,具體還要取桃木,插在門、戶上,還要頌一段“祝”的咒語。進而說:“越為楚的吞併,故越俗同化于楚。漢武平兩越,乃令越巫立越祝祠,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越巫楚巫可合而觀之。巫與醫不分,古稱為巫醫。巫有治病之俗,在苗、傜少數民族至今尚然。秦漢時楚巫治病詳細情形,可于馬王堆《五十二病方》中見其大概。”[28]今潮汕地區很多風俗與此相關,固其來有自,如十分注重“新桃換舊符”的春聯習俗,并且潮汕地區仍存在“膠了”[kaliao]的辟邪驅鬼的巫醫術,([ka]實為古苗瑤語的一個詞頭,潮汕話中有如“曱甴”[katsua]、膠走、膠椎,丟東西稱“膠老”[kaliau]、屁股稱“膠村”、脊骨稱“膠脊”,稱自己為“膠己”等不一而足。[29]潮汕端午用艾,在門、老爺爐(天神)、阿公爐(祖宗神)、米甕、箸桐、辮子、耳后都要插艾草以除魔辟邪;饒平古樓山有“藥簽”同樣是上古巫醫的遺存。原始的端午節是祭江神,至今南方少數民族、日本均是,五月節無疑是古苗瑤族一個重要節日,以至于用來紀念屈原,可見對這位楚國大夫帝高陽之苗裔的無比崇敬。“我們既悉關戲童仍承數千年侏儒的舊俗,歷觀各地‘請紫姑’、‘扶箕’、‘關亡’……便明了都為古代關戲童的分支衍變。可是各地關戲童的的風俗轉趨泯滅,惟獨潮州,則本干和分支并存,亦可說是奇異的得很了。”[30]
3.白字戲音樂源于弋陽腔儺舞
(1)白字戲音樂以龍虎山道樂為宗。
《白字戲志初稿》的記載:“據‘紅壇’后裔劉振豐先生(現年65歲、陸豐甲子鎮人)的介紹,紅壇在開壇時‘請五土’的曲調,就夾有‘啊咿噯’的襯腔,伴奏音樂曲調有【粉紅蓮】、【戲水】、【福德詞】、【楊柳岸】、【柳金花】、【南正宮】、【北正宮】、【過江龍】等。紅壇的祖師爺是江南龍虎山的張伏波——張天師,劉振豐先生一年一度前往龍虎山晉偈廟觀,白字戲的聲腔及其所以與‘法曲’相似,在這里可以印證。”[ 31]
龍虎山被視為道教最早的發祥地,道教正一派之祖庭,在道教宮觀中享有非特別地位。2010年,“龍虎山正一天師道齋醮科儀”被列入江西省第三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天師道音樂是在民間音樂和南方戲劇音樂相融合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并廣泛地吸取了唐、宋以后的宮廷音樂。從音樂結構和內容上看,龍虎山道樂有經韻和曲牌兩大類,經韻音樂又分為“弋陽腔”和“上清腔”兩個腔系。“弋陽腔”是以江西弋陽一帶的方言、民歌為基礎而形成的一種腔系,其韻腔旋律及經韻的唱誦有突出的地域性民俗風格,用同一基本旋律的腔型套用不同經詞的同曲異詞現象比較普遍。這一腔系多在弋陽籍和相鄰地區籍的道人中流傳,主要用于鄉間道場。曲牌音樂於數量上所占比例不大,但使用靈活并富於變化,且具有很強的功用意義。而且原汁原味的弋陽腔,沒有絲弦伴奏,只靠人聲幫腔,鑼鼓打節奏,顯示出儺的特征。
(2)龍虎山正一天師道齋醮科儀源于上古楚巫原始宗教。
正一天師道音樂的主要價值,在于它繼承了上古巫祝文化的某些遺傳,又介于宮廷音樂、民間音樂,儺舞音樂之間,是宗教特有的“通神”、“娛神”的音樂。“周禮既廢,巫風大興;楚越之間,其風尤盛。王逸《楚辭章句》謂:楚國南部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俚,因為作《九歌》之曲。”[32]道教與上古楚俗有千絲萬縷的關系,饒宗頤先生《道教與楚俗關系新證——楚文化的新認識》一文有考證:“西方學人喜歡用薩滿教的原理,去了解楚辭。雖然,它和巫術結上不可避免的宿緣,但從深一步看,楚人本身有他的宗教意識,和巫醫關系非常密切。從馬王堆出土各種文書看來,甲乙本的《老子》和其它戰國末期關于黃老學《十大經》一類的佚書,自然,這分明是道家的著作,但其它的簡策,像《日書》、《刑德》、《導引圖》、《卻谷食氣經》、《養生方》、《五十二病方》等等,事實上幾乎包括《漢書·藝文志》中的數術、方技略,這些寫本相當后來《道藏》內涵中最重要的部分。”[33]
其中最有說服力的是,龍虎山正一天師道齋醮科儀所施行“禹步”,即出自馬王堆漢墓《五十二病方》:現行道教正一派齋醮科儀分兩大類:以祈福、消災、開光為主的清醮(又稱陽醮)和以度亡、追薦為主的幽醮(又稱陰醮)。宮觀道士逢重大節日或應齋主要求舉齋醮。清醮一般在陽氣充足的上午于道觀殿堂中舉行,陰醮則在陰氣漸盛的下午或晚上在空曠戶外進行。醮壇上置供桌,上有香爐、木魚、罄、供器、供養、法器等一應器物。參加齋醮的道士一般為四至七人,中大型齋醮有幾十人或數百人。法師身著金絲銀線刺繡的圖案花紋。主要舞蹈動作有掐訣、叩齒、步罡、禮拜等。
掐訣:手指按一定的方法盤結捏掐而成的形狀稱作訣,其過程稱作掐訣。能通真制邪,招遣神靈。
步罡踏斗:相傳創自夏禹,故又稱“禹步”。“罡”指天罡,“斗”指北斗。高功在壇場上,手持朝笏,按特定步伐,腳踏太極八卦,以進入上天,啟奏神明。
禮拜:俗稱“叩頭”、“作揖”,其又分稽首、作禮、遵作和心禮,以表示對神明的尊敬。
灑凈:高功右手舉桃木劍,左手掐訣持小香爐。用以潔凈法壇。
召將:高功手舉天皇號牌,大聲吟唱,召遣天兵天將。
叩齒:即上齒與下齒相叩,以集神驅邪。
齋醮過程是道教中溝通神明、祈求保佑、消災賜福的儀式。
饒宗頤考證“黃神”、“禹步”非三張的創始,實源自上古楚俗,“實在出于楚國的巫醫”:“楚人信巫鬼,崇奉“黃神”,使用禹步祝咒之術用以治病。寧鄉出土人面方鼎應該是象征黃帝四面,如果這說可信的話,楚國黃老之學根深柢固,可以追溯到殷商時代。結合新舊材料尤其在帛書《五十二病方》中的記載,說明東漢三張之設鬼道,為人治病請禱等活動,實際上秦漢之際,在楚國地區已是司空見慣。北周甄鸞斥責三張之術造黃神殺鬼之法,這在《五十二病方》中己證明所謂黃神不是他們所杜撰,而有悠遠的來歷。實在出于楚國的巫醫。許多名目可以看出當時民間流行的醫術,正和鬼道有許多雷同之處,加以馬王堆出土各種房中術養生方等方技之流行,正是后來道教徒的課題。”[34]
也就是說,上古楚俗雖無道教之名,而有道教之實,這種道教音樂和科儀,源自上古楚國流行的原始宗教活動——禹步,這一在馬王堆《五十二病方》廣泛采用的巫術。這一點,龍虎山懸棺葬更加可以幫助揭開這一實行懸棺葬的南島語文化圈的人類學之謎。龍虎山崖墓數以百計,全部鑲嵌在仙水巖一帶的懸崖峭壁之上。仙水巖諸峰峭拔陡險,巖壁光滑平展,巖腳下便是瀘溪河,臨水懸崖絕壁上布滿了各式各樣的巖洞,獨特的地理環境是龍虎山崖墓的基本成因。從瀘溪河舟中或地面眺望,隱約望見一個個巖洞口或釘木樁,或封木板,“藏一棺而暴其半者”多處可見。這些崖墓大多是2500多年前春秋戰國時期古越人的崖墓懸棺,其葬位離水面20-50米以上,高的達300多米。在大片巖壁上,洞穴星羅棋布,星星點點,或高或低,或大或小,數以百計。因這些洞穴高不可攀,無人入內,其中所藏之物,多少個世紀以來一直是一個不解之謎。這也是西南儺文化也以龍虎山為宗的重要原因。中國西南地區的藏、壯、瑤、苗、侗、水、彝、佤、白、土家、仡佬、布依、哈尼、納西、門巴、基諾等民族都保存著儺祭習俗,難怪西南少數民族儺壇與道教關系密切,無論是何地起教的儺壇,都自稱屬江西龍虎山張天師的正一派。
4.潮劇扮仙戲《六國封相》存在“童魕”、“禹步”上古楚俗遺存
潮劇承正字戲傳統,演出前必先凈棚,演出帶有宗教色彩的儀式性的扮仙戲,禮失求諸野。據新加坡容世誠的記述,《六國封相》在1990年代一年內演出300多臺。《六國封相》隱約透露了不少宗教儀式,最明顯有,花旦向蘇秦和黃門官敬茶完畢,走入后臺拿出一盤鹽米,走向臺中央往臺下撒米。撒米在中國傳統民間宗教有播種謝土,也有施食飼鬼的象征意義,所以同時是增殖儀式,也有驅邪去煞的目的。[35]而且,《六國封相》保留了原始的禹步。容世誠記述:“在一名乩童帶領下,百多名男子在廟前排陣穿插,演出達一個小時,他們稱這種隊舞為‘練兵排陣,也有稱為‘踏罡’,從‘踏罡’這個名字看來,上述舞步很可能和傳統道教的‘七星步’、‘禹步’屬同一類型的儀式步法,其目的功能都和驅邪趕煞有關。”[36]
(二)道教、佛教與潮劇的形成
1.佛教道教融合促成目連戲成為弋陽腔發展的過渡一環
目連戲起源于唐代長篇變文《目連緣起》、《大目犍冥間救母變文》。由南戲變成的弋陽腔,中間還有個目連戲為其過渡。也就是說弋陽腔最早是專演南戲的目連戲,經過發展再由目連戲變成弋陽腔的。“所以元末明初在江西興起的戲曲,當然就是以高腔唱出的目連戲。這種情況雖然不見記載,但是江西和湖南民間流傳的一些說法,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如江西弋陽縣人傳說認為弋陽腔是由道士唱目連戲衍變而來的(1956年我到弋陽縣調查戲曲時,曾訪問當地著名人士張景崗,談到弋陽腔的產生。他說,弋陽縣有種傳說,就是因道士唱《目連戲文》分為兩派,一派為道士腔,一派即變成弋陽腔)。現今贛東北和贛南的高腔藝人都說弋陽腔的音樂唱腔,就是以目連戲為其標準曲牌(贛劇弋陽腔老樂師王仕仁、贛州東河戲高腔老藝人鐘銘鵠等都有這種說法)。在湖南各地流傳的高腔劇種中,目連戲被藝人看作是弋陽腔的“娘戲”。這些事例足以說明,從宋元南戲到明代的弋陽腔,目連戲是一個承上啟下的環節,如果缺少這一環節,根本就不會有弋陽腔的產生。”[37]
2.正字戲的道教遺存
(1)“三公曲”( “師公(道士)曲”)。
正字戲“三公曲”具有比較濃的師公曲的味道,唱腔中有許多似唱似念,大多是一字一音的朗誦體,有點兼有三板的“快”和散板的“散”;板式用[三板散],落板如過江鯽子那樣密集,一路就那么急急打下去;有點幾乎是一字一板,速度可以和三板一樣,可以比它更快,更可以比它稍慢,用[塹板]。無論[三板散]和[塹板],都是節奏急促,而且比較自由的眼板。它們當是王驥德在《曲律·論板眼》中所說的弋陽腔的流水板。這些朗誦體腔調與師公曲幾乎相同,其中有的和師公曲如出一轍。
除唱腔同師公曲有血緣關系外,其他方面也顯著殘存著道壇的色彩。海豐、陸豐一帶至今流傳古老的正字道和福建道。道壇俗稱師公班,故道士也被稱為“師公”。正字道講官話;福建道,語言以福佬話為主,雜以官話。后者是由前者衍變而成,是前者的地方化。他們信奉張天師,其源出于江西龍虎山。屬福建道的陸豐甲子鎮福安壇的傳人劉振豐說,從前他們同龍虎山壇主間每一代見面一次,以師徒相稱。[38]
(2)正字戲的道教色彩。
除道士腔,三公戲和正字戲班至今都帶有道壇的色彩。根據陳守繼敘述:全部戲箱(包括一雙槍刀白桶,即裝槍刀把子的大桶),都繪上太極圖——繪于箱囊的前后兩面,以紅色為底色,用黑、白二色繪就,頗突出。與道壇的道箱,所繪圖案相同。牛皮制作的裝上長柄的刀槍把子,如長矛、銀槍、大刀、畫戟、長斧等,槍頭稍寬處也都繪上太極圖,這一點與甲子福安壇的槍刀把子相同。在原屬明代衛、所的戲臺演三國戲,每天開演前,要先擂[三報鼓]和“跳天將”,[三報鼓]的鑼鼓點講究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跳天降”也稱“凈棚”,由八名藝人作天將打扮,手持長柄刀槍,神情莊嚴,在大鑼大鼓的伴奏下,滿臺穿行,它與道壇的一種稱作“穿五土”的舞蹈,參加人數相同,穿行的路線和構成的圖形也正好相同。在玄武山,雙班合演之前,全體藝人要沐浴齋戒,在北極元天上帝爐前,把一把劍和一把三股叉請上后臺奉祀,劍和三股叉都是道教的法器。藝人會畫一種能夠驅邪制煞的紙符,每到剛剛修建的戲臺,或者剛搭建的草臺演出,便要把它貼在前臺、后臺的各個角落。畫紙符,戲班里世代有師承,它與道壇的同類紙符完全一樣。戲班除道教色彩,它和道壇在其他方面也有一些共同點:戲棚和道棚式樣相同,臺上都是一桌兩椅,各種陳設的稱謂大致相同,如“門簾”稱“卷壁”;甚至行話也相同,如食稱“乞口”,“肉”稱“內人”,“酒”稱“三點酉”。[39]
3.潮劇的道教、佛教遺存
(1)明本潮州戲文中的“哩啰漣”來自佛教。
明嘉靖本《荔鏡記》劇作為“內唱”,即臺后唱處理。《荔》劇的唱詞是:“羅漣漣里漣漣柳漣漣漣呵柳漣柳,漣漣漣柳漣漣漣。”
饒宗頤考證:莆劇認為唱“哩啰漣”等于念咒,可以避兇趨吉,我以前曾研究這一類和聲(打和),是從《悉談章》的“魯流盧樓”而來,演變為唐人《渭城曲》的“喇里離賴”。源出于佛家《涅槃經》文字品。全真教采用它,變為“哩啰”,禪家作“啰啰哩”,再變成為“哩啰漣”。由莆劇把它作為咒文一層看,鄙說是可以成立的。[40]另外,白字戲唱腔中的句末頻繁出現的“啊咿噯”襯詞也是來源于道壇的聲腔。
(2)“歌冊體”的潮劇戲目受佛教變文影響。
變文于1907年被發現于甘肅敦煌千佛洞之唐代抄卷中,此類抄卷的內容,包括佛教道經典樂曲及中國失傳之文學作品。抄寫年代自公元五世紀起。現摘錄變文一二段。
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目連啼哭念慈親,神通急速若風云。若問冥途刑要出,無過此個大將軍。左右攢槍當大道,東西立杖萬余人。縱然舉目西南望,正見俄俄五道神。守此路來經幾劫,千軍萬眾定刑名。從道各自尋緣業,貧道慈母傍行檀。魂魄漂流冥路間,若問三涂何處苦,咸言五道鬼門關。”
包公會里后(潮曲):提起前事淚汪汪,滿腹冤情在此中。老身受苦楚,在此破窯苦難當。昨夜夢見神仙語,果然大人到此間,把我冤情對你說,正能替我報仇冤。
楊令婆辯十本(潮曲):臣妾一本奏冤情,為保社稷之功臣,仁君后愛安臣等,須念江山坐龍廷。

圖5:敦煌莫高窟172窟盛唐時期《觀無量壽經變》
(三)潮腔、潮調與潮劇聲腔體制形成
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詩詞北曲勾欄荔鏡記戲文全集》坊告:“前本《荔枝記》字多差訛,曲文減少,今將潮、泉二部增入《顏臣》、勾欄、詩詞、北曲,校正重刊”;并有方言劇本《荔枝記》、《荔鏡記》刊行,一些曲牌還注明“潮腔”,雛形的潮劇己確為形成;接著萬歷九年(1581)潮州東月李氏編集《新刻增補全像鄉談荔枝記》和民間《重補摘錦潮調金花女大全(附〈蘇六娘〉》刊行,《重補摘錦潮調金花女大全》劇且用“潮調”冠于書名,可知潮腔、潮調在明代中葉以前已經形成和盛行。一般認為,潮腔、潮調產生是潮劇從正音戲脫胎為潮劇的標志。通過嘉靖刊本《荔鏡記》與萬歷《荔枝記》、《金花女》對比研究,聯曲體結構在嘉靖到萬歷時期發生丕變,即從聯曲體中滾唱滾調的大量運用,形成潮劇對偶句的聲腔體制。從微觀分析,聯曲體這一變化發展情況由《荔鏡記》嘉靖本到萬歷本的演變情況可以看出軌跡,萬歷本聯曲體結構已經較大改變:(1)出現無曲牌的音樂,曲牌大量減少:嘉靖本曲牌76支,萬歷本則只有15支,同時代的萬歷刊本《金花女》則只有10支;(2)尾聲多不存在;(3)下場詩則大為減少,有的變為七言二句,有的則融入腳色中。可以說戲劇的發展在形式上更為寬松,而更加適合劇情化需要。由于萬歷本出現大量的無曲牌音樂,所以戲文中“唱”、“白”標志十分清楚。嘉靖本中,有曲中或二曲之間穿插詩句的例子,一種是以七言四句、五言四句出現的“暢滾”,也有以二句出現的“加滾”,萬歷本則大量出現“子母句”句式,可以見到這種潮劇音樂中對偶句的曲調形式的發展歷程。再由“對偶句”的聲腔體制的運用,到在外江戲的影響下潮劇又從聯曲體變為“聯曲板腔”綜合體,直至新中國成立后廢除童伶制促使聲腔丕變,進入20世紀五六十年代潮劇發展的“黃金時代”。
注釋:
[1]逍遙天:《潮音戲的起源與沿革》,廣東省藝術創作研究室編:《潮劇研究資料選》,1984年版,第 152頁。
[2]吳國欽、林淳鈞:《潮劇史》廣州:花城出版社 ,2016年版,第48頁。
[3]張伯杰:《談<掃窗會>的源流和音樂》,廣東潮劇團編:《掃窗會》,北京:音樂出版社出版,1959年版,第138頁。
[4]俞為民、孫蓉蓉編:《歷代曲話匯編》:新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清代編.曲海總目提要,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版,第1273頁。
[5]蘇子裕:《弋陽腔發展史》臺北:“國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134頁。
[6]筱三陽:《潮劇源流考略》,《潮劇研究資料選》,1984年版,第78頁。
[7][12]李平:《南戲與潮劇——兼,與新版<辭海>正字戲、弋陽腔釋文商榷》,《潮劇研究資料選》,第240、251頁。
[8][9][40]饒宗頤:《明本潮州戲文五種》說略,明本潮州戲文五種,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15頁。
[10]徐渭:《南詞敘錄》,俞為民、孫蓉蓉編:《歷代曲話匯編》新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明代編(第二集),合肥:黃山書社,2009年版,第481頁。
[11]王驥德:《曲律》,俞為民、孫蓉蓉編:《歷代曲話匯編》第75頁。
[13][14]逍遙天:《潮音戲的起源與沿革》《潮劇研究資料選》,第132頁。
[15]饒宗頤總纂,逍遙天分纂:《潮州志·戲劇音樂志》,潮州: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編,2008年版,第3831頁。
[16]逍遙天:《戲劇音樂志》,《潮劇研究資料選》,1984年5月,第26頁。
[17]陳蕾士:《潮樂絕譜“二四譜”源流考》,《潮劇研究資料選》,第157頁。
[18]陳蕾士:《潮樂絕譜“二四譜”源流考》,《潮劇研究資料選》,第 174-182頁。
[19][20]黃玉生:潮州二弦演奏藝術,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6年版,第250、260頁。
[21][38][39]陳守繼:《廣東正字戲與弋陽腔的淵源關系》,劉禎、錢貴成、裴建勤主編:《弋陽腔新論》,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6年版,第288、290、292頁。
[22]錢南揚:《魏良輔南詞引正校注》漢上宦文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頁。
[23][37]流沙:《從南戲到弋陽腔》,《明代南戲聲腔源流考》,王秋桂主編《民俗曲藝叢書》,臺北施合鄭基金會1998年版。
[24]溫丹銘:《溫丹銘先生詩文集》,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352頁。
[25][26]逍遙天:《潮音戲的起源與沿革》,1984年版,第128頁。
[27]逍遙天:《潮州戲劇志》,《潮劇研究資料選》,1984年版,第40頁。
[28]饒宗頤:《道教與楚俗關系新證》,饒宗頤:《饒宗頤史學論著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頁。
[29]陳勃:《潮汕話底層語言中的苗瑤語遺存初探》,《嶺南文史》2011年1期第19頁。
[30]饒宗頤總纂,逍遙天分纂:《潮州志·戲劇音樂志》,第3629頁。
[31]海豐縣戲曲志編寫組:《白字戲志初稿》,海豐縣戲曲志編寫組,1986年版,第12頁。
[32]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北京:團結出版社,2006年版,第1頁。
[33][34]饒宗頤:《道教與楚俗關系新證》,饒宗頤:《饒宗頤史學論著選》,第129頁。
[35]劉枝萬:《中國民間信仰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74年版,第131頁。
[36]容世誠:《潮劇扮仙戲的<六國封相>新加坡的演出觀察》,容世誠:《戲曲人類學初探:儀式、劇場與社群》,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頁。
(作者單位: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廣東無線網絡運營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