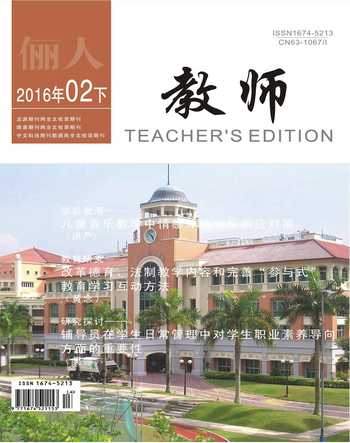解構的文本
陳乙寧
【摘要】余華的《一九八六年》通過對傳統敘事的顛覆,消解了傳統的二元對立結構,在重復敘事中實現了“用敵對的態度看待現實”,在文本思想和表達上均體現了解構主義的“反成規,反理性、反傳統”特點。
【關鍵詞】余華 解構主義 二元對立 文革
《一九八六年》中作者用瘋子的眼光展現了“文革”后異化的世界,人物、事件、情節都是處于非理性,非常態的現實生活之中,在創作主體的死亡——作家的零度寫作和故事主體的解構——中學歷史教師身份的消解之基礎上實現了二元結構的消解和意義的不確定,體現了“反成規,反理性、反傳統”的解構主義特點。
一、二元對立結構的消解
余華在《一九八六年》中設置了一位本是知識分子﹑啟蒙者的中學歷史教師變成一位瘋子的形象,通過由瘋子一條線及其妻女個和眾人一條線這兩條平行而又糾結的復線貫穿,一面形成緊張的對峙關系而推動了情節的發展,一面同時進行了解構,實現了對傳統“絕無兩個對項的和平共處,其中一項在邏輯、價值等方面統治著另一項,高居發號施令的地位”[1]二元結構的消解,萬事萬物都是處在相互平等,相互補充的地位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滲透關系[2]。
(一)清醒與渾噩
該小說中的瘋子不是傳統意義上渾噩的代名詞,相反是徹底沉醉在虛假的永恒的“春天”的眾人缺乏了感知的能力。“十年前那場浩劫如今已成了過眼云煙,那些留在墻上的標語被一次次粉刷徹底掩蓋了。他們走在街上時再也看不到過去,他們只看到現在”[3],余華在影院和展銷會上盡情描畫了迷失在物欲享受的眾人。而瘋子清楚地記得過往的一切,在他眼前的世界還是和從前一個色調,充滿著血腥和暴力。對周圍也有著最靈敏的感覺,太陽是“一顆輝煌的頭顱,正在噴射著鮮血”,樓房是“一座墳墓”,水泥路“像一根新鮮的白骨橫躺在那里”……他用自己的生命為代價,在街頭一次次痛苦的自戕中,讓眾人聽到從不知方向的遙遠的地方傳來“在昏黑的夜間行走是聽到的駭人的聲音”。這聲音正是他在十年前被人半拖半拉的聲音,也是現在已經麻木沉醉在新世界的“沒有皮肉只有骨骼的人”行走的聲音。
(二)刑者與被刑者
瘋子的自戕行為建構起了兩組刑者與被刑者:瘋子和他自己,瘋子與眾人。瘋子自身是在像“吹著口風琴”一樣陶醉的施刑者,在影院里﹑展銷會上,瘋子以啟蒙者的姿態,用臆想和街頭的酷刑表演,他揮舞著手中的“刀”,盡情地向施用著“劓刑”﹑“斬首”、“刖刑”、“烹煮”、“剝皮”及“剖腹觀心”各種酷刑。作為“文革”的唯一銘記者,他臆想著懲罰健忘的眾人,同時也是“渾身像篩谷般抖動著”一樣痛苦不可自持的受刑者。面對要將他捆綁起來的眾人,他只是費勁地微微抬起頭來看著他們,沒有絲毫的抵抗能力。他的啟蒙是失敗的,是悲哀的,無論他經受了多大的折磨,給眾人帶來怎樣強烈的震撼,卻敵不過善于“健忘”和麻木的看客。
通過兩組刑者與被刑者構成了權利者與反權利者的悖論關系,消解了刑者的權威。權力摧殘人的肉體以昭顯權威之時也恰恰反映了其內在的無力與懦弱,無法征服反抗者的精神與思想,既在說文革,也具當今意義。
(三)歷史與現實
該小說有三組敘事時間,發生在十多年前的文革,當下的初春,還有這十多年來的間隔。作者并沒有按正常的時間發展順序展開,而是打破了時空的限制,三組時間穿插進行,甚至對時間地點的切換都沒有清晰的交代,作者任意切換鏡頭,不僅僅是為了語言表達的游戲,增添情節的緊張感。
在瘋子的眼中過去、現在和未來,不同地點都處在同一個結點,呈現的是瘋子眼中已然混亂的時空世界。給我們帶來了強烈的碰撞和痛感。文章主人公在同一個瞬間“他看到自己在洗腳,有看到自己正在師院內走著。同時有看到自己坐在這里”,在家里的溫馨,突然被帶走的張皇失措,被懲罰的當下三個畫面同時浮現,強烈表現了主人公遭受“文革”直接打擊的突然與無措,表現了文革中瞬息萬變的世界給他帶來的反應力缺失。十年后回到故鄉街頭的他,看到的馬路上人們的行走竟是“他們的腳踩在滿地的頭顱和血肉模糊的軀體上”。他將對國人文化的關懷和對過去了十多年的“文革”與當下的現實生活融為一爐。歷史、刑罰并不是外在于主人公的歷史事件,不是一個抽象的或者已經徹底遺忘在過去的概念,歷史就是現在,歷史也是將來。
二、意義的不確定
解構主義理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意義的不確定或對終極意義的否定。這個特點在余華的小說中表現得十分明顯,語言在本質上是修辭的、隱喻的,而不是指稱和表達的。首先表現在如前文所講的具有游戲性的“瘋子”的概念,意義的不明確還體現在余華的重復敘事,以此拆解了作品權威的、固定的意義內核,使作品呈現完全無法歸納和統一在一個中心的多種意義,從而將文本分解成碎片。
《一九八六年》處處充滿隱喻和象征,最突出地表現在意象的使用上。除了最顯著的刑罰這一意象的使用,通過瘋子在街頭的刑罰表演,連接了歷史和現實,溝通了文明、秩序與人性、暴力,是打開詭秘世界的鑰匙。寓意豐富的還有貫穿全文的窗口意象。一開始主人公在被關著的房子里感到徹骨的寒冷,可是看到窗戶明明是關著的,再認真一看,原來是一塊破了的窗玻璃讓風灌了進來,再仔細一看,原來這塊玻璃是僅存的一塊,那些干凈得像不存在的窗戶原來真的不存在。反反復復一來一去,讓讀者的閱讀體驗隨著主人公的精神狀態跌起滑落,最后在窗口中看到的吊死的人一幕把人徹底逼瘋,以緩和漸進的方式構成了對苦難的消解,沒有強烈的沖突之感,但實際上也蘊含著“文革”對人深刻的傷害。而后文革結束了,新的春天和過去的文革之對比也是通過窗口這一意象實現的,余華諷刺著健忘的現在。他女兒所看到的“自己家中那敞開的玻璃如何閃閃爍爍了”的窗戶就像有了屏障和保護的現在與呼嘯著寒風的過去徹底絕決。但在窗邊的女兒看到了瘋子在街上進行的自戕表演,就像他之前在窗戶看到的殘忍一幕,瘋子向窗口里的人重演了令人顫栗的過去。窗口連接起了過去和現在,連接起了他和女兒,連接起了真實與虛偽。
“我的經驗是寫作可以不斷地去喚醒記憶,我相信這樣的記憶不僅僅屬于我個人,這可能使一個時代的形象,或者說是一個世界在某一個人心靈深處的烙印,那是無法愈合的疤痕”[4]。余華通過對中學歷史教師這一人物身份的顛覆,淡化了小說情節,濃墨重彩地渲染血腥,采用了“虛偽的方式”,透過瘋子來呈現他眼中的文革和他個人的生命體驗,把“文革”這一歷史的“宏大敘事”轉變為個人化的理解,用敵對的態度對現實進行解構,“這種形式背離了現狀世界提供給我的秩序和邏輯,然而卻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實”。
【參考文獻】
[1]高燕:《德里達的解構主義初探》,出國與就業理論探討,2011年第18期)
[2]王洪濤:《論德里達解構主義的文學觀》,山東大學,2008年)
[3][4]余華:《余華中短篇小說集》,青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