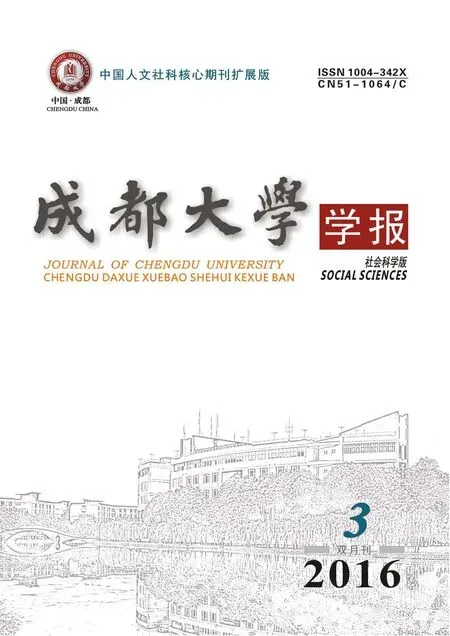大自然文學的文化“空間”*
王雅琴
(1.安徽行政學院, 安徽 合肥 230051; 2.吉林大學 文學院, 吉林 長春 130012)
?
·文藝論叢·
大自然文學的文化“空間”*
王雅琴1,2
(1.安徽行政學院, 安徽 合肥230051; 2.吉林大學 文學院, 吉林 長春130012)
摘要:劉先平是我國大自然文學的開拓者。在大自然文學中,自然與人是文學塑造的主要內容,同時也是作者著力表現的情感對象。自然與人之間并不是簡單的事物之間的關聯體,更是作者文學觀和價值觀的隱喻體。自然的在場、人的在場;自然與人的關系存在、價值生成都遠遠高出文學性和文學價值,從而構建了一個豐富的文化空間。這些文化空間的構成以文學作品為表征,體現出作家、世界與作品的關系,也展示了作品的文化生成和言說的開放性。
關鍵詞:大自然文學;文化;在場;解構;建構
安徽籍作家劉先平致力于大自然文學三十余年,出版作品四十多部,多次獲得各類國家級獎項并于2010年獲得國際安徒生獎提名。劉先平不僅著作豐碩、成就顯著,更是在文學界中舉起“大自然”文學的旗幟,以其“自然抒寫”展示了自然與人的關系、人對自然的態度以及自然與人的生存之道。從1978年創作《云海探奇》以來劉先平就以人為本,探尋自然與人之間的奧秘,追求“詩意地棲居”的美好生存空間。這不僅是其文學觀更是其人生觀和價值觀的表現。因此對大自然文學的研究,就不能僅從文學性上來審視,更應從文化的視角來探尋其社會性和文化價值。在大自然文學中,透過那一層層“自然”的迷霧,我們可以發現在自然與人背后構建了諸多層次的文化空間,這些文化空間的構成以文學作品為表征,不僅體現出作家、世界與作品的關系,更展示了作品的文化生成和言說的開放性,從而使大自然文學具有經典氣質。
一、在場——自然與人
劉先平曾多次提到自己的文學創作是直面生態危機,是用自然與人的和諧相處來傳達作者對理想人生的追求和向往。大自然文學不僅是作者生態文學觀的表現,更是作者人生觀和價值觀的體現。因此在大自然文學中大自然和生命的壯美是文學表征,更是作者情感所指符號。在大自然文學中存在著諸多關系,其中自然與人的關系是最為基本和永恒的關系項。
人類對自然與人關系的探尋,從古希臘的神話中就已經開始。在古希臘神話中神就是自然的象征:奧林波斯山上的十二主神如天神宙斯、太陽神阿波羅、海神波塞冬、豐收女神得墨特耳、月亮女神阿爾忒彌斯、農業保護神雅典娜等等這些神都是大自然的化身,而神與人的關系就是大自然與人的關系的表現,“萬物有靈論”中自然不僅富有人的特性,更是人的創造者和庇護者。人與神的和諧相處之時正是世界的美好時代。意大利哲學家維柯接受了埃及一個傳統歷史分期的看法,人類發展經過三個階段:神的時代、英雄的時代和人的時代。在神的時代中雖然人類已經產生,但“神—自然”無疑是占據世界的主導,而在英雄的時代和人的時代中人不僅逐漸取代“神—自然”成為世界的主導,更以其自身的各種矛盾成為人們書寫歷史的主要內容。從“神—自然”的主導到人的主導,人類歷史經歷了從對自然的崇拜到自然的退場和缺席。大自然從人類“以己度物”的“會說話的主體”轉變成“沉默的客體”。在這樣的歷史演變過程中,大自然與人不僅在中心地位上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而且更是一種哲學思辨的變化。
在大自然崇拜時期,人不僅是后于自然產生,更是自然產生的結果,大自然處于世界的核心和統治地位,正如宙斯作為天神的至高地位,人們以祭祀完成對“神—自然”的膜拜過程。當工具論出現之后,大自然經歷了去魅的過程,成為人們生存和生活的手段和工具,征服自然和占有自然成為人類走向邏各斯中心的橋梁。德里達的解構理論認為,中心的位置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流變不居的,“中心沒有自然基地,它并不是一個固定的中心點而是一種功能,是一種無中心點,在那里無窮盡的符號——替換物開始投入到差異運動中”[1]。在解構主義理論中,邏各斯中心主義者所說的那種位于事物和結構內部一成不變的中心只是邏各斯中心主義者的一種理論設想,“所以德里達說,沒有中心在那里,中心不能理解為是以某一呈現物,中心沒有自然基地,它并不是一個固定的中心點,中心不是中心”[2]。根據解構理論的理解,大自然和人并不是一種中心的置換,因為根本就沒有所謂的中心,“中心不是中心”。因此,在大自然文學中的大自然和人都并不是符號的象征,而是具有意義和價值的兩個沒有本源差別、沒有等級差別的二元項,兩者都是一種“在場”。

大自然在大自然文學中的主體化過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從1978年劉先平創作第一部大自然文學作品《云海探奇》開始到2013年的《西沙有飛魚》,大自然的形象不僅逐漸清晰、豐滿,而且更富有了生態美學的意味,它不僅以客觀形態出現更是富有情感色彩,是作品的主體。生態美學家曾繁仁曾說過在人類歷史發展中,“自然”經歷了“去魅”到“復魅”的過程,這種“復魅”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生態環境的變化及生態學發展的產物。后結構理論者德勒茲認為生成是一種弱勢生成,在他看來“社會中的強勢或弱勢族群不僅以一種量的方式對立,相反,‘強勢的’本身包含著一種表達或內容的常量、標準”[4],“強勢族群被分析性地包含于一個抽象標準中”“生成是一種弱勢生成”[5],如“生成—女人”、“生成—兒童”、“生成—動物”。按照德勒茲的理論,自然的“復魅”并不是回到神的時代中的那個萬能形象,而是人類邏各斯中心映照下的“弱勢生成”,正如同女人、兒童、動物一樣。自20世紀以來,生態危機不僅在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也逐漸引起發展中國家的重視,生態危機成為世界性危機。伴隨著這一社會性現象的出現,各種應對措施包括生態保護的研究也逐漸出現,生態學也成為顯學。在生態學視閾中,自然的“復魅”正是在生態危機現狀中出現的,并不是真正的主體而是人類強勢族群下的弱勢生成。但在大自然文學中,作者并沒有將大自然作為人類的一種弱勢生成,相反是將其作為平等主體的一項。正如德里達的解構理論中所繪制的沒有本源差別、沒有等級差別、動態化多元化的世界,事物之間不是決定和被決定的關系,而是一種“延異”(difference)。“延異”這個詞是德里達所創造的,雖然學者對這個詞的內涵闡釋并不統一,但“差異”無疑是該詞包含的重要內容之一,正是差異規定了事物間本質性的存在而不是規定性的存在。德里達還曾提出類似與德勒茲“弱勢的生成”的“他者”理論,但德里達顯然更重視多元關系之間的“延異”,因為這種“延異”是消除“他者”的方法之一,也是德里達追求的多元項共處的一種方法和原則,而這種關系恰好是大自然文學中作者所想要表達的大自然與人之間的關系,正如劉先平所說的“我把考察大自然看作第一重要,然后才是把考察、探險的所得寫成大自然探險紀實”[6]。不過在大自然文學中大自然顯然是以一種外在的、表征的、能指的、場景的符號“在場”,而人則是內在的、內涵的、所指的、精神的符號“在場”。
2.人的“在場”。文字是“心靈書寫”(psychical writing),這清晰地表達了文學作品與作者情感之間的關系。劉先平說大自然文學是大自然對他的一種召喚,而他的作品都是在長期的自然探險中的心靈感悟。在人類活動中,文學就是一種注重親身在場性體驗的活動。劉先平幾十部大自然文學作品中以第一人稱出現的“我”很少,作品中的人物也是融入大自然之中的,探尋大自然的規律,感悟大自然的奧秘,人似乎是大自然的追尋者,是一種“缺席”,但事實上,在大自然文學中,“人”與“大自然”一樣都是一種“在場”的存在,只是,“人”的“在場”要更為隱秘、更為多元和豐富。
與“惡”的較量。大自然文學中,人的“在場”首先表現在與“惡”的較量中。作為一種文學創作,一種虛構的藝術形式,善與惡的斗爭是必不可少的創作內容,但在大自然文學中的這種善惡較量要更為隱蔽。大自然與人的和諧相處顯然是作者所追尋的理想境地,但與之相對立的則是現實中的“惡”——生態環境的惡化。人的“在場”正是在與生態環境惡化的較量中充分體現出來。這種較量雖然并沒有像典型的生態文學文本中那樣鮮明、強烈的抨擊生態環境的惡化,但卻以人的“在場”來展示這種憂慮和思考,其中以“自然”為主要表現對象和情感傳達的敘事生成凸顯“在場的人”。事實上,“不存在作者聲音絲毫不介入的文學作品。作者在創作中不直接現身向讀者說話,卻往往將自己的意圖或傾向隱含于作品的敘事或抒情進程中,使讀者不知不覺中領略到作者的牢固在場。”[7]大自然文學中人的“在場”是一種意義性在場,是價值的生成性在場,它以作者的情感為基調表現出對生態環境惡化的憂慮和斗爭。事實上,事物的存在往往是處于一種關系之中,在與“惡”的較量中,“人”作為作者的代表,顯示出作者的情感與愛憎。福柯在《作者是什么》一文中“對傳統的作者概念作了層層辨析,進而提出作者不是一般的專有名詞而是話語的一種功能,是把一個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從話語的內部影響外部”[8]。由此可見,正是“作者”將作者的生態文學觀和價值觀處于作品之中,在與“惡”的較量中體現出了“人的在場”。
3.教育的在場。文學有認識、教育、審美等作用,其中教育作用強調文學的社會價值。大自然文學中的主人公多是少年兒童,從敘述視角來看,大自然文學可以被看成是兒童文學作品;但從接受視角來看,劉先平顯然并不僅僅是將少年兒童作為教育的對象,更是將整個人類作為教育的對象,因為與大自然相處的是整個人類。自20世紀以來,生態危機已經波及到全球,一方面人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生態危機的災難,另一方面卻又在不斷地制造新的生態危機。在經濟高速發展的追求下,“拯救地球”似乎只是空洞的口號。在大自然文學中,作者卻不是僅僅呼喊口號,而是以真實可信的現狀來展現這種危機和災難:被捕殺的黃鸝、十元進行的懶貓的買賣、鳥的買賣,因生態破壞動物食物的缺乏、竹子開花對熊貓的災難性影響、山林的頻繁起火砍伐等等,各種野生動植物數量的減少和消失。雖然作者并沒有用過多的話語來抨擊生態環境的惡化,但在作品中金絲燕、長臂猿、山樂鳥、白腰雨燕、麋鹿、大熊貓等野生動物數量減少、蹤跡難覓就是最為深刻的批判。在大自然文學中作者不僅以這些令人震撼的文學書寫來展現作者的憂慮,更是在教育讀者要行動起來做生態保護的行動者,特別是作品中所塑造的眾多人物形象為保護大自然而做出的努力,像小黑河、望春、李龍龍、劉早早、藍泉、小叮當、翠衫、林鳳娟等這些孩子形象,護林員老鄒、羅大爺、孫大爺、阿山等這些與大自然朝夕相伴的人物形象;陳炳歧、張雄、趙青河、王黎明、王陵陽,老楊、小羅、老范、小秦、小李、幕容、王三奇等這些為保護生態環境、探索生態規律而孜孜不倦辛勤工作的人物形象,都具有正能量。正是在這種人物和自然的互動中營造出和諧共處、共同發展的生存之道。因此,在大自然文學中作者一方面以“人的在場”展現出對生態危機的憂慮和痛心,另一方面又不斷渲染自然與人和諧相處的理想家園,在這兩種對比中作品中的教育意義更為鮮明,同時也是在不斷展現人類的在場。
二、建構——價值生成
大自然文學從大自然與人的關系出發,深入探尋大自然與人的存在關系,力圖尋找“美好家園”。在“美好家園”的建構過程中,大自然文學首先以文學的形式完成了對人類中心主義的解構,搭建起大自然與人關系的橋梁,并通過生態道德來完成美好世界的圖景構建。
1.二元解構。自柏拉圖的理念、黑格爾的絕對精神、笛卡爾的理性傳統,西方傳統哲學都建立了一個邏各斯中心,而在中心的對立面中設定了一個次元項。由此,“主體與客體相分離,認知者與他所認識的對象相分離”[9],“在笛卡爾那里,自然貶低為‘廣延的物質’,而人則被重新賦予‘思想的物質’,于是這種二元對立本體論上的鴻溝愈加深刻而永久”[10]。“二元對立其實是傳統哲學把握世界的一個最基本模式,而且,兩個對立項并非是平等的……其中一項在邏輯、價值等方面統治著另一項。”[11]在自然與人的二元對立中,自然和人類也并不是地位對等的雙方,而是人類中心主義之下的二元對立,也就是將自然置于人類之下,是工具理性世界觀的表現。
20世紀60年代開始,后現代主義逐漸在文化領域中興起,成為一種文化思潮,影響了諸多方面。在后現代主義文化思潮中,“解構”是其關鍵詞之一,它“對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工具理性、科學主義以及機械劃一的整體性、同一性等的批判與解構,也是對西方傳統哲學的本質主義、基礎主義、邏各斯中心主義等的批判與解構”[12]。在大自然文學中這種解構首先就是對人類中心主義的解構,對將大自然作為人類的“他者”關系的解構,對大自然與人類二元對立的解構。在作品中大自然不僅是描寫的環境,還是人物存在和故事情節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大自然的壯美和野生動物的生活情境是作品展開敘述的主體部分,與由人物構成的情節相比,大自然所展現的魅力和奧妙顯然要更為吸引人。作品中展現了野生動物之間的情愫:愛情、親情甚至友情,以及人與動物之間的情感。這些情感雖然是擬人化的,卻生動地展現了大自然的魅力。作者著力渲染這種情感甚至淡化作品中人之間的情感,如陳炳歧與方玲、趙青河與王黎明、東島上的小趙與小李的愛情,具有明顯的傾向性。在大自然文學中,大自然并不是“弱勢生成”,更不是人類中心主義中的“他者”,大自然和人一樣是美好世界的締造者。在大自然與人和睦相處的世界中,人類中心主義被懷疑、顛覆、消解。
2.價值生成。價值的存在和肯定來自于對立面的存在和肯定。人類的存在價值來自于大自然,大自然的存在價值也來自于人類,兩者并不是二元思維下的對立與抗爭、工具與目的,而是整體主義下的相互肯定和融合。德里達說一個事物或結構的中心并不在于它本身,而是在其他的東西。“一個符號的意義根本不是根之于它自身的內在性,如概念、所指等,而是根之于它與其他符號的差異關系,它的意義是由它的‘他者’所賦予的。”[13]這也就是說差異并不是事物間的隔閡,更不是促成二元項對立的原因,相反差異是促成事物之間關系的紐帶,是事物間價值存在的必要因素。因此,無論人在場或不在場、大自然在場或不在場,兩者都不是對立和抗爭的,而是從差異中走向彼此、走向有機和協同,正如懷特海所說的“我們在世界中,而世界也在我們中”,而事物的價值和意義也在雙方的肯定中實現。
1973年挪威著名哲學家阿倫·奈斯(ArneNaess)曾提出淺層生態學運動和深層生態學運動的說法。他認為:“淺層生態學是人類中心主義的,只關心人類的利益;深層生態學是非人類中心主義和整體主義的,關心的是整個自然界的利益。”[14]從本質上來看,淺層生態學實際上仍然是將人類置于世界的中心地位,是從人類利益出發,關注的是非人類對人類的貢獻和作用,在人類利益的終極目標下來看待大自然以及一切其他非人類事物,其思維方式遵循的仍舊是人類中心主義。正如“環境”二字,“‘環境’是在某個中心存在的外圍圍繞、服務、影響該中心存在的物質”[15]。事實上,“淺層生態學”也好、“環境”也罷,都是二元思維的產物,是人類中心主義的產物,而大自然文學則將從整體主義出發,將大自然與人置于世界的同樣地位,不僅關注環境惡化、生態危機,更“主張重建人類文明的秩序,使之成為自然整體中的一個有機部分”[16]。“解構”是后現代主義的關鍵詞之一,但在德里達的結構理論思想中,解構理論并不是單純的消解性的理論,而是一種建構性的理論指向,“他創立解構理論的目的就是為了徹底突破這種靜態封閉的壓制性的思想文化系統以期開辟出新的存在空間”[17],也就是說解構指向建構,因此,大自然文學就不只是停留在對人類中心主義的解構上,更是在建構整體主義。正因為有了這樣的意識自覺和哲學思維,劉先平才能在近四十年的大自然探險和文學創作中明確提出自然與人相處之道——生態道德,從道德層面上來完成價值和意義的建構。
生態道德下的價值生成。生態美學從主體間性出發,強調關系中的存在。在大自然文學中大自然與人的關系就是價值生成的基礎,“關系”指向生成。在人類中心主義的映照下,大自然是人類的工具和手段,兩者處于不平等的地位,不存在平等的關系,也就無法形成真正的和諧和統一,正如人類對大自然無節制的開發導致的生態危機。對于事物間的關系,德里達曾提出“蹤跡”(trace)的概念來指代事物間的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包容的關系,“蹤跡指的是在場的不在場,顯現的非顯現,表述的是事物或語言符號間,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相互映照的關系”[18]。也就是說無論是在萬能大自然的“神的時代”中,還是大自然缺席的“人類之上”之時,真正能促使大自然與人價值存在的是一種“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相互映照的關系”。因此,在大自然文學中并沒有過多展現驚心怵目的場景,而只是通過作品中人物的憂慮來表現作者的情感,更多的則是自然與人和諧相處、其樂融融的情景。人對于大自然、大自然對于人,都是相互的一部分,不僅在護林員老鄒、羅大爺、孫大爺、阿山等這些與大自然朝夕相伴的人物身上表現出來,還在那些關心大自然、保護大自然、探索大自然的人物如陳炳歧、張雄、趙青河、王黎明、王陵陽、老楊、小羅、老范、小秦、小李、幕容、王三奇等身上。正是在大自然與人平等關系的基礎上,價值才逐漸生成。大自然文學中主要的關系就是大自然與人,但這些關系的連接并非是簡單的結合,而是包含作者情感的道德指向。文學作品是情感的產物,凝聚著作者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在對人類中心主義的解構中、對大自然與人關系的連接中,作者不僅完成了文學書寫更提出了實踐操作方法——生態道德。所謂的生態道德就是人和自然相處時應遵循的行為準則。“建設性的后現代主義是一種科學的、道德的、美學的和宗教的直覺的新體系。”[19]生態道德首先就是一種道德的甚至是美學的、宗教式的目標,它注重自然與人相處時的關系法則,“只有生態道德才是維系自然與人血脈相連的紐帶”。文學不是單純地表達思想的工具而是思想本身。在劉先平的生態道德中體現了作者的整體思維而不是二元思維方式,看中的是大自然與人之間的關系而不是對立、抗爭,約束于道德準則而不是法律內,體現的和諧、交融之美而不是占有、征服之霸權。從藝術形態來看,這是一種美的追求;從實踐活動來看,這是一種生存方式;從形成結果來看,這是一種價值生成。
大自然文學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創作,經歷了近四十年的發展。從“文革”的陰霾中走出到對人類生存環境的憂慮和感悟,與其說是一種藝術表達,更不如說是一種人生探索。劉先平說過他把考察大自然看作第一重要,而在大自然文學中所設置的大自然場景由于是來自作者的親身體驗,因而顯得格外真實和可信。雖然作為文學作品,虛構是必不可少的,但在大自然文學中紀實性、探險性顯然要高于虛擬性,正是“目睹了大片森林被亂砍、亂伐、水土流失正在加重……自然生態嚴重破壞的惡果”[20],作者才能將真情實感寄寓于文學創作,并能正確認識大自然與人之間的關系。在大自然文學中,大自然與人作為兩個最為關鍵的要素都處于“在場”之中,不僅體現了人與世界、人與人、人與藝術之間的關系,更在文化的空間中探尋了大自然與人關系的構建、價值的生成。從這個角度來說,大自然文學的意義就不僅僅在于藝術性更在于實踐性。也正因為如此,對大自然文學的考察就不能拘泥于文學的視角,而更應結合作者的認識活動、實踐活動以及作者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從作品形成的文化環境中來考察和闡釋,只有這樣才能更好、更準確地把握大自然文學的真正涵義和當代價值。
參考文獻:
[1][13][17][18]肖錦龍.德里達的解構理論思想性質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3][6][20]安徽大學大自然文學研究所.大自然文學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
[4][5][8][11]朱立元.當代西方文藝理論[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
[7]劉陽.構的在場與文學的在場——兼論德里達在場理論對中國文學的反照[J].文藝理論研究,2011(1):125.
[9]【美】菲利普·克萊頓.從過程視野看作為后現代理論和實踐的生態美學[J].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3(7):43.
[10][14][16]郭繼民.生態倫理的本體論承諾——莊子與西方后現代生態哲學的會通[J].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9):6.
[12]劉文良.生態批評的后現代特征[J].文學評論,2010(7):81.
[15]劉青漢.生態文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9]邵金峰.生態美學的后現代特征[J].社會科學家,2010(11):17.
(實習編輯:徐雯婷)
On the Cultural Space of Nature Literature
WANG Yaqin1,2
(1.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hui Academy of Governance, Hefei, Anhui, 230051;2.College of the Humaniti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Key words:nature literature;culture;presence;deconstruction;construction
Abstract:Liu Xianping is the pioneer of the nature literature in China.In nature literature,nature and man are the main content of literature creation,and at the same time,it is also the emotional objects that the writer tries to show.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nd man is not only the relationship of things but also the metaphor of the author's view of literature and values.The presence of nature and man,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nd the value generation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literariness and the value of literature,thus building a rich cultural space.This cultural space is characterized by literary works,which refl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riter,the world and the works, and also shows the cultural creation and the openness of the works.
收稿日期:2016-03-10
*基金項目:安徽大學大自然文學研究協同創新中心項目;安徽省2014年高校優秀青年人才支持計劃資助。
作者簡介:王雅琴(1980-),女,安徽行政學院社會與公共管理系副教授,吉林大學博士后。
中圖分類號:I206.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4-342(2016)03-6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