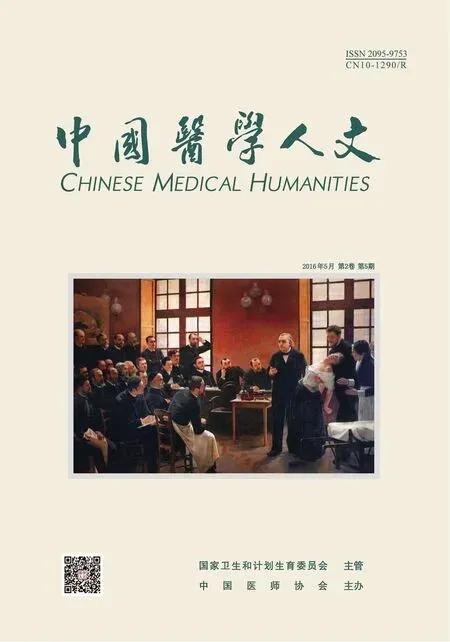以寧靜之姿 行喧嘩之中
文/余秋蓉
?
以寧靜之姿行喧嘩之中
文/余秋蓉
昔日詩僧寒山問拾得曰:世間謗我、欺我、辱我、笑我、輕我、賤我、惡我、騙我、如何處治乎?拾得云:只是忍他、讓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幾年你且看他。
巴赫金說,這是一個眾聲喧嘩的時代。在這個眾聲喧嘩的時代,醫患關系一次次被推上輿論之峰。醫生的培養和待遇,醫改的理想和現實,醫患的互存與互傷……激起一輪又一輪的波瀾。人們在爭論、在謾罵、在惋惜、在痛恨、在質疑,這既是對醫療,也是對社會,或許,更是對人性。
我們生活在一個眾聲喧嘩的時代,如果跟著喧嘩走,那么,必將迷失在喧嘩里。不如靜下心來反思。是誰錯了?也許,是我們自己的心錯了。“鼻有墨點,對鏡惡墨,但揩于鏡,豈可得焉?”真正的醫者,他絕不會在喧嘩中亂了分寸。因為他有定力,他的定力源自于信仰。
柴靜在《一百多年前的醫患關系》中寫道,1881年蘇格蘭醫生梅藤更來到中國,當時醫患關系的緊張遠大于今天。一方面是落后愚昧國人在就醫過程的種種不信任,一方面是內部醫護人員基于民族主義崛起背景下對西方文化的抵制,更可怕的是義和團事件后官方對傳教士的打壓乃至于屠殺,梅藤更在中國的從醫生涯可謂始終在鮮明的敵意籠罩之下。可他深耕以求生機,孜孜不倦,對所在醫院的要求有一條即是“創造力”:“不是一個破壞者,是一個建造者;不是一個說教者,是一個行動者。”熱衷于給人帶去照護、帶去歡樂、帶去安慰。護士傅梅生回憶,當年甚是勞苦,卻也相當寬展,因為竟可得到“病人對護士回報以毫無保留的信任和尊敬。”人心換人心,是一種幸運。換不來人心,卻也毫無怨言。真正的醫者,必定執守于對生命的敬畏和愛護。有足夠的信仰,才會有足夠的定力行走于喧嘩之中,而不變其心,不改其志。
或許每一個醫生,都經歷過不同程度的醫療糾紛。十余年前,我第一次經歷在門診被無理謾罵砸打,事后滿心憤懣委屈,自己關在屋里哭到眼腫,只覺社會不公。后來,師兄找到我,微微笑著說:“也能理解,病人把在醫院就診的悶氣集中發泄在你身上了。”我恨恨道:“真是好心沒好報,以后再也不做好人了!”師兄突然出奇的嚴肅,重重對我說:“你必須要做個好人!不管什么時候都要做個好人!”當時的我甚不理解,直到數年后看到2000年發生的德國人普方滅門慘案報道。事后在南京居住的一些德國人及其他外國僑民設立了紀念普方一家的協會,當他們了解到兇手——4個青年是由于貧困而產生的搶劫動機后,自此致力于募集捐款為蘇北貧困家庭的孩子支付學費、改變生活狀況,資助其完成9年制義務教育,希望給他們走上“自主而充實”的人生道路創造機會。記得讀于此處,頓感心下釋然。以惡止惡,如揚湯止沸,其有何益?惟有以善止惡,方是治本。醫者仁心,亦是如此秉持善之信仰,照護人類生命;進一步言,若能以善之信仰,救治人類精神,那更是踐行醫者正道了。
我們生活在一個眾聲喧嘩的時代,我們聽到的觀點太多,我們想表達的觀點太多,我們的心如此不安寧。我們指責政府,我們指責社會,我們指責醫生,我們指責患者,我們指責一切。大家似乎都病了,卻都看不到自己的病。就像有一個小笑話所講,精神病人不肯吃藥,還理直氣壯地問道:“明明是這個社會病了,為什么要我吃藥?”我們的病,就病在內心嗔恨,病在內心不安寧。若沒有足夠的智慧看穿真相,沒有足夠的信仰堅持方向,沒有足夠的力量去除內心的嗔恚,那又將如何行醫于世?
因病施治,是對患者,也是對亂象。在黑暗面前,無論是菩薩垂眉、春風化雨,還是金剛怒目、雷霆之鈞,都應該是以善為信仰。醫患關系,不需問“以德報怨,何以報德”,因為,好人,本來就是做給自己看的。
愿醫者,始終以寧靜之姿,行走于喧嘩之中。

命若懸絲 天壇醫院神經外科 攝影/汪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