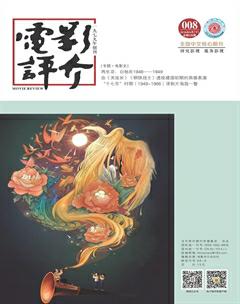兩版《洛麗塔》,誰更懂納博科夫
袁云博
美國后現代作家納博科夫的長篇小說《洛麗塔》于1955問世之后, 馬上成了20世紀50年代倍受關注、倍受爭議并給作者帶來極大榮譽的作品。因為《洛麗塔》的成功,納博科夫成為國際知名作家,《洛麗塔》也在半個世紀里兩度搬上銀幕。納博科夫是堅持追求純藝術效果的作家,他堅持認為:“毫無疑問,使小說不朽的不是其社會意義,而是其藝術,只有其藝術。”[1]所以納博科夫要用豐富的語言、精彩的細節、多彩的后現代手法,來渲染人物的悲情與愛戀,實踐其所提倡的“為藝術而藝術”的主張。因此,在《洛麗塔》原著中,精致璀璨的句子、巧妙的隱寓、化龍點睛的細節綴成全篇,將納博科夫的作品推向一個新的美學維度。正是因為納博科夫在《洛麗塔》里隱寓了太多的道德話語與藝術命題,小說《洛麗塔》才會于1962年和1997年兩度被搬上銀幕。
由斯坦利·庫布里克執導的1962版的《洛麗塔》(以下簡稱62版)和由阿德里安·林恩執導的1997版的《洛麗塔》(以下簡稱97版),分別采用不同的情節安排、不同的人物設計、不同的細節改編了納博科夫的經典之作。兩版《洛麗塔》既帶有導演自己對作品的理解,也呈現出美國不同年代的社會傾向和公眾道德的許可度。撇開電影技術的元素,單從電影的故事情節來看,就可以看出在處理同一部名著時,因為導演對原著認知的不同而呈現的差異。
一、 情節安排上的差異
首先,兩版《洛麗塔》都和原著一樣采用了以倒敘手法開頭、以順敘為主要敘事方法的方略,都從享伯特槍殺奎爾第開始講起,然后依然進入影片的以下橋段:享伯特入住黑茲夫人家時看到了洛麗塔,黑茲夫人死后享伯特與洛麗塔駕車出游,洛麗塔在路途中多次與享伯特發生沖突,洛麗塔最終在醫院里逃離了享伯特,三年后享伯特與洛麗塔再次相逢。在這一個個相似的片段里,兩版的導演也設置了相同的重點情節:如享伯特在電影院里和母女二人的“手戲”、激怒的黑茲夫人死于突發的車禍、享伯特與奎爾第在旅館里的相見、享伯特第一次與洛麗塔同床、享伯特大鬧醫院、享伯特與洛麗塔的種種爭執、最終以與奎爾第激烈而詭異的槍擊場面而告終。雖然兩版《洛麗塔》中有情節繁簡的不同,也有人物表演所產生的不同視覺效果,但在時間的順次上,都保持了基本的一致性。
兩版《洛麗塔》也有情節安排上的明顯差異,62版中沒有安排亨伯特和安娜貝爾相愛的那場戲,省略了對享伯特的戀童癖的心源性分析,也使享伯特的畸型愛戀更顯得沒有可以原諒的理由。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有著嚴格的電影審查制度,公眾的道德要求更傳統化,對于反傳統的、特別是享伯特與洛麗塔之間的帶有“亂倫”色彩的不良情感,壓根不會得到任何人在公開場合的肯定,這從庫布里克本來想讓喬伊·希瑟頓扮演洛麗塔,但是卻被喬伊的爸爸雷希瑟頓拒絕、亨伯特本來要由加里·格蘭特出演,也被他憤怒地拒絕這兩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公眾當時的道德傾向。基于上述原因,導演庫布里克必須帶著嚴肅的態度設計享伯特這個人物,這就是說,他不想為享伯特做道德上的解釋,也不能對享伯特表示任何的同情,所以62版才把享伯特少年時代與安娜貝爾的戀情省掉,讓他在觀眾眼里完全成了心理變態者,成了一個道德上的被批判者。而97版導演林恩與庫布里克的做法完全相反,他有意把亨伯特與安娜貝爾的戀情放在全片的開頭,用安娜貝爾飄逸的金發、純潔的眼神、在浪花中嬉戲的神態、掀起衣裙的羞澀把這段少年之戀渲染得相當唯美。表現出導演鮮明的情感:享伯特在少年失戀的心態中一直沒有走出來,才會對14歲的美少女洛麗塔一見傾心。如果能從心理學意義上為享伯特辯護的話,導演林恩一定會為享伯特找到充足的理由,使之得到心理上的關懷。
二、 人物戲份設計上的差異
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有著嚴格的電影審查制度,所以在開拍《洛麗塔》時洛麗塔的年紀被提高到14歲,比原著多了兩歲,據說這樣可以避免“戀童癖”所引起的公眾反感。除此之外,兩版《洛麗塔》和原著一樣,主要人物依次是黑茲夫人、享伯特、洛麗塔、奎爾第。兩版《洛麗塔》中,除了黑茲夫人和奎爾第的戲份差不多之外,則在洛麗塔與享伯特的戲份上出現了巨大差異。
(一)洛麗塔
庫布里克于1962年花費150萬美金買下《洛麗塔》的改編權,顯然是想用《洛麗塔》在當時的社會道德思考方面有所突破。基于當時嚴格的電影審查制度,庫布里克原來的許多話語無法實現,所以在62版中,洛麗塔的造型被觀眾指責為過于成熟,她梳著成年人的發型,穿著成年人的牛仔褲和襯衣,與享伯特相處的時候,她的裝束嚴謹而缺少風情。如在洛麗塔與享伯特第一次入住賓館時,洛麗塔一直天真地睡得很熟,即使侍者和享伯特那么麻煩地安放小床,也沒有能夠吵醒她。在后來長長的旅途中,62版中的洛麗塔都沒有大膽而刁鉆的挑逗享伯特,也沒有大膽地向周邊的人物發現色情的暗示,整個影片中他們二人之間最具性誘惑的情節僅僅是享伯特用手托起洛麗塔的小腳,為她涂抹紅指甲。因此,62版的洛麗塔從人物造型和演員選擇上,都沒有把洛麗塔“妖精化”,反而讓觀眾覺得洛麗塔成了一個弱者,她無法擺脫的享伯特的糾纏,成了一個被人誘拐而無法脫身的可憐小女孩。
在97版的《洛麗塔》中,導演林恩為洛麗塔增加了大量的戲份,讓她從一開始就以一個“小妖精”的姿態出現。97版中的洛麗塔是早熟的、放蕩的、惹事生非的、粗陋無知的壞女孩,14歲時她已經有了掌控男性的技巧,她敢于主動地用自己的身體向男性發起進攻。所以,在洛麗塔與享伯特的關系上,洛麗塔顯然占有著主動權,當她以全身濕漉漉的美少女形象出場時,注定會把享伯特的少年戀情勾引起來,讓他落入萬劫不復的畸情愛戀之中。所以導演為洛麗塔安排了許多挑逗的情景,如清晨的她進入享伯特的房間,故意高高地翹起右腿坐在享伯特的對面,把正在嚼著的口香糖粘在享伯特的筆記本上;又如在黑茲夫人、享伯特和洛麗塔一起蕩秋千的這場戲中,洛麗塔故意用腳面磨擦享伯特,還把嘴里的牙套丟進享伯特的酒杯,說明洛麗塔已是一個懂得向男性發出性信號的女性。在長長的旅途上,洛麗塔除了不停作怪(用腳拍打享伯特的臉、用嘴嚼子發出怪聲、用涼水猛激洗澡的享伯特)來折磨享伯特之外,她不斷地講著自己在夏令營里的荒唐事,主動地向身邊的任何陌生男性發出挑逗,弄得享伯特氣急敗壞,精神高度緊張,甚至出現了幻想癥。97版里還有洛麗塔要挾享伯特的鏡頭,比如她用撫摸享伯特下身的方法,使自己的零花錢從每周一美金長到了兩美金,她還會用“做到一半就漲價”的促狹手段,從享伯特那里拿到更多的現金。總之,97版中的洛麗塔有著十足的粗俗淫蕩,使她在這場畸型的愛戀中占據強勢地位,成了這場愛戀的掌控者與后來的殺人罪行的設計者。這正是林恩所要表達的話語。
(二)享伯特
無論在小說里還是在電影里,享伯特這個人物都不太會贏得同情與支持,更何況 62版的享伯特在演員選擇上就出現了偏差。1962年的詹姆斯·梅森已53歲,由他出演的享伯特顯得太老,影片中的享伯特刻板、僵硬、猥褻,笑起來有些發傻,眼神也沒有深情。從相貌外型來看,都與觀眾心目中的中年的風度翩翩的法語教授有一定的差距。這種形象的享伯特對年少美貌的洛麗塔心存邪念,極易讓觀眾產生反感和憎惡心理,這也許正是63版導演所要表達的隱性話語:一個美麗粗俗的少女與年過半百的老者之間的畸型戀情。影片中的享伯特一邊讀黑茲夫人的示愛信一邊狂笑的樣子骯臟猥褻,也加深了他的罪惡感。接下來享伯特在床上擺弄手槍,設想著殺死黑茲夫人的情景,以及黑茲夫人猝死后,享伯特泡在浴缸里愜意地咂著美酒的樣子,都讓享伯特的形象更加丑惡。所以,當他把剛剛失去母親的洛麗塔接出了夏令營時,他說出的那句“我很想你”的話干癟無味,更像是一場有預謀的事件,而不會讓人感動。影片結尾處洛麗塔面對哭泣的老享伯特,嚴厲地說出了“你毀了我太多的東西”,就是導演對享伯特所做出的批判。最終,暴怒的享伯特殺死了杰奎第,也可以看成是他對洛麗塔占有欲的極端表現形式。
97 版中的享伯特由杰瑞米·艾恩斯扮演,艾恩斯在1997年時也已49歲,但他身材瘦削,目光含情,從外型看去更接近儒雅又神經質的法語教授兼作家享伯特。這位來自于高校里的作家,是把14歲的洛麗塔當成他失去多年的愛人阿爾貝娜來欣賞,他欣賞穿著男襯衫打球歸來的洛麗塔,欣賞頭上纏著發卷半夜醒來的洛麗塔,同樣欣賞失蹤三年已淪為粗糙孕婦的洛麗塔。因為愛,享伯特快樂地為洛麗塔梳頭、洗衣、溫習功課,忍受著她的任性和無知。在與洛麗塔告別時刻,滿懷愛意的享伯特眼前仍然是那個鮮艷的小女孩。影片最后,滿臉血污、神思恍惚的亨伯特驅車到洛麗塔的家鄉,心里想的卻是:“我聽見山下孩童的笑聲,我難過的不是身邊沒有洛麗塔,而是這笑聲里沒有洛麗塔。”此情此景,突然讓人感到享伯特內心真誠的愛意和無助的悲哀,讓人頓生同情。
三、 細節上的差異
作為蝴蝶專家的納博科夫,從捕捉蝴蝶中發現了細節對于蝴蝶類別的重要性。因為,對小說細節的強調,成了納博科夫作品的標志之一。從細節的角度觀之,97版顯然大大優于62版,這并不是因為電影里加進了色彩的因素,而是因為導演林恩使用了大量的唯美細節。如在電影開頭殺人犯享伯特驅車行進時,林恩用大片的綠草坡、奔走的牛群、舒卷的云團來映襯滿臉血污的享伯特;如暴怒的洛麗塔雨中沖進冷飲店,林恩用緩緩打開的水果罐、正在流動的巧克力、跌入杯中的紅櫻桃來使方才激烈的爭吵停頓,也預示著下一個橋段里情節上的急劇轉換。在享伯特讀著洛麗塔來信時,導演用了一個長鏡頭掃過享伯特的房間,房間空蕩、凌亂,蜷縮在搖椅上的享伯特衣衫不整,說明享伯特的生活已被徹底改變,他早已不是那個在高等餐車里喝著紅酒的優雅書生。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幾次出現在鏡頭里的狗:享伯特第一次來到黑茲夫人門前,有一條狗沖過來狂叫,這為后來“為了躲狗而撞到了人”的車禍埋下伏筆;在洛麗塔第一次進入旅館時,奎爾第也是用狗誘惑洛麗塔;享伯特追趕雨中的洛麗塔時身旁突然沖出一條狗,顯示享伯特內心的慌亂;而當享伯特與成年的洛麗塔重逢,洛麗塔身旁有一條骯臟的長毛狗,這也洛麗塔最終命運的寫照。這些都是納博科夫小說里的暗示性細節,在97版的《洛麗塔》里得到保留。林恩設計的這些細節有效地濃化了享伯特的悲劇,那個趴在草地上、玩弄著濕淋淋的腳指頭的小女妖,成功把“粗俗少女”的美國少女形象搬上銀幕,也形成了全片最經典的細節。洛麗塔在這一瞬間營造的韻味,視覺的享受似乎要沖淡道德的桎梧,似乎在為男性的戀童癖做出最好的詮釋。
正如黃鐵池教授所言:“無論如何,納博科夫在《洛麗塔》中,以一種全新的觀察角度和表述方式,在文學作品中探索了人性的多樣性、復雜性和特殊性……在表達另類人物的痛苦與隱私方面,具有發人深省的獨特意義。”[2]林恩在自己的影片里對享伯特做如下解釋:享伯特對洛麗塔的所作所為確實驚世駭俗,但享伯特畢竟付出了真情,所以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也可以看能是一個特殊的愛情故事,可以從中獲得對人類命運思索和感動。因此,雖然97版《洛麗塔》仍有許多缺憾,但與62版相比,它畢竟往納博科夫的內心邁出了更接近的一步。
參考文獻:
[1]納博科夫.洛麗塔[M].黃麗萍,譯.伊犁:伊犁人民出版社,2000:75-76.
[2]黃鐵池.“玻璃彩球中的蝶線”——納博科夫及其《洛麗塔》解讀[J].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