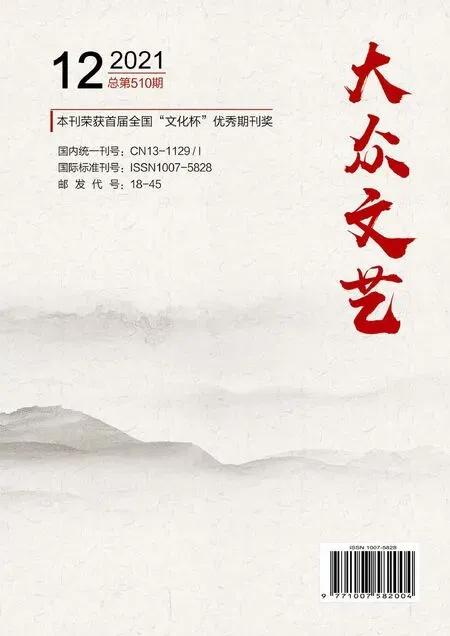對“中國畫”的一點思考
陳嘉欣 (浙江師范大學 321000)
對“中國畫”的一點思考
陳嘉欣 (浙江師范大學 321000)
面對一個事物時,我們往往以一種慣性的思維去解讀,然后嘗試在這個慣性思維的基礎上決定相應的問題,解決問題的關鍵或會被忽視。中國繪畫已處在與西方當代文化的接口上,中國藝術生態系統積極尋求通往當代的途徑。當代語境中,現代的觀念注入使繪畫形式改變,但同時表現出自我糾結。中國畫”這一詞匯,仿佛給我們一種無形的心理暗示,它似乎無形中與一種民族情感、民族文化掛鉤,并且把它當做傳統文化的守護,形成了限制它必須是一種規范。本文作為筆者的一點思考。
中國畫;歷史;解構;發展
什么是“中國畫”?或許學者們對于你的疑問都能地引經據典來闡述著他們的理解。他們普遍會帶著特殊的民族主義和感情,追溯中國傳統繪畫的歷史淵源,并把一系列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代入到“中國畫”這一詞匯的描述中。但如若對一件作品、一個藝術家或一個流派所處的社會與歷史結構缺乏了解,那對它的判斷就會變得缺乏依據,而變成純粹個人心理的記錄。“例如以2300年前的戰國帛畫的存在提示傳統繪畫的久遠與自身完整性。但是這些對遠古的追溯之于20世紀才使用的‘中國畫’這個詞匯沒有直接的關系,這就正如研究西方美術史去討論阿爾泰米拉山洞、拉斯科洞的圖樣與凡?愛克研制油畫沒有直接的關系一樣。”1
我們似乎忽略了一段歷史。“中國畫”這個詞與清末“國學”這個概念的出現時間應該很接近。“‘國學’,乃是外來語,并非國產。日本原有‘那支學’‘漢學’這樣的名詞,因此,十九世紀后期,留學日本歸來的學人,譯之為‘國學’,也就是‘中國學術’之意。”2在此并不多加論述。但無論在“國學”名下具有那么豐富的內容以及學派,“國學”這個詞的出現本身就已經表明,西方學術的進入構成了對傳統文化與思想的嚴重挑戰。其中康有為、陳獨秀及蔡元培等人對革新中國畫進行了探討,“以上三家的美術革命觀盡管不盡一樣,但我們依然可以清晰地發現他們之間的一些共同點:中國畫至近世已經衰微,必須改革,文人畫專重寫意、不上肖物的畫學正宗導致了人的精神退避,必須引進西方寫實主義,重新梳理中國美術傳統,以救援經濟、啟蒙國民,使其向著有利于人生的方向發展。”3
西洋畫隨著基督教傳教士來華傳教而逐漸在中國傳播。其實“中國畫”這一特殊詞匯正是開始于那讓人一開始有些抵觸的“西洋畫”進入中國之后的才有了產生與應用。“在晚清畫學中,這個詞更多地是中國的繪畫——‘中國之畫’——的意思,直至滿清政府被推翻、都市大街小巷里透露出更多‘西洋’氣息的時候,與‘西洋畫’相應的‘中國畫’一詞才開始為更多的人接受。”4可是,這個時候中國書畫家內心復雜的困惑 。后來畫家分別有三種表現。第一種為在社會生產的需求下,轉而學習西洋畫或圖案科等;第二種則為“折衷派”畫家,探討傳統與西方藝術的切入點;第三種則為以研究傳統國畫為己任。同時層出不窮的美術學校對“國畫系”“國畫科”以及“國畫”課的設立也進一步推進了這個含糊不清的新詞的使用。但縱觀歷史,畫壇對“中國畫”的探索不斷,徐悲鴻的“引西入中”、林風眠的“借洋興中”的實踐等;還是社會建設時期,畫家們被安排的外出寫生,李可染的“寫生求新”、潘天壽的“拉開距離”的主張,還是21世紀吳冠中“筆墨等于零”引發的爭論等探索,事實上還是對于“國畫”與“西畫”的交流問題。它無形地給繪畫藝術的交流加了一層心理暗示——西畫與國畫存在本質差異。
與解構的理論存在相似之處。“心靈是身體的牢籠”5。心理的枷鎖困住了人們突破常規的能力。如同一種無形的監獄,困住所有的可能性與自由。解構是打破固定模式,開創可能性。在被不斷的書寫的“蹤跡的蹤跡”后的組合體就是現在所看到的文本。所以這個文本與本身屬于那一個概念的東西存在著差異。一個詞的意義是從這個詞與其它的詞的差異中產生的,是一個無盡推衍的過程。每一個詞語的出現,都會使另一個詞被改變。對詞的意義來說,不可能有最終的、根本的確定。“中國畫”這一詞語,亦與其他的詞匯進行比較,同時得到自身的一個說法,但這個說法與其本質不一定是對等的。而且他是一個不斷比較從而得出結論的過程。那他其實并不是一個僵死的概念。正如德里達拒絕給“分延”下定義,因為一旦下定義就必須成為一個概念、一個中心。它不支配什么,也不統治什么。
“中國畫”這一詞匯的存在,必須承認已被廣泛被接受,成為一種民族驕傲。但要明白驕傲的是文化,而非詞匯。“魏茲提出‘藝術’是個開放的概念,新的藝術形式,新的藝術運動不斷出現,使藝術具有擴展性和探索性,而正是藝術中不斷出現的變化和新奇的創造,使得確定任何一套用以界定藝術的屬性在邏輯上都是不可能的,當然,人們可以選擇去封閉這一概念,但這樣做就封閉了藝術中的創造性條件,因而所有這些情況都將要求對美學感興趣的人們,是職業批評家們,去解釋還都擴展‘藝術’這一概念。”6作為一門繪畫語言,以民族的獨特性為由,可能不同意擴展這個概念,但這就難以把新的東西包括進來,那么這就意味著把一個東西接受為這個概念是有限制條件和約束的。
歷史總是不斷推進的,以前的經典成為今天的視覺經驗,成為一種規范。創新是在打破原有規范基礎上邁進一步,成為另一種規范。今天的我們或許會成為后人的一種規范,也或許會跟隨前人的規范,無聲無息地生活著。獨創性是打破該規律的一道鑰匙同時又導致另一場規范性的產生。古人的時代背景、思想環境是歷史賦予他們的禮物。現在時代變了,視覺經驗與思維模式也不一樣了。它是一種歷史選擇的合理性,是必然發生的。我們是歷史的產物,都是必然存在的,如同我們對“中國畫”的發展的迷惑,也是我們這個時代賦予我們的任務。
注釋:
1.呂澎.20世紀中國藝術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2:104.
2.曹聚仁.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生活·讀書·知新三聯書店,2012.7:003.
3.譚天.中國美學史新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10:299.
4.呂澎.20世紀中國藝術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2:104.
5.米歇爾·福柯著,劉北城譯.規訓與懲罰.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1:30.
6.朱王芬.莫里斯·魏茲“反本質主義藝術觀“批判性研究——兼論定義藝術的必要性[D].山東大學,2007.5:17.
[1]福柯,王育平譯.加里·古廷.譯林出版社,2013.6.
[2]宇文所安.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1.
[3]尼采著,賀驥譯.權力意志.漓江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