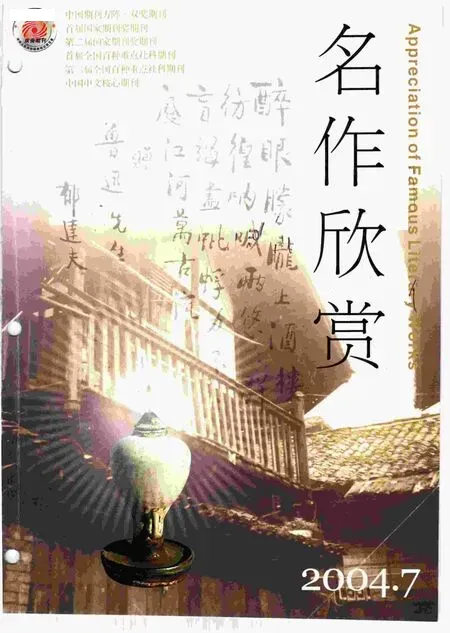炮制侵華文學的“國民英雄”火野葦平
北京 王向遠
?
炮制侵華文學的“國民英雄”火野葦平
北京王向遠
摘 要:火野葦平是日本侵華文學作者中的一個代表人物,因炮制侵華文學有功而被軍國主義宣傳機器捧為“國民英雄”。他的《士兵三部曲》(《麥與士兵》《土與士兵》《花與士兵》),站在軍國主義的立場上,美化歌頌侵華日軍,誣蔑丑化中國軍民,向數以百萬計的日本讀者傳達了侵華戰場上片面的乃至錯誤的信息,煽動了日本國民的戰爭狂熱,發行量逾百萬,并被改編成了電影,影響十分惡劣。
關鍵詞:侵華文學 “國民英雄” 火野葦平
一手揮刀、一手操筆的火野葦平
在侵華戰爭期間,提起火野葦平(本名玉井勝則,1907—1960)及其《士兵三部曲》,在日本幾乎是家喻戶曉。如果說,在日本的侵華文學中,最著名的人物是火野葦平,最著名的作品是他的《士兵三部曲》(包括《麥與士兵》《土與士兵》《花與士兵》),那是沒有異議的。《士兵三部曲》單行本出版后不斷重印,僅其中的《麥與士兵》當時就發行了一百多萬冊,成為罕見的暢銷書。這么大的發行量在日本前所未有,它竟使得瀕臨倒閉的出版商改造社一下子起死回生。不久,三部曲中《麥與士兵》和《土與士兵》被改編成電影,公開上映,影響更大,幾乎盡人皆知。當時有一首和歌云“《土與士兵》已看完,歸途炮聲繞耳畔”,反映了作品及其電影對觀眾的沖擊。火野葦平本人也深得軍部的賞識,被軍國主義宣傳機器奉為“國民英雄”。
在日本侵華文學的作者當中,火野葦平是少數幾個兼“士兵”與“作家”于一身的人。他在二十歲之前就曾寫作過長篇小說,出版過童話集,創辦過同仁文學雜志。二十歲的時候,作為“干部候補生”參軍入伍,后以“伍長”身份退伍。此后從事文學活動,1937年,發表以掏糞工人自強不息為主題的中篇小說《糞尿譚》以及詩集《山上軍艦》。同年,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作為“伍長”的火野葦平再次接到了入伍令,被編入第十八師團,參加了杭州灣登陸作戰。到1938年4月之前,一直作為杭州警備部隊的一員留守杭州城。
極為重視戰爭中的“思想戰”“宣傳戰”的日本軍部,是不會把火野葦平這樣的“文學者”作為普通士兵來使用的。1938年2月,已被軍部操縱的權威文學獎“芥川龍之介文學獎”,決定把本年度的獎項授給火野葦平的《糞尿譚》,并派遣著名文學評論家小林秀雄專程來到杭州,給火野葦平頒獎。日本軍部的這種超乎常規的行動,無疑是為了表明對“士兵作家”的一種特殊的鼓勵。是年5月,隨著徐州會戰的展開,火野葦平被派到“中支(即華中——引者注)派遣軍報道部”,主要從事戰爭的宣傳報道活動。他先是參加了徐州會戰,接著又參加了漢口作戰、安慶攻克戰、廣州攻克戰,1939年參加了海南島作戰。
此間,他以徐州會戰為題材,發表了日記體長篇小說《麥與士兵》(《改造》雜志1938年8月);以杭州灣登陸為題材,發表了書信體長篇小說《土與士兵》(《文藝春秋》雜志1938年11月);以杭州警備留守為題材發表了長篇小說《花與士兵》(《朝日新聞》1938年12月)。不久,這三部作品由改造社分別出版單行本,火野葦平總稱之為《我的戰記》,評論者也稱為“士兵三部曲”(日文為“兵隊三部作”)。隨后,他又以進攻廣州為題材,發表了《海與士兵》(后改題為《廣東進軍抄》);以海南島作戰為題材,發表了《海南島記》(《文藝春秋》1939 年4月)。1939年12月,火野葦平“榮耀”地從侵華戰場回國。接著,《士兵三部曲》獲朝日新聞文化獎、福岡日日新聞文化獎。他本人也到日本各地及琉球、臺灣等地做旅行演講。1941年又應關東軍的邀請,和川端康成、大宅壯一等人一道,為紀念“滿洲事變”十周年而到中國東北和北京游覽、講演。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火野葦平第三次應召參軍,作為“報道班”成員被派往菲律賓,后又被派到緬甸,1943年初回國。此間,一直到日本戰敗投降,火野葦平都是“戰爭文學”中最活躍的作者之一。
在侵華戰爭中,火野葦平以“士兵”和“作家”的雙重身份,一手揮刀,一手操筆,連續制作出不少侵華文學作品。在這些作品中,影響最大的還是他的《士兵三部曲》。當時“戰爭文學”作者作品眾多,為什么日本讀者對《士兵三部曲》最為青睞?這種現象本身就是耐人尋味的。那時日本全國都沉浸在如癡如狂的戰爭狂熱中,人們非常希望了解侵華戰場上的實際情況。但當時的“戰爭文學”絕大部分出自從軍作家之手,這些作家一般只在前線待幾周的時間,難以深入部隊中,缺乏實戰的體驗。而像火野葦平這樣既是作家,又是士兵,并且參加過徐州會戰等幾次重大戰役的人是很少的。上田廣也是身兼作家與士兵雙重身份,但上田廣一直在山西的日軍鐵道部隊,經歷比較單一,所以其作品的影響也遠不如火野葦平。當時有關的新聞報道和新聞紀錄片,表現的都是日軍如何節節勝利,特別是占領中國戰略要地或某某大城市的場面,缺乏對士兵生活的詳細報道和描寫。而日本國內的讀者,幾乎都有親朋好友在中國前線作戰,他們關心前線的士兵,希望了解戰場上的詳細情況,特別是士兵們日常的戰斗生活。火野葦平的《士兵三部曲》正是在這些方面適應了讀者的要求。
與此同時,日本的文學評論界對火野葦平的《士兵三部曲》也給予了異口同聲的贊揚。如評論家森山啟在《陣中文藝與文藝政策》(載《文學界》1938年9月)一文中認為火野葦平把“士兵寶貴的血與汗真正地滲透到作品中了”,同時又“閃耀著清醒的文學家的眼光”,所以《麥與士兵》等作品是“第一等級的戰爭文學”。三好達治在《麥與士兵的感想》 (載《文藝》1938年9月)一文中認為,是火野葦平的《麥與士兵》等作品“把新聞報紙上、電臺廣播中以及銀幕上沒有的東西,終于完美地送到了我們的手上”。北原武夫在《戰爭文學論》(載《文學與倫理》,中央公論社1940年版)一文中說:火野葦平的戰爭文學和其他的戰爭文學的差別,“就是在戰爭之中還是在戰爭之外的差別”;“火野葦平作為一名士兵服從軍隊的嚴格的紀律,并在這種紀律所規定的行為中了解了戰爭”,“他是一個作家,但又是作為一名戰士充分地融入了規定的行為之中”,這就是他的作品成功的原因。伊藤信吉和今日出海都認為,《麥與士兵》等作品的可貴之處就在于它們的“誠實”。今日出海說:“《麥與士兵》是作者……在蠟燭前不敢懈怠地寫成的日記。這個日記比幾百條戰爭新聞都更能夠打動我們的心,原因不正在于它的單純嗎?不正在于面對生死存亡,面對命運的那種誠實嗎?”(《戰爭和文學》,載《新潮》1938年9月)坂垣直子在《現代日本的戰爭文學》(六興商會出版部,1943年)一書中說:火野葦平只是描寫自己的真實的戰爭體驗,他的戰爭文學的寫作方法和過多強調勇武的寫法大有不同;“火野葦平的態度和方法,反映了現代日本的少壯作家的文學方法”,“在戰爭文學中如何強化作者的個性,火野是一個典范。心態的健康性和充滿生氣的富有彈力的睿智,在世界上也沒有先例。具有公正而又純正的文學感覺的戰爭文學作品,在日本誕生了”。
戰爭狀態下,日本軍部當局對火野葦平如此重視,讀者對火野葦平的《麥與士兵》等三部曲如此嗜愛,日本評論家如此慷慨地贊美,其更深層的原因,只能到作品里邊去尋找。
《士兵三部曲》對日本士兵的美化
《士兵三部曲》之所以受到日本讀者的普遍贊賞,首先在于火野葦平對日本士兵的描寫,正好投合了戰時日本人對士兵的心理期待。
《士兵三部曲》首先是侵華戰場上日本士兵的頌歌。在火野葦平筆下,侵華戰場上的日本軍隊是偉大神圣的軍隊,他們所向無敵,戰無不勝。置身于這樣的軍隊中,讓人感到一種力量和自豪——
我在這行進的隊伍中感到了一種雄壯的力量,仿佛那是一股有力的浩蕩洶涌的波濤。我感到自己身處在這莊嚴的波濤之中。在這廣漠的淮北平原,面對的是一望無際的麥田,我為踩在這片大地上的頑強的生命力而贊嘆……我將有力的雙腳踩在麥田上,眺望著蜿蜒行進的軍隊。那飽滿的、氣宇軒昂而又勢不可擋的雄壯的生命力撞擊著我的心扉……
士兵們在戰場上時刻都有戰死的可能,但是,為了祖國,他們隨時準備著死:
我覺得“祖國”這個概念在我的心中越來越偉大清晰了。這當然不是今天忽然產生的感覺。但是,特別是在最近幾天里,耳聞目睹了士兵們無法形容的艱苦,與此同時,在我的心中,我仿佛有了自己的思想。杭州灣登陸以來,直到現在的徐州會戰,像以往一樣,很多士兵倒下了。我親眼看到了他們的死。何時戰死無法預測。然而,在戰場上,我們從來沒有畏懼死亡……沒有一個人不珍惜自己的生命,我也更加熱愛自己的生命,生命是最可寶貴的東西……很多士兵有家庭,有妻子,有孩子,有父母。可是,在戰場上,不知為什么,這一切都容易舍棄掉。而且舍棄了也決不后悔……
(《麥與士兵》)
為了祖國而奮勇前進,這比什么都簡單而又單純。也是最崇高的事情。為此,我們前進。在戰場上,被槍彈打中將要死去的時候,大家嘴里只知道喊出“大日本帝國萬歲”這句話。
(《土與士兵》)
而這種不怕死的無畏,又來自對“支那兵”的“強烈的憎惡”——
我對于那些給我們的同胞造成如此艱難困苦,并威脅到我的生命的支那兵,充滿著強烈的憎惡。我想和士兵一起突擊,我想親手消滅、殺死他們。
(《麥與士兵》)
但是,面對著戰場上的險惡環境和艱苦卓絕,火野葦平并不是一味糾纏在“死亡”與“憎惡”中。總體上看,他是以一種樂觀主義的態度,把殘酷的戰場美化了。他特別注意表現戰場上的詩意和美感,他覺得:“和這些士兵一同在戰場上馳騁,真是快樂得很。”在他的眼里——
無論哪個士兵,肯定都是腳疼、胸悶,咬緊牙關艱難地行進。但是看上去,又是那樣英姿颯爽,那樣美。不,也許是我逐漸地感覺到了這種世上少有的美麗的情景。每一個都是那樣難以言喻的辛苦,但整體又是非常的美。不是看上去美,而是感到真美、真強、真勇。
(《土與士兵》)
不僅如此,火野葦平還極力在日軍對中國人的殘酷的屠殺中,體現出日本士兵的英勇來。一方面,他們把瘋狂屠殺中國人作為一種值得炫耀的美德,在給自己的孩子的書信中,自豪地宣稱:“爸爸就要殺那些支那人了。爸爸使用那把爺爺給的日本刀,像巖見重太郎(生于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的武士——引者注)那樣。等我把敵人的青龍刀和鋼盔帶回去給你當禮物好嗎?”(《土與士兵》)一方面瘋狂地殺人,包括已經放下武器的中國戰俘;另一方面,他又企圖在殺戮中表現日本士兵的“人性”之美——
在二十五里鋪的城墻前面挖掘的壕溝中,支那兵的尸體堆積如山。附近戰壕縱橫,麥田下面都挖有通道。這些膝射散兵壕似乎挖成不久,因土色尚新,也許是剛挖好的。堆積的尸體也都是血跡未干的新尸。尸體中有的在微微蠕動著。看到這種情景,忽然感到自己竟這樣漫不經心地麻木地看著這人間的慘狀。我愕然了。我變成惡魔了嗎?在戰場上,我真想親手射擊、斬殺支那兵,而且,我也屢屢射擊或斬死了他們。面對敵人的死尸,我又感到了一種悲痛和感傷。我覺得一陣寒噤,轉身離開了這里。
這就是日本人的所謂“菊花”與“刀劍”、“和魂”與“荒魂”的兩面,一面是殺人如狂,一面是唏噓感傷。火野葦平曾手書一個條幅,大意是:“強的東西,就是美的東西,就是悲的東西。”屠刀上面有菩薩,鮮血里面見佛陀,這就是日本人自《平家物語》以來形成的武士道的怪異的“審美”傳統。
在他的筆下,士兵們是那樣的單純,只要性命還在,他們就充滿著快樂。行軍或戰斗結束后,他們“互相充滿了慶生的快樂,大家嘻嘻哈哈地笑著”,洗澡、做菜,朝著東方,向他們的天皇“遙拜”。甚至在野外蹲著大便時面面相覷,都覺得那樣有趣。士兵們像兄弟般的親密無間,部隊長官對士兵也是那樣的關懷備至——
高橋一等兵躺在擔架上,抬頭看著我。說“班長,對不起,對不起”,說著,眼睛里噙滿淚花……“對不起”,我說了一句,眼淚也止不住流了下來。
(《土與士兵》)
部隊長一一看望傷兵來了。他只說了句“你們辛苦了”。但在他那表情上,卻又在說:干得好啊!那無言的感謝之情分明流露在部隊長的臉上。
(《麥與士兵》)
這就是火野葦平筆下的日本侵華士兵,既是那樣的英勇無畏,又是那樣的富有“人情味”;既有那樣的偉大的愛國精神,又是那樣的樸實單純;既是那樣的艱苦卓絕,又是那樣的樂觀自信;官兵之間既是那樣的上令下達,又是那樣互敬互愛。總之,儼然正義之師的形象。這就是火野葦平所要刻意表現的所謂“忠勇義烈的皇軍的形象”。火野葦平在表現日軍的這一總體形象的時候,比其他日本侵華作家顯然技高一籌:《麥與士兵》使用自言自語的日記的文體,《土與士兵》使用的是給弟弟通信的形式。因此,這里沒有其他侵華文學中常見的歇斯底里的叫喊和生硬的侵略戰爭的說教,而是從瑣碎的戰場小景寫起,盡可能顯得冷靜客觀、真實可信。日本讀者從火野葦平的作品里,找到了他們期待中的日本士兵的形象。
《士兵三部曲》中的中國軍民
在戰爭中,交戰雙方都希望了解對方的情況,火野葦平似乎很清楚這一點。在《士兵三部曲》中,火野葦平特別注重對于中國軍民的描寫。
他筆下的普通的中國,大都是徐州、杭州一帶及長江三角洲一帶的淪陷區。在對有關中國老百姓的描寫中,火野葦平著意表現了中國人的亡國奴相。在他筆下,中國人對日本侵略者沒有反抗。“無論在什么時候,什么地方,支那人一看見日本兵,就會照例做出笑意來。”(《麥與士兵》)當日本軍隊到來的時候,中國老百姓打著日本國旗,抬著茶水,歡迎日軍。他們不知道什么國家和民族,僅僅是被利用的工具——
附近村落中的避難的農民陸續到廟里來了。我們的部隊留在村落把土民全部集中起來避難……廟里擠滿了避難的人。老人和孩子燒了開水來到我們面前。他們端給士兵說:喝吧喝吧。廟里有一個村長,拿著裝飾過的長煙袋悠悠地噴著煙霧。那是一個長相有點嚴厲的老頭兒。翻譯正跟他說話。村長微微轉過身來答話,引起了一陣快活的哄笑。他說:這一帶蔣介石沒有來過,李宗仁和另外幾個大人物倒是帶著軍隊來過。要問拿出茶水招待嗎?不,我們不光招待日本人,中國軍隊來了的話,我們也招待。又問:那要是兩方面的軍隊都一塊來了呢?笑而答曰:那就跑啊。真是個直率而又狡猾的老頭兒。
(《麥與士兵》)
日本軍在其占領區召開所謂“難民大會”,讓中國方面的“代表”發言,說什么“我們老百姓從苛捐雜稅、橫征暴斂的國民政府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多虧了追求東洋和平的大日本國皇軍的庇護,使我們安居樂業,真是說不出的幸福”云云。雖然看不懂日軍的傳單上寫的是什么,但是為了討好日本人,他們一個個畢恭畢敬地從日軍手中接過傳單。面對這樣的中國老百姓,火野葦平的看法是——
我對于這些樸實如土的農民們感到無限的親切。也許是因為這些支那人與我所認識的日本的農民長得很相似。這令人無可奈何的愚昧的民族,被他們所不能理解的政治、理論、戰爭弄得暈頭轉向,但他們仍充溢著不為任何東西所改變的鈍重而又執拗的力量。他們一個個像比賽似的抹著鼻涕,把沾滿鼻涕的手在衣服上抹一抹,或用好不容易討來的傳單揩了鼻涕后丟掉。看到這可憐的農民,我心想:這就是我們的敵人啊,禁不住笑出聲來。
(《麥與士兵》)
在火野葦平看來:中國的老百姓根本就沒有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他們不把日本人的到來看成是侵略。為了證明這一點,火野葦平在《花與士兵》中,還通過一個中國人“肅青年”(實際上是個漢奸)的口說出了這樣的話——“中國的民眾和國家之類的一切東西都是游離的,和那些東西完全沒有關系……和日本軍隊的戰爭,民眾也看得與己無關。中國軍隊失敗了,民眾也滿不在乎。”并認為:“中國的民眾沒有自己可以保衛的國家。”對此,火野葦平感慨地寫道:
我們日本軍隊每占領一個支那城鎮的時候,留下來的支那人就到我們的駐地來,滿臉堆笑地和我們套近乎。這種做法我們是無法理解的。我想,這如果是在日本,敵軍攻來的時候,不是軍人的國民誰都不會討好敵人,連小女孩也會同仇敵愾地反抗,戰斗到最后一個人,直到以死相拼。所以,我們對“蘿卜”“咸菜”(作者對兩個漢奸的稱呼——引者注)為代表的支那人,單個的人覺得親近。但對這整個的民族,置本國失敗的命運于不顧,為了個人的性命而向敵人獻媚,是感到輕蔑的。用我們士兵的話說就是:都是些沒有廉恥的東西。
在這里,火野葦平把中國人中的漢奸敗類,看成是整個中國人的代表,把漢奸賣國的言論,看成是不刊之論了。我們不禁要問:如果中國就是這樣的國家,中國人都是這樣的軟骨頭,那就會不戰而降;如果是這樣的話,火野葦平及日本的軍隊又是在同誰作戰呢?
火野葦平還極力宣揚“皇軍”的“功德”。他借一個中國老太太的嘴,說:“中國軍隊每到一處,米、錢、衣服、姑娘,什么都洗劫一空。日本軍隊什么都不拿,非常好。”(《麥與士兵》)仿佛侵略中國的日本軍隊倒成了中國人的救星。在日本占領區,“皇軍”對中國老百姓是那么友好、文明。中國老百姓給他們水喝,他們硬是要付錢;雞蛋和蔬菜都是花錢跟老百姓買;中國老百姓的店鋪都開張,“景色悠閑竟令人不相信這里是戰地”(《麥與士兵》)。這一切描寫,無非是讓讀者相信,日本軍隊到中國來不是侵略,而是在“幫助”和“拯救”中國老百姓。
更有甚者,在《花與士兵》中,火野葦平還講述了一個名叫“河原”的日本士兵與一位名叫“鶯英”的中國杭州一家裁縫店的姑娘的浪漫的戀愛故事。河原救助了從馬背上摔下來的鶯英,鶯英愛上了河原,于是兩人戀愛,互相學習日語和漢語,最后決定結婚。為什么要和中國的姑娘結婚,作為班長的“我”(火野葦平)論述道:
我們現在的確在和支那進行戰爭。但是,戰爭的目的不是扼殺人間之愛,讓人們互相憎恨,而是為了我們兩國人民更緊密地握起手來。也就是說,現在兩國的戰爭就像兄弟吵架一樣。我們現在一面和支那軍隊交火,一面必須和支那民眾融合起來。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對于你和裁縫店的姑娘的事情,我不想因為她是敵國的姑娘就加以反對。我想說的只是:我們時刻不能忘記我們作為軍人的本分。
于是,河原就和鶯英結了婚,鶯英的家人喜出望外。從那以后,鶯英家的裁縫店就義務地為日本士兵們縫補衣服,日本士兵一個個“變得漂亮干凈了”。火野葦平正是通過這樣杜撰的故事,既說明了中國人沒有民族意識和民族自尊,也反映出日軍在中國的“文明”與“正義”,同時還把中國淪陷區描繪成了日本保護下的“王道樂土”,從而宣揚了“東亞共榮圈”及“大東亞主義”,可謂一石三鳥。
但是,侵略畢竟是侵略,火野葦平常常一不小心,便帶出了日軍在中國燒殺搶掠的真相。在《麥與士兵》的5月9日的日記中,火野葦平寫到了日軍滿地追著捉老百姓的雞,在老百姓的菜田里“收獲”蔬菜;在5月20日的日記中,寫到了日軍屠宰中國老百姓的豬;在5月15日的日記中,寫到了日軍所到之處,十室九空,日軍侵入農家,大肆入室搶劫;在5月17日的日記中,寫到日本人在麥田里捕殺中國農民,理由是他們與中國軍隊有“聯絡”;在《土與士兵》中,寫到了日軍放火燒房,并拉牛、捉雞,稱為“戰利品”;甚至,還恬不知恥地寫道:“我們自從登陸以來,糧食一回也沒分發過。反正我們走到哪里,都有中國米,也能捉些雞來,還有蔬菜什么的。”在《花與士兵》中,火野葦平還寫到了日軍侵入中國民居,由于不了解情況所造成的窘狀——
老百姓家家閉門鎖戶。只能見到零零星星的骯臟的支那人。來到石橋上一看,渾濁的河道上,有兩只糞尿船在通過。支那人不時地從建在石崖上的房子里,把紅漆的糞桶提出來,把黃色的糞尿倒在船上。我一看見紅漆的桶,就不由得打了一個冷顫。因為我意識到這是登陸以來最叫人生氣的一種失敗。原來,我們登陸以后,在支那每戶人家都看到了涂紅漆的漂亮的桶,我們就用它做飯桶,或者用它打水。那上面有泥金和黑漆的花紋,很干凈的樣子,而且有的還放在架子上。做夢也沒有想到那是便器,支那人稱為“馬桶”。我們知道后簡直驚愕得說不出話來……
這個情節至少說明了:日軍登陸后中國老百姓都棄家逃難了,日軍便侵占了中國老百姓的家,隨心所欲,為所欲為。
對中國抗日軍隊,火野葦平在誣蔑之余,也禁不住感嘆中國軍隊的勇敢頑強。《麥與士兵》中寫到一個中國兵,當日軍走近的時候,突然躍起來掏出一顆手榴彈,和敵人同歸于盡;《麥與士兵》在講到一次戰斗時寫道:“敵人非常地頑強。而且實際上勇敢得可怕。臨陣脫逃的一個沒有,還從圍墻上探出身體射擊,或者投擲手榴彈。很快又在正面和我們展開了格斗……”《麥與士兵》結尾處,寫到了三個被日軍俘虜的中國軍人——
敗殘兵中,一人看上去四十來歲,另外兩人不足二十歲。一問,才知道他們不但頑固地堅持抗日,而且對我們的問話拒不回答。他們聳著肩膀,還抬起腳要踢我們,其中一個蠻橫的家伙還朝我們的士兵吐唾沫。我聽說這就要處死他們,于是跟著去看。村外是一片廣闊的麥田,一望無際。前面好像做好了行刑的準備,割了麥子騰出了一塊空地,挖了一條橫溝,把被捆著的支那兵拉到溝前,讓他們坐著。曹長走到背后,抽出軍刀,大喝一聲砍下去,腦袋就像球一樣滾下去,鮮血噴了出來。三個支那兵就這樣被一個個殺死了。
在當時出版時,這一段文字被日本軍部的書報檢察機關刪除了。之所以被刪除,恐怕是因為它不但表現了日軍屠殺俘虜的情況,而且反映了中國軍人寧死不屈、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火野葦平寫到這樣的情節,主觀意圖當然不是為了表現中國軍人的英雄氣概。緊接著上一段引文,火野葦平寫道:“我移開了眼睛。我還沒有變成惡魔。我知道這一點,并深深地舒了一口氣。”這一段話作為《麥與士兵》全書的結尾,不過是在表明作者覺得自己還沒有變成“惡魔”罷了。
“人道主義”?“寫實主義”?
然而,火野葦平即使還沒有變成“惡魔”,也是和“惡魔”為伍,并自覺地為“惡魔”歌功頌德、樹碑立傳的人。正因為這樣,日本投降后他被判為主要的“文化戰犯”,受到了應有的懲罰。可是,當代有的日本學者以“我還沒有變成惡魔”這一句話為據,以出版時這句話及其他許多段落被軍部刪除為理由,認為“這可以證明”《麥與士兵》等作品“不是以軍國主義宣傳為寫作目的的”(見《日本文學鑒賞辭典·近代編》,東京堂1985年版,第677頁)。但是這種看法顯然不符合事實。為軍國主義侵略做宣傳一開始就是火野葦平寫作的出發點,一直到日本戰敗后,他對此也沒有反省。他堅信日本發動的戰爭是為了“建立大東亞新秩序”,認為日本的士兵在戰場上的所作所為是偉大的,是值得贊揚的。他在戰后寫的文章中仍然說:“很多軍人犧牲了,這尊貴的死絕不是白死。他們永遠活在真正的日本人的精神中。作為皇國日本的精神基礎早晚要發揮它的力量。很多的軍人死了,但實際上一個人也沒有死。”他還為自己的《士兵三部曲》等做辯護,說:“戰爭是以殺人為基調的人間最大的罪惡,最大的悲劇。這里集中了一切形式的犯罪,搶劫、強奸、掠奪、放火、傷害,等等,一切戰爭概莫能外,即使是神圣的十字軍的宗教戰爭,也可以證明這一點。作為一個作家倘若不立體地表現這一切,那么作為文學就很難說是完全的。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卡羅沙的《羅馬尼亞日記》、海明威的《永別了,武器》等作品之所以能打動我們,就在于以高度全面的人道主義精神寫出了這些戰爭的罪惡。”但是,對于火野葦平來說,問題不在于寫不寫戰爭的罪惡,而在于沒有把日本侵略軍的“罪惡”作為“罪惡”來寫,況且火野葦平從來沒有承認日軍的“罪惡”。所以在這里他無視戰爭的正義與非正義的本質區別,竟把產生于反侵略戰爭的文學名著拿來做自己的侵華文學的虎皮。
還有人認為火野葦平的《麥與士兵》等三部曲在某些地方表現了對中國老百姓的“同情”,表現了對戰死的中國士兵的憐憫之情,而認為這些作品所表現的內容是“人性的”,甚至是“人道主義”的(見吉田精一:《現代日本文學史》,筑摩書房,第155頁)。這種說法也實在是匪夷所思。人道主義是一種超越國家、民族和階級的對人的同情和愛,而火野葦平明明是一個軍國主義的擁護者,談何“人道主義”!事實上,所謂對中國老百姓的同情,不過是見了被日軍嚇得“顫抖”的抱著小女孩的老太太,而用日語說了聲“老太太,叫你受驚了”(見《土與士兵》)之類的事情;不過是對將被殘酷屠殺的中國俘虜的虛偽的憐憫。我國作家、評論家巴人在評論《麥與士兵》的時候,曾引用了作品中的這樣一段描寫:
兵士們有的拿出果子和香煙送給孩子,她們卻非常懷疑,不大肯接受。于是一個兵拿出刀來大喝一聲,那抱著小孩的女人才勉強受了。
巴人接著精辟而又一針見血地評論道:“這刀頭下的恩惠,卻正是今天日本所加于我們的一切。只有漢奸汪精衛才會奴才一般地接受的。火野葦平所宣揚于世界的,也就是相同于這類情形的大炮下的憐憫。”(見巴人:《關于〈麥與士兵〉》,原載《文藝陣地》第4卷5號,1939年)
還有的當代日本評論者認為火野葦平的《士兵三部曲》所描寫的內容是“真實”的,作品是“寫實主義”的,認為它們“絲毫沒有修飾和虛構,具有能夠再現真實的強烈的真實性,即一種強烈的現實主義”(見小松伸六:《昭和文學十二講:戰爭文學的展望》,改造社)。火野葦平自己在《麥與士兵·作者的話》以及《土與士兵》“前言”中,也都強調說:“我相信,能夠真實地描寫戰爭,是我一生中最有價值的事情。”他還聲稱,《麥與士兵》等“三部曲”是作戰的日記,而“不是小說”;《土與士兵》是寫給弟弟的信,“更不是小說”。也就是說,作品所寫,不是向壁虛構,而是真實。誠然,《士兵三部曲》采用的是寫實的手法,細節的描寫非常細膩逼真,但是,寫實的手法和細節的真實,并不等于作品是“寫實主義”的。因為,作為日本士兵的一員,作為指揮十幾個士兵的“伍長”,作為侵華日軍報道部的成員,火野葦平非常清楚他寫作這些“戰爭文學”的目的是什么。而且,軍部政府也對火野葦平這樣的士兵作家做了十分明確而具體的規定和限制。據火野葦平自己的記述,這些規定和限制主要有如下七條:
一、不得寫日本軍隊的失敗;
二、不能涉及戰爭中所必然出現的罪惡行為;
三、寫到敵方時必須充滿憎惡和憤恨;
四、不得表現作戰的整體情況;
五、不能透露部隊的編制和部隊的名稱;
六、不能把軍人當作普通人來寫。可以寫分隊長以下的士兵,但必須把小隊長以上的士兵寫成是人格高尚、沉著勇敢的人;
七、不能寫有關女人的事。
(轉引自《火野葦平選集》第4卷后記,創元社1958年版)
火野葦平顯然就是按照這樣的規定來寫的。按照這樣的規定來寫,還談什么“真實”,還談什么“寫實主義”呢?在《士兵三部曲》中,火野葦平寫了軍部所希望宣傳的“真實”,回避了軍部不希望披露的“真實”,因而是不可能真實反映戰場狀況,尤其是不可能充分反映出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的燒殺奸掠的真實情況的。
總之,火野葦平的《士兵三部曲》站在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的立場上,按照軍部的要求,美化日本侵華軍隊,歪曲地描寫中國抗日軍民,壯日本侵略軍隊的聲威。它向日本數百萬的讀者傳達了侵華戰場上的片面的甚至是錯誤的信息,煽動了日本國民的好戰氣焰,影響十分廣泛和惡劣。戰后幾十年來,《士兵三部曲》在日本又不斷被再版或重印,僅《麥與士兵》在戰后初期就發行了五十萬冊,至今仍擁有眾多的讀者。因此,對《士兵三部曲》做科學的分析和批判,對于正確認識日本軍國主義的侵華歷史,準確評價日本侵華文學,都是非常必要的。
作 者: 王向遠,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編 輯:趙斌 mzxszb@126.com
當代新青年
“80后”批評家:我們的觀點與立場 特邀主持:周明全
曾經有人戲說,世界上有三種人,男人、女人、女博士,其意在調侃女博士的怪癖。芳坤雖一路被學院教育規訓,但始終沒有消磨掉自己的天性,能說、會說、敢說。在當下批評界,能說會說者實在太多,但藏著、掖著,只揀好話說,敢直陳自己觀點的卻寥寥無幾。芳坤博士論文即為王安憶論,本文卻以犀利的筆鋒對準了她素日喜讀的研究對象。在她看來作為“50后”寫作的癥候之一種,《月色撩人》顯然是一部失敗了的“歷史之書”。文中敏銳甚至尖刻的批評隨處可見,例如:“王安憶小說創作頑強地與各路文學思潮匯合、分離,但始終面臨著終極的匱乏。她沒有讓雯雯們沐浴于時代探險的強光之下,而最終讓她們敗落于‘青春’的‘本次列車終點’,長久地駛入陰影之中。”但是,從這樣的判斷中,我們同時感受到了批評家對研究對象的善意和希冀。
芳坤有北方女人單純直爽的性格特征,亦有北方男性一般的豪氣。她的文字見心見性,文和人在芳坤這里得到了高度的統一。
——周明全,青年批評家
日本侵華文學研究(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