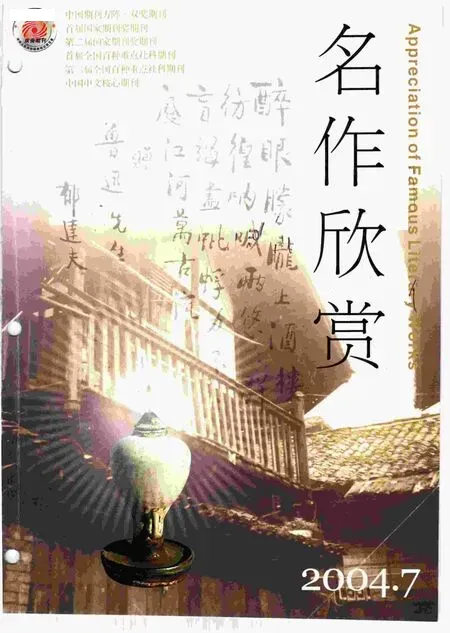影視觀眾的感性迷失與理性回歸——現(xiàn)象級IP劇《羋月傳》熱議引發(fā)的思考
北京 張文娟
?
影視觀眾的感性迷失與理性回歸——現(xiàn)象級IP劇《羋月傳》熱議引發(fā)的思考
北京張文娟
摘 要:本文聚焦《羋月傳》熱播熱議中存在的問題,重點(diǎn)解讀在《羋月傳》高收視低評價現(xiàn)實(shí)中觀眾的角色、地位和身份。文章從以下四點(diǎn)具體展開:一、收視率追逐中觀眾的角色:被出賣的觀眾;二、“皇帝的新裝”的隱喻:期待敢說真話的孩子喚醒大家;三、從廣告到影視熱點(diǎn):中國大眾正在經(jīng)歷媒體的深度催眠;四、浮士德式的難題:如何不靠出賣靈魂獲得快樂。本文揭示中國當(dāng)代傳媒現(xiàn)狀中影視觀眾正從感性迷失走向理性回歸,呼吁傳媒制作、傳播方關(guān)注觀眾的真實(shí)需求,以誠信著力打造品牌,告別現(xiàn)象級,提升文化產(chǎn)品的能量級,構(gòu)建影視傳媒的良性生態(tài)格局。
關(guān)鍵詞:《羋月傳》 觀眾 收視率 “皇帝的新裝” 媒體催眠 浮士德難題
2015年底至2016年初,談及中國電視劇的熱點(diǎn)事件,不能繞開的就是在北京、東方兩大衛(wèi)視黃金檔播出的古裝長篇巨制《羋月傳》。
談到《羋月傳》,首先我們要面對這樣幾個現(xiàn)實(shí)處境:
第一,這部劇由東陽市花兒影視文化有限公司、北京儒意欣欣影業(yè)投資有限公司、北京星格拉影視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聯(lián)合出品,鄭曉龍執(zhí)導(dǎo),孫儷、劉濤、方中信、馬蘇、黃軒、高云翔等眾多實(shí)力演員聯(lián)袂主演,可謂陣容強(qiáng)大。
第二,總共八十一集的《羋月傳》從2015年年底開始播出,算是陪伴電視觀眾“跨年”的大劇,隨著近一個月的熱播,該劇收視率直線上升,成為2015年電視劇的年度收視冠軍。《羋月傳》正在為其出品方樂視網(wǎng)帶來一輪熱播紅利,不久前,樂視網(wǎng)宣布《羋月傳》全網(wǎng)播放量突破一百億,目前樂視全平臺累積播放量獨(dú)占七十一億。臺網(wǎng)聯(lián)動,獲益巨大,讓所有參與利益角逐的個人和群體心滿意足。
第三,《羋月傳》未播先熱,開播后迅速占據(jù)微博話題榜首位,與高收視相悖的是,該劇口碑卻是一路走低,觀眾表示看后很失望,稱其沒有走出宮斗的狹隘格局;網(wǎng)友吐槽史實(shí)錯誤、情節(jié)重口味、劇情拖沓。該劇的網(wǎng)絡(luò)劇評分?jǐn)?shù)從播出前的8.7分下降到收官時的4.9分,成為近年來少有的“大劇口碑滑鐵盧”事件。觀眾普遍具有的感覺是翻了五味瓶,總有點(diǎn)不對勁,更有被欺騙的感覺。
以上這些現(xiàn)實(shí)的呈現(xiàn)確實(shí)發(fā)人深思。通過各種前期宣傳攻勢,網(wǎng)絡(luò)小說的人氣口碑,導(dǎo)演、演員、各種傳媒平臺與傳播方式的聯(lián)動,《羋月傳》成就了自己火爆的現(xiàn)象級熱門劇的地位,而在整個熱鬧的事件中,究竟誰是受益者?毫無疑問,首先是該劇的自制方與版權(quán)方,其次是提供平臺的電視臺和網(wǎng)絡(luò)。其他,不管是大導(dǎo)演、名演員還是觀眾,收獲的都可能只是熱鬧過后的一地雞毛。
回望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多年的發(fā)展,中國已經(jīng)進(jìn)入了物質(zhì)豐富甚至過剩的時代,但是這其中卻有一個悖論,首先是面對市場中琳瑯滿目的商品,人們出現(xiàn)了選擇的困難性;第二,商品數(shù)量雖然多,但是品質(zhì)難以保證,很多曾經(jīng)是廣告上大肆宣傳并由明星代言的,后來卻被曝光有嚴(yán)重質(zhì)量問題。這其中還特別包括食品安全問題。看上去是色香味俱全的,卻可能是騙子蒙混你的感覺器官、掠奪金錢的手段。商業(yè)背后整個利益導(dǎo)向的就是一個“錢”字。
同樣的狀況出現(xiàn)在精神產(chǎn)品特別是影視產(chǎn)品的現(xiàn)狀上。在上世紀(jì)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央視一統(tǒng)天下之時,雖然電視頻道少、節(jié)目少,卻有很多可圈可點(diǎn)的佳作給人們提供了精神大餐,是中國電視傳播史上第一個黃金時期。這其中包括對四大名著的改編,金庸小說改編為武俠劇等。上世紀(jì)90年代末以來,隨著電視劇的產(chǎn)業(yè)化進(jìn)程,從央視到衛(wèi)視到網(wǎng)絡(luò),影視產(chǎn)品數(shù)量之大,讓人目不暇接。各大影視傳媒利益集團(tuán),為了爭奪觀眾資源,展開了窮兇極惡的生死廝殺。借專家助陣、明星造勢、收視率造假、網(wǎng)絡(luò)狂轟濫炸等宣傳方式,最終不僅觀眾迷失了方向,電視臺、制作方、廣告商、導(dǎo)演、演員都共同迷失在傳媒亂象的迷魂陣中。
從物質(zhì)產(chǎn)品的消費(fèi)來看,在經(jīng)由時間展開、市場檢驗(yàn)、用戶受害等一次次血的教訓(xùn)中,老百姓已經(jīng)變得逐漸理性,知道從狂轟濫炸的廣告中稍稍撤退,自己明辨一下是非;從精神產(chǎn)品的消費(fèi)來看,因?yàn)槎嘣默F(xiàn)實(shí)取向,觀眾也有了更多自主的選擇,逐步不易成為廣告商和制片商手中的拉線木偶。但是從中國整個影視業(yè)發(fā)展現(xiàn)狀來看,在虛幻的熱鬧的精神垃圾產(chǎn)品之后,隱藏的仍然是編劇、導(dǎo)演、演員和觀眾深層的精神貧窮。
提到目前電視、網(wǎng)絡(luò)等傳媒中的各種亂象,我立刻聯(lián)想到這樣一些詞組:被出賣的大眾、皇帝的新裝、媒體催眠、浮士德的難題。下面我將結(jié)合《羋月傳》對電視傳播中大眾的角色做進(jìn)一步解讀。
收視率追逐中觀眾的角色:被出賣的觀眾
中國的收視率競爭大戰(zhàn)起源于20世紀(jì)90年代中后期,正處于計(jì)劃經(jīng)濟(jì)向市場經(jīng)濟(jì)的轉(zhuǎn)型,隨著電視臺及電視頻道數(shù)量的迅猛擴(kuò)張和電視媒介市場化的快速發(fā)展,電視收視市場的競爭加劇,收視率作為反映電視觀眾收視行為和偏好的主要指標(biāo),在節(jié)目編排、廣告投放決策以及電視節(jié)目評估中的作用越來越被業(yè)內(nèi)人士認(rèn)可,在這種背景下,中國收視率調(diào)查得以快速發(fā)展。對于收視率指標(biāo),從歷史發(fā)展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巨大的進(jìn)步,意味著中國電視開始關(guān)注老百姓對于電視的需求和評價了。在此之前,電視的評價標(biāo)準(zhǔn)是官方確定的,節(jié)目的編創(chuàng)者關(guān)注的是他們的節(jié)目能否獲得政府頒發(fā)的獎項(xiàng)。
收視率這個紅線,牽動著廣告商的廣告投放,牽動著電視臺的廣告創(chuàng)收,唯收視率論已成業(yè)界痼疾。在中國,收視率一直是個非常可疑的數(shù)字,因?yàn)槲覈氖找暵收{(diào)查非常不科學(xué),更有甚者,為了數(shù)字背后的金錢利益,收視率造假手段層出不窮。
收視率營造“觀眾中心”的虛假意識,以撫慰普通人渴望被媒體重視的脆弱心靈,又可以在與廣告商討價還價的時候提供商人能夠看得懂的或者確切地說能夠直接匯兌為貨幣符號的數(shù)字。想想觀眾在媒體傳播中的角色地位,真是別有意味:一方面,從表面上看,電視節(jié)目一直打著“滿足受眾需要”的旗號,觀眾是影視的欣賞主體,是可以選擇和評價電視節(jié)目的“上帝”;另一方面,觀眾又是電視臺以“收視率”這樣的數(shù)字賣給廣告商的產(chǎn)品。在電視節(jié)目欣賞中受眾的真實(shí)身份是:被迫出賣掉一部分自身的資源來換取電視節(jié)目給你帶來的信息、知識、審美、娛樂。那么觀眾所出賣的那一部分是什么呢?是時間,是“注意力經(jīng)濟(jì)”中的注意力,是廣告商“催眠式”的營銷方式中狂轟濫炸的包含高額利潤的產(chǎn)品,是長期被“媒體法西斯”占據(jù)的閑暇時光,這些被迫吃下去的精神垃圾食品,最后導(dǎo)致我們的價值系統(tǒng)混亂,又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加混亂。從前到后,我們都是在自己為自己買單并把自己送上不歸路。
這其中,第一步看上去是觀眾被電視臺賣給了廣告商,廣告商把觀眾賣給了生產(chǎn)商品的廠家,直接的受害者是觀眾;但是,隨著廣告商過分依靠收視率來投放廣告,電視臺為了提升收視率,一方面不惜下猛藥、支怪招、搶資源、降低品位、出賣社會底線換取收視率來垂死掙扎般吸引觀眾,另一方面又使出更為層出不窮的手段來制造虛假收視率,結(jié)果是廣告商也成了被欺騙者。最終,因?yàn)閻盒愿偁幒驼\信的缺失,電視生態(tài)慘遭破壞,電視臺和從業(yè)人員也出現(xiàn)了現(xiàn)實(shí)生存的重重危機(jī)。
不過,在當(dāng)今媒介融合時代,廣播電視均面臨著新媒體的劇烈沖擊。無論是節(jié)目內(nèi)容的傳播,還是受眾的媒介使用,跨平臺多終端已經(jīng)逐漸成為一種常態(tài)。所以目前的收視率大戰(zhàn)又有了新的變種。《羋月傳》能夠取得收視火爆,其中一個原因是它的一個獨(dú)特身份——IP①劇。近兩年,IP儼然已是熱門大劇核心。一時間,文學(xué)圈、游戲圈、影視圈無不覬覦“大IP”,唯恐慢了一步,失去的就不僅僅是IP這個主題,而是站在IP背后成千上萬的狂熱粉絲和他們不容小覷的消費(fèi)能力。IP原著經(jīng)過時間沉淀,積累良好的口碑和穩(wěn)固的粉絲,由此改編的電視劇或者電影自帶光環(huán),堪稱影視劇中的“富二代”。2016年開年已有報(bào)道稱“良心IP都被‘媒老板’買空了”,“IP資源遭遇瘋狂掠奪后正日趨枯竭”。 曾經(jīng)高舉“電視是藝術(shù)”的編導(dǎo)演員們,在嚴(yán)峻的市場競爭中已經(jīng)變身為商人、強(qiáng)盜、騙子、劊子手、叢林中的猛獸,真是可悲啊。
“皇帝的新裝”的隱喻:期待敢說真話的孩子喚醒大家
《皇帝的新裝》是丹麥著名童話作家安徒生的代表作之一。為了加強(qiáng)比照性,我們可以重新來溫習(xí)一下這個故事:一位奢侈而愚蠢的國王每天只顧著換衣服,一天國中來了兩個騙子,他們聲稱可以制作出一件神奇的衣服,這件衣服只有圣賢才能看見,愚人不能看見。騙子索要了大量財(cái)寶,不斷聲稱這件衣服多么華貴以及光彩奪目。被派去的官員都看不見這件衣服,然而為了掩蓋自己的“愚昧”,他們都說自己能看見這件衣服,而國王也是如此,最后穿著這件看不見的“衣服”上街游行。一位兒童說出了真話:“他什么衣服也沒穿啊!”故事中奢侈而昏庸的皇帝、虛偽而愚蠢的大臣、巧舌如簧的騙子和人云亦云的看客,對于當(dāng)今傳媒影響下的世界來說,真像一個莫大的隱喻。看看現(xiàn)在的廣告商和“媒老板”,他們真正關(guān)心的是經(jīng)濟(jì)效益,就像故事中的騙子;他們所鼓吹的影視作品就像故事中的皇帝;而所謂的專家、其他媒體就像是故事中的大臣,他們無意中充當(dāng)了騙子的幫兇;而觀眾就是那些人云亦云的看客。整個故事中,最大的亮點(diǎn)人物是那個敢說真話的孩子,他的一聲不受污染和干擾的最直觀的評價喚醒了眾人,使大家從迷夢中蘇醒過來。可是在中國的傳媒發(fā)展中,缺少的正是這樣一個響亮的聲音。
這讓我想到了一個典型事例,就是張藝謀和他的《金陵十三釵》。2011年我在美國洛杉磯南加州大學(xué)訪學(xué)期間,正逢張藝謀導(dǎo)演帶著他的《金陵十三釵》到校放映,讓我非常奇怪的是,觀者寥寥與國內(nèi)的造勢形成強(qiáng)烈反差。據(jù)導(dǎo)演說,“這部戲是我當(dāng)導(dǎo)演二十年來碰到的最好劇本”,“是我耗時最長、耗資最大、耗費(fèi)心血最多的一部電影”,并且集結(jié)“多國精英部隊(duì)”,廣受觀眾媒體專家一片熱捧,在中國大陸上映后,票房收入創(chuàng)下奇跡。后來我收到了美國教授給我發(fā)來的《好萊塢報(bào)道》上的一篇文章,同期國內(nèi)媒體在正面報(bào)道張藝謀上了《好萊塢報(bào)道》的封面,繼續(xù)為《金陵十三釵》造勢。可是當(dāng)我讀完了那篇文章,卻嚇出了一身冷汗,該文翻譯出來的意思是這樣的:好萊塢只有最愚蠢的三流導(dǎo)演才會在南京大屠殺這樣的災(zāi)難中用性來作為噱頭以吸引觀眾。②我徹底震驚了,同樣的一篇報(bào)道,國內(nèi)的媒體就是通過這樣的選擇性粉飾太平、混淆視聽,讓我們在《皇帝的新裝》的鬧劇中無法清醒的。美國著名電影批評家、哥倫比亞大學(xué)教授Emanuel Levy在《電影》雜志發(fā)表評論文章,批評《金陵十三釵》不是來自真實(shí)生活的靈感,而是張藝謀制造的一個雜亂、嚴(yán)重缺少平衡、過度炫耀某些場景的電影大雜燴(a hodgepodge of a movie),是張藝謀發(fā)跡以來最糟糕的一部電影。可以說美國媒體的角色就是《皇帝的新裝》中那個敢說真話的孩子。一部想要逐鹿奧斯卡的“戰(zhàn)爭史詩大片”,卻在北美點(diǎn)映后遭遇“滑鐵盧”,遭遇了近年來中國電影在美國所得到的最惡劣評論,最終在“情色”本質(zhì)被揭露的鬧劇中狼狽收場,更無緣奧斯卡。
相比《金陵十三釵》,《羋月傳》有同樣的借媒體造勢、夸大宣傳、混淆視聽的嫌疑。電視傳媒打著“滿足觀眾”的旗號,但是他們卻從來沒有了解過觀眾的真實(shí)需求。相反,他們滿足的是觀眾的 “偽需求”:他們把討好、迎合人性中“惡趣”的一面當(dāng)作觀眾的真實(shí)需求,把“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個人臆造當(dāng)作觀眾的真實(shí)需求,把媒體刻意制造的話題和事件當(dāng)作觀眾的真實(shí)需求。《羋月傳》播出之初,鋪天蓋地的通稿都在為《羋月傳》造勢,稱其是一部大格局之作。網(wǎng)友對于《羋月傳》的吐槽集中在對羋月這個核心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歷史上的大秦宣太后,是以一位女政治家的形象而立足,她的一生充滿傳奇,觀眾渴望能夠找到失落已久的能夠代表中華歷史精神與民族氣節(jié)的精神偶像,期待這部“史詩巨獻(xiàn)”能讓人產(chǎn)生一種蕩氣回腸的審美體驗(yàn),但編導(dǎo)者呈現(xiàn)的卻是宮斗,“整個故事都被一系列的小恩小怨小聰明小誤會小陰謀拖住了后腿,足以看出導(dǎo)演和編劇對于宮斗的熱衷,也足以看到其格局之狹隘和見識之淺薄,顯得格調(diào)不高,價值取向流于庸俗”。《羋月傳》直接可參照比較的是2013年的《甄嬛傳》,因?yàn)檫@是由原班人馬打造的。《羊城晚報(bào)》有文章評論“《羋月傳》開播收視高企,口碑不如《甄嬛傳》”,很多網(wǎng)評一致認(rèn)為《羋月傳》的服裝造型、精致妝容、后宮顏值、宮斗精彩程度等多方面都不如《甄嬛傳》。時間再往前推,2013年,《甄嬛傳》熱播時,《人民日報(bào)》就有文章對比《甄嬛傳》與《大長今》,稱后者“價值觀更正確”。韓劇《大長今》被稱為“2003—2005全亞洲收視最高的電視劇”,有人評價《大長今》是韓國走向世界的一張文化身份證,《大長今》最動人之處在于對于人的精神層面的重視。
中國電視的評價標(biāo)準(zhǔn),從最早的能否獲得政府評獎的政治標(biāo)準(zhǔn),到唯收視率是求的經(jīng)濟(jì)標(biāo)準(zhǔn),一直沒有回歸到真正的人文關(guān)懷中來。在缺少獨(dú)立思考、習(xí)慣他人引導(dǎo)型的模式中,觀眾選擇相信政府、相信利益集團(tuán)、相信專家、相信媒體炒作,缺少表達(dá)自己真實(shí)感受的勇氣。媒體從業(yè)人員包括導(dǎo)演和演員,在巨大的經(jīng)濟(jì)利益的誘惑下,有的半推半就,有的為虎作倀,都加入了騙術(shù)的狂歡交響中。可是為了中國影視的良性發(fā)展,我們再也不能繼續(xù)掩耳盜鈴下去了,希望有更多的類似《皇帝的新裝》中的孩子能夠揭穿騙局,結(jié)束鬧劇。
從廣告到影視熱點(diǎn):中國大眾正在經(jīng)歷媒體的深度催眠
催眠是用一定的誘導(dǎo)方法把人引導(dǎo)到特殊的心理狀態(tài)。某些連續(xù)、反復(fù)的刺激,尤其是語言的引導(dǎo),非常容易使我們從平常的意識狀態(tài)轉(zhuǎn)移到另一種意識狀態(tài)下時,我們會比平常狀態(tài)更容易接受暗示。自從弗洛伊德提出潛意識理論之后,潛意識對人的行為的影響已逐漸為人們所認(rèn)識,潛意識形成了我們行為的自動導(dǎo)航系統(tǒng)。催眠是一種非常有效的直接與潛意識交涉的技巧。催眠治療在心理治療中就是通過清理潛意識中的負(fù)面信息,幫助病人從心理障礙中釋放出來,達(dá)到生理疾病痊愈的目的。另外如祈禱、宗教儀式、印度的瑜伽術(shù)、中國的氣功術(shù)等都可以理解為是以不同的方式實(shí)施自我催眠。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父母給孩子的各種語言暗示和行為暗示,也可以理解為是施加在孩子身上的一場曠日持久的催眠術(shù),足以影響孩子的一生。
為了深入了解媒體對人的意識狀態(tài)的影響,我曾經(jīng)專門參加過催眠治療師的培訓(xùn)。經(jīng)過學(xué)習(xí),我最大的收獲就是提升了覺知水平,能夠主動從“被催眠”的巨大幻象中解脫出來。另外我也更加深入理解了媒體——特別是廣告媒體,是如何利用觀眾的潛意識,對觀眾進(jìn)行深度催眠引導(dǎo)消費(fèi)欲望、消費(fèi)習(xí)慣、品牌選擇的。關(guān)于廣告,麥克盧漢③認(rèn)為,它完全是一種“使消費(fèi)者神魂顛倒的猛攻無意識的‘洗腦程序’”。《新世界》一書的作者艾克哈特·托爾認(rèn)為“電視是由一群小我掛帥的人來主導(dǎo)的,所以電視有一個隱含的目的就是:利用讓你入眠來控制你,也就是說,讓你進(jìn)入無意識”④。因?yàn)橹袊娨暶襟w的強(qiáng)勢效應(yīng),加上中國人普遍缺少信仰,高度依賴媒體,所以當(dāng)代中國觀眾成了媒體催眠中催眠敏感度極高的人群(催眠敏感度越高的人越容易進(jìn)入催眠狀態(tài))。2012年初有這樣一則網(wǎng)絡(luò)報(bào)道:一個女孩的男朋友被人搶走了,其原因是男友嫌棄她胸部不夠豐滿(因?yàn)槊襟w上狂轟濫炸的廣告宣揚(yáng)的都是“做女人挺好”,這個宣傳已經(jīng)建構(gòu)了當(dāng)代人的審美觀),然后這個女孩就去豐胸,結(jié)果成功搶回了男友。婚后順利生子,皆大歡喜。但她聽媒體的報(bào)道說毒奶粉很多,出于偉大的母愛于是堅(jiān)持母乳喂養(yǎng),但不久孩子得了腦癱,因?yàn)樗呢S胸材料外泄,毒殺了孩子。類似這樣的例子層出不窮,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媒體傳播的價值觀念是如何成功地植入受眾潛意識,并成為他們?nèi)粘P袨榈摹白詣訉?dǎo)航機(jī)制”的。
現(xiàn)實(shí)生活中我們都處在一定的被催眠的環(huán)境中,所不同的是有的是給潛意識播種鮮花的“正向催眠”,有的是給潛意識種植毒草的“負(fù)向催眠”。每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主流價值觀,這和一個國家的政治、宗教、歷史、經(jīng)濟(jì)等因素有關(guān)。如果有一定的宗教信仰,我們可以理解為他們正處在相對的正向催眠系統(tǒng)中。2011年我在美國訪學(xué)期間,發(fā)現(xiàn)美國教堂之多、教堂活動之繁密讓中國人無法想象,每個周末,同一社區(qū)的人會聚集到一處,以他們自己特殊的方式進(jìn)行禮拜活動,包括唱贊美詩、聽牧師講道、為自己最近一段時間的生活向神禱告等;2012年,我去馬來西亞的馬六甲,看到移居馬來西亞的華人建了很多祖廟,包括關(guān)公廟、媽祖廟,被當(dāng)?shù)厝朔Q為“華教”,而馬來西亞當(dāng)?shù)刈疃嗟氖邱R來族穆斯林的清真寺;2013年我跟隨一些修習(xí)瑜伽的朋友去印度繞拜圣地,從城市到鄉(xiāng)村,從早到晚,此起彼伏,流淌著各種樂器伴奏的歡樂的唱誦。印度的很多神廟從早到晚每日開放,鄉(xiāng)下的農(nóng)民,最早凌晨三四點(diǎn)就到神廟中祈禱、唱誦。根據(jù)我的觀察,我不敢說他們都找到了真正的神,并且按照神的教導(dǎo)來行事,但至少,這已經(jīng)成為他們的一種生活方式,建構(gòu)著他們穩(wěn)定的價值體系和內(nèi)在豐富的精神生活。
轉(zhuǎn)型期的中國人普遍缺少自己的信仰,但是電視卻成了中國人的教堂和神廟,成了建構(gòu)人們精神世界的主要軟件來源,也成了主要的“負(fù)向催眠”系統(tǒng)。因?yàn)榕c教堂和神廟不一樣的是,教堂與神廟傳講的道是與“大我”同行、引人向善的“上帝之道”,而與商業(yè)利益結(jié)盟的媒體真正關(guān)心的是與“小我”同行、如何用坑蒙拐騙之法攫取金錢的“魔鬼之道”。靠電視來構(gòu)建的價值觀體系是非常矛盾、混亂和低級的,帶來的惡果是全民拜金主義、消費(fèi)至上、誠信缺失。觀眾強(qiáng)烈而天真地渴望媒體能夠成為他們精神救贖的引領(lǐng)者,結(jié)果卻一次次失望,在商家眼里,觀眾只是可以變現(xiàn)的商品。作為一個普通人,我希望自己能從這個負(fù)向催眠的環(huán)境中走出來;作為一名傳媒研究學(xué)者,我希望自己不要成為這種負(fù)向催眠的幫兇。
這次《羋月傳》的高收視反映的是媒介整合營銷的成功,在我看來,這是媒介催眠大師開始“下猛藥”了。以往業(yè)界依靠某一款單獨(dú)的作品或產(chǎn)品去贏得市場,而如今業(yè)界思考更多的是如何可持續(xù)地利用已有成就的作品,如何與市場發(fā)生更多的化學(xué)反應(yīng),如何實(shí)現(xiàn)品牌化。樂視的垂直生態(tài)體系推動《羋月傳》全方位的營銷,從媒體投放、衍生節(jié)目開發(fā),到定制產(chǎn)品開發(fā)等都能獲得樂視各個強(qiáng)勢子生態(tài)(樂視網(wǎng)、樂視視頻、樂視超級手機(jī)和樂視超級電視多屏終端)的推廣,讓《羋月傳》的IP價值得以放大,并深度運(yùn)營以挖掘IP的價值。最終樂視網(wǎng)也借助這樣的整合營銷策略讓自己成了最大的贏家。
浮士德式的難題:如何不靠出賣靈魂獲得快樂
在全國上下爭看“羋月”的鬧劇中,大家到底收獲了什么?從《甄嬛傳》的8.9分,到電視劇《紅高粱》的7.6分,再到《羋月傳》的4.9分,鄭曉龍導(dǎo)演近兩年的劇集網(wǎng)絡(luò)評分逐級出現(xiàn)下滑,金字招牌打了折扣。參與該劇的演員本希望借助《羋月傳》東風(fēng)再火一把,但由于該劇的網(wǎng)絡(luò)評分過低,使得這部大劇并未像以往一樣捧出幾個人氣明星。而對于觀眾來說,也上了新的一課:有大導(dǎo)演、名演員的電視劇不一定是好的;有很多人看的收視率高的,不一定是好的;有好本子拍成電視未必就是好的。
看到編劇、導(dǎo)演、演員以及觀眾在這場鬧劇中的困境,我想到了歌德筆下的浮士德。在歌德的《浮士德》⑤中蘊(yùn)含著一個困惑著幾代人的“浮士德難題”——怎樣謀取個人幸福而不出賣靈魂?這其實(shí)是人類共同的難題,是每個人在追尋人生的價值和意義時都將無法逃避的“靈”與“肉”、自然欲求和道德靈境、個人幸福與社會責(zé)任之間的兩難選擇。全劇由兩個賭局開篇:一是魔鬼與上帝的打賭,上帝認(rèn)為盡管人類在追求中難免會犯錯誤,但最終能夠達(dá)到真理,“在摸索中不會迷失征途”,而魔鬼認(rèn)為人類無法滿足追求終將導(dǎo)致其自身的墮落;二是浮士德與魔鬼的打賭,簽訂契約條件為:魔鬼滿足浮士德一切的欲望,一旦浮士德感到滿足,他的靈魂便歸魔鬼所有。《浮士德》中的上帝正是代表了人性中善良正義的一方,而魔鬼梅菲斯特卻恰恰處于對立面,是丑陋罪惡的化身。
歌德所處的18、19世紀(jì)是這樣一個時期:封建主義走向沒落、資本主義正在萌芽,人的理性主義、人文主義正在重新建構(gòu),多元化文化凸顯。與之相比,放眼20至21世紀(jì)轉(zhuǎn)型期的中國社會,伴隨著科技的高速發(fā)展、影視業(yè)創(chuàng)造出來的光怪陸離的世界的誘惑,當(dāng)今的人們,不管是媒體從業(yè)人員還是普通大眾,普遍面臨著與浮士德同樣的難題——如何在獲得快樂的同時不出賣靈魂?如果我們不想在一片“娛樂至死”的大潮中同歸于盡,我們就該嚴(yán)肅對待這個問題。在一切向錢看齊,要錢不要命,甚至寧愿出賣個人名聲和尊嚴(yán)也要把錢快速掙到自己口袋里的當(dāng)今時代,尤其值得警醒。“現(xiàn)象級”就是《泰坦尼克號》,在惡性電視競爭的生態(tài)格局中,被賣掉的不僅是觀眾,還有專家、導(dǎo)演、演員,大家將在脫下最后一件尊嚴(yán)外套的集體狂歡中走向滅亡。
美國著名的心理學(xué)教授,大衛(wèi)·R·霍金斯花了三十年的研究,發(fā)現(xiàn)存在于我們這個世界的隱藏的圖表,一個有關(guān)人類所有意識的能級水平的圖表。不論是書籍、食物、水、衣服、人、動物,還是建筑、汽車、電影、運(yùn)動、音樂等,統(tǒng)統(tǒng)都有一個確定的能量級。絕大多數(shù)流行歌曲的能級都在二百以下,大多數(shù)電影都把觀眾的能級降到二百以下的水平。世界上85%的人能級都處于二百以下,邪念會導(dǎo)致最低的頻率;而心存善念,保持一顆真誠、仁慈、友善、寬容的心則可以大大提升人的能量層級。層級越高,正面能量越大,獲得的成功和快樂也就越多。作為人類,我們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提升自己的個人意識能量層級。⑥
三十多年以來,我國“以經(jīng)濟(jì)建設(shè)為中心”的發(fā)展戰(zhàn)略取得了顯著的成就,提高了經(jīng)濟(jì)、科技、軍事實(shí)力等表現(xiàn)出來的“硬實(shí)力”,但是包括以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吸引力體現(xiàn)出來的“軟實(shí)力”卻顯得非常不足。長時間以來,人們有一種誤解,認(rèn)為“現(xiàn)代化=西化=全球化=美國化”,一切向“錢”看,以利益作為衡量一切的標(biāo)準(zhǔn)。在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體制日趨成熟的條件下,中國的社會轉(zhuǎn)型必然要求文化實(shí)現(xiàn)轉(zhuǎn)型。面對正在覺醒的大眾,編創(chuàng)者應(yīng)該展示更多的誠意,去發(fā)掘觀眾真實(shí)的需求,不要只是把目光聚集在短期效應(yīng)上,在“你方唱罷我登場、城頭變換大王旗”的亂象中,多一些文化堅(jiān)守,不與魔鬼做交易,而與天地宇宙大道同行,多傳播點(diǎn)正能量,多打造些品牌和長壽節(jié)目,這樣才能真正實(shí)現(xiàn)文化價值和產(chǎn)業(yè)價值的共贏,營造良性的文化產(chǎn)品市場。
①IP,即Intellectual Property,直譯是知識產(chǎn)權(quán),目前更多是指適合二次或多次改編開發(fā)的影視文學(xué)、游戲動漫等。
②原文見《好萊塢報(bào)道》,《The Flowers of War:Film Review》,12/11/2011, by Todd McCarthy:It's something you'd think only the crassest of Hollywood producers would come up with — injecting sex appeal into an event as ghastly at the Nanjing massacre —but it's an element central to The Flowers of War, a contrived and unpersuasive look at an oft-dramatized historical moment.
③〔加拿大〕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增訂評注本),何道寬譯,譯林出版社2011版。
④〔德〕艾克哈特·托爾:《新世界——靈性的覺醒》,張德芬譯,南方出版社2009年版。
⑤在歐洲幾千年的文學(xué)史中,豎立著四座豐碑:古希臘的《荷馬史詩》、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亞的戲劇,以及歌德的《浮士德》。《浮士德》是歌德傾其畢生精力完成的一部史詩性巨著。盡管“浮士德”的傳說在歐洲流傳已久,然而到了歌德這里,浮士德的形象更是歌德所屬時代的精神體現(xiàn)。
⑥〔美〕大衛(wèi)·R·霍金斯:《意念力:激發(fā)你的潛在力量》,李楠譯,光明日報(bào)出版社2014年版。
作 者: 張文娟,中國傳媒大學(xué)藝術(shù)學(xué)部副教授。
編 輯:趙斌 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