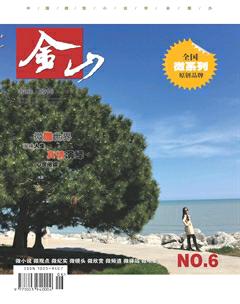讓新詩與傳統(tǒng)詩詞“并駕齊驅(qū),各擅其美”
卞祖玉
鎮(zhèn)江市近幾年以弘揚詩詞文化為主題,以創(chuàng)建“全國詩詞之市”為抓手,出版了《鎮(zhèn)江詩詞一百首》和多部詩詞作品集,拍攝《詩話鎮(zhèn)江》,編排舞臺劇《詩畫鎮(zhèn)江》,開展詩詞“六進”活動(進學校、進機關(guān)、進農(nóng)村、進社區(qū)、進企業(yè)、進軍營),旨在傳承和發(fā)揚好鎮(zhèn)江的優(yōu)秀詩詞文化。我以為“創(chuàng)建詩詞之市”,也要重視現(xiàn)代詩的普及,但目前校園里,街道旁,吟唱會上,詩刊、報刊上,幾乎全是古體詩詞,極少看到現(xiàn)代詩的蹤影。
《揚子江詩刊》原執(zhí)行主編、詩人黃東成同志說得好:“中國詩歌的健康發(fā)展,首要的一條,詩應(yīng)該而且必須走向人民大眾。”單靠推廣古體詩,很難做到“走向人民大眾”。毛澤東是詩詞大家,他在答復(fù)《詩刊》主編臧克家的信中寫道:“詩當然應(yīng)以新詩為主體,舊詩可以寫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為這種體裁束縛思想,又不易學。”事實證明他老人家的意見基本正確。
我曾在《京江晚報》上發(fā)表過兩篇短稿,題為《按譜填詞》《趙忠祥的七律有毛病嗎?》,建議報刊發(fā)表古體詩詞應(yīng)當合乎格律,反對不倫不類的“詩詞作品”。2015年夏,鎮(zhèn)江某報報道了某小學的詩詞吟誦創(chuàng)作活動,發(fā)表了該校師生創(chuàng)作的20首詩,或五言或七言,或四句或八句,表面上像格律詩,但沒有一首合乎格律,或平仄失調(diào),或韻腳不對。只有一首五律《春游長江路》稍好一點:“風動鶯驚去,櫻花片片飛。垂髫追紙鷂,怡悅笑開眉。遙望江中寺,氤氳繞廟扉。輕嘗君贈酒,醉倚錦羅帷。”所謂好,是指它平仄基本協(xié)調(diào),韻腳也押得好。缺點有二:一是沒有對仗句;二是“垂髫追紙鷂”的“鷂”是平聲,應(yīng)當用仄聲字。也許,他們發(fā)表的不是格律詩,而是新詩,那我就錯怪他們了。但是他們?yōu)槭裁匆扇「衤稍姷慕^句、律詩、五言、七言的表現(xiàn)形式呢?我們應(yīng)當指導(dǎo)中小學生寫新詩。2015年8月11日《新華日報》第8版刊登《童心的詩篇》30首,全是新詩,靈動,凝練,純樸,想象力非常豐富,多數(shù)是小學生,童心可貴,童趣可愛。例如第一首《樹》:“樹是泥土的信,一個個果子/是一個個字/風讀了又讀/把每一個字,都讀熟了,才讀懂了,泥巴的甜言蜜語”果實向人世發(fā)出豐收的信,甜蜜在泥土深處,在大地母親的心頭。
今年1月25日《揚子晚報》報道了“手寫三行詩”大賽頒獎情況,一等獎選手是力行小學二年級學生卞含章的《美麗的缺點》:“外星人說地球上有好多破洞真丑/走近一看/這些‘破洞真美”。她的靈感是從山西王家大院拍的“破洞”照片上獲得的,很有詩意,很有想象力,有逆向思維,看到“破洞”美。有人說,其中有哲學意味和美學思想。我想,這種“三行詩”南京小朋友能寫,鎮(zhèn)江小朋友也能寫。由于新詩易學,沒有古體詩那么多清規(guī)戒律,眾多現(xiàn)代詩人會大力支持,各行各業(yè)會涌現(xiàn)更多詩歌愛好者,青少年們誦詩寫詩的熱情也會高漲起來,鎮(zhèn)江的詩詞文化品牌就能做優(yōu)做大。
下面舉例說明古體詩詞確實束縛思想不易學。
我曾經(jīng)按譜填詞,寫過一首《相見歡·茅山“軍號”》:“當年‘打敵迎風,立如松。抗日新兵‘東進氣如虹。放鞭炮,聽軍號,響蒼穹。今日小康華夏又沖鋒!”(注:這是茅山獨具的奇觀。人們在“蘇南抗戰(zhàn)勝利紀念碑”下放鞭炮時,紀念碑上空便會響起清晰的軍號聲。聽說當年有位年輕的小號手就犧牲在這里。“打敵”:象聲詞,模擬軍號聲)由于字數(shù)、平仄、韻腳的限制,我在寫景抒情上受到許多限制,不能充分展開。一位本地詩人寫的新詩《爆竹·軍號》:“沉淀在碑石里的英雄豪氣/因此嘹亮了云霄/嘹亮了與那個年代/相距遙遠的心靈//司號者/因為吹響過驚雷、風暴/而沉寂,半個世紀/唯有松濤,如銅號上的,流蘇,一遍遍拂過/歲月的艱辛,拂過斤峰萬壑間的期盼//磨礪過革命的山脈/喂養(yǎng)過正義的叢林/在失血的歷史結(jié)束的時候/一個普通的山民/以生活的歡欣,終于/照亮屬于犧牲與勝利的聲音//活在號音中的英魂/在蒼鷹盤旋的高度上/加入到今天/另一種石破天驚的/凱旋”。這首詩是緬懷先烈的血色記憶,為時而作,有感而發(fā),讀來感人至深。
新詩沒有格律束縛,不問字數(shù)行數(shù),不問平仄對仗,比較容易學,也容易推廣(這是相對而言,并不否認推廣、創(chuàng)作新詩的另一類難處。去年江蘇首屆全國少兒詩會在兩個月內(nèi)收到45000余首少兒新詩,其中120首獲獎。這個事實證明新詩容易推廣)。新詩(包括敘事詩、抒情詩等)完全可以在鎮(zhèn)江創(chuàng)建“全國詩詞之市”進程中,和傳統(tǒng)詩詞并駕齊驅(qū)、各擅其美;在詩化鎮(zhèn)江的征程中,新舊體詩人同心協(xié)力,共享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