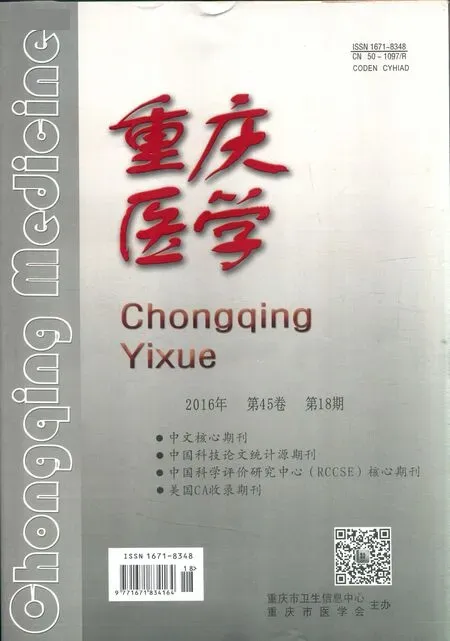血漿D二聚體、纖維蛋白原在糖尿病腎病中的臨床價值分析
徐曉宏,席志鳳,朱愛民,王軍升
(南京鼓樓醫院集團宿遷市人民醫院腎內科,江蘇宿遷 223800)
?
血漿D二聚體、纖維蛋白原在糖尿病腎病中的臨床價值分析
徐曉宏,席志鳳,朱愛民,王軍升
(南京鼓樓醫院集團宿遷市人民醫院腎內科,江蘇宿遷 223800)
[摘要]目的探討D二聚體(D-D)、纖維蛋白原(FIB)在糖尿病腎病(DN)早期診斷中的臨床應用價值。方法測定60例DN患者(DN組)及50例健康體檢者(對照組)的空腹血漿D-D、FIB及血肌酐(Cr)水平,并同時收集24 h尿液進行尿微量蛋白測定。根據尿清蛋白排泄率(UAER)將60例DN分為早期DN (EDN)組和臨床DN(CDN)組,比較各組對象的相關指標。結果3組對象的FIB、D-D、UAER水平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腎臟病飲食改良(MDRD)校正的腎小球濾過率(GFR)與D-D、FIB呈負相關,與UAER呈正相關,FIB與GFR呈負相關(r=-0.512,P<0.05),D-D與GFR呈負相關(r=-0.798,P<0.05),UAER與GFR呈正相關(r=0.397,P<0.05),相關系數D-D高于FIB、UAER,FIB高于UAER。結論D-D及FIB對DN早期診斷有重要的臨床應用價值。
[關鍵詞]D二聚體;纖維蛋白原;糖尿病腎病
2型糖尿病(T2DM)是一種臨床上常見病,凝血與纖溶系統紊亂在糖尿病血管并發癥的發生和發展中起至關重要的作用[1-2]。研究表明,糖尿病患者體內血栓前狀態與糖尿病進行性發展并累及心、腎等器官有密切關系[3]。腎臟代償功能強大,早期腎損傷臨床多無癥狀,常規實驗室腎功能監測指標普遍具有滯后性,血漿D二聚體(D-Dimer,D-D)是纖維蛋白單體交聯后再經纖維溶解酶水解所產生的一種特異性降解產物[4],它反映體內存在高凝狀態[5-6],血漿纖維蛋白原(fibrinogen,FIB)也是在體內出現高凝狀態和繼發性纖溶時的分子標志物[7]。本研究通過檢測糖尿病腎病(diabetic nephropathies,DN)患者的血清D-D、FIB水平,旨在探討其在DN患者早期診斷中的臨床價值。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選擇2012年1月至2015年6月本院門診及住院的DN患者60例,均符合2010年美國糖尿病協會糖尿病的診斷標準[8],近期未使用過血管緊張素轉換酶抑制劑(ACEI)或血管緊張素受體拮抗劑(ARB)影響腎功能的藥物,排除標準:(1)其他原因所致蛋白尿;(2)嚴重心腦血管疾病;(3)肝功能異常;(4)惡性腫瘤;(5)妊娠期及哺乳期;(6)自身免疫性疾病。按照Mogensen的DN分型標準[9],根據24 h尿清蛋白排泄率(UAER)將60例DN患者分為兩組:早期DN組(EDN組,UAER 20~200 μg/min) 27例,男14例,女13例;年齡35~69歲,平均 (55.4±5.7)歲;臨床DN組(CDN組,UAER>200 μg/min)33例,男18例,女15例;年齡39~76歲,平均(57.7±3.9)歲。同時選擇同期本院健康體檢者40例作為對照組,入選標準:(1)血壓、血糖、血脂均正常;(2)無肝、腎功能損害;(3)排除心、肺及其他系統疾病;(4)排除妊娠期及哺乳期;(5)未服用阿司匹林、雙嘧達莫等影響血小板聚集功能的藥物;(6)排除血栓、出血等病史,其中男21例,女19例;年齡35~72歲,平均(55.3±4.6)歲。各組對象年齡、性別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所有對象于清晨空腹取血檢測D-D、FIB、血肌酐(Cr)。采用酶聯免疫吸附測定法和凝血酶法分別檢測D-D、FIB水平,測定儀為美國ACL-100型血凝儀及其配套試劑。Cr采用肝素抗凝及酶法,試劑均由寧波美康生物有限公司提供,全自動生化分析儀為HITACHI 7600- 20(日本)。同時準確收集所有對象24 h尿液5 mL,采用免疫比濁法檢測尿蛋白總量,計算出UAER。操作過程嚴格按照說明書進行。D-D正常范圍0~0.55 mg/L,FIB正常范圍0~4.0 g/L,Cr正常范圍30~106 μmol/L,腎臟病飲食改良(modification of diet in renal disease,MDRD)校正的腎小球濾過率(GFR)公式計算如下:
GFR=186×Cr-1.154×年齡-0.203×0.742(女性)。


表1 3組對象各項指標檢測結果比較±s)
a:P<0.01,與對照組比較;b:P<0.01;與EDN組比較。
2結果
2.13組對象臨床檢測結果比較3組對象的FIB、D-D、UAER水平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兩比較中,EDN組與對照組FIB、D-D、UAER水平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Cr水平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CDN組與對照組FIB、D-D、UAER、Cr水平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EDN組與CDN組的各指標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2DN患者D-D、FIB、UAER水平與MDRD校正GFR的相關性兩組DN患者的D-D、FIB、UAER水平與MDRD校正GFR經Spearman相關性分析,FIB、D-D水平與GFR呈負相關(r=-0.512、-0.798,P<0.05),GFR水平與UAER呈正相關(r=0.397,P<0.05),相關系數D-D高于FIB、UAER,FIB高于UAER。
3討論
DN是T2DM最嚴重的微血管并發癥之一,是一種以血管損害為主的腎小球病變,主要以血管內皮損傷,血小板活化,微血栓形成和繼發纖溶亢進為表現,亦是導致終末期腎臟疾病的主要死因[10],其病理改變是腎臟高濾過、高灌注、腎小球基底膜增厚以及系膜細胞增生,從而造成腎小球結節性或彌漫性硬化[11]。Cr為臨床較為常用的腎功能監測指標,對腎功能早期損傷的診斷局限性也較為明顯,大部分患者Cr出現異常時,腎功能已處于失代償期[12],指標滯后性特點較為明顯,本次研究結果與之相符合。本研究結果發現,3組對象的UAER水平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但由于早期腎臟損害出現的微量蛋白尿易被漏診[13],誤差也較大[14-15]。患者出現大量尿蛋白時,T2DM的病情較為嚴重,通常無法逆轉。因此,選擇敏感有效的腎損害早期診斷指標,對逆轉或阻止T2DM繼發性腎損害具有重要意義。
D-D為機體凝血纖溶的標志物,其血漿水平升高反映機體的高凝狀態及凝血、纖溶系統的激活[16],糖尿病患者的血管內皮細胞損傷、微血栓的形成可激活纖溶系統,引起繼發性纖溶亢進、D-D的血漿水平升高,均為糖尿病腎損傷的病理基礎之一[17],故D-D一定程度上可反映腎小球的病理改變[18]。FIB作為一種急性時相反應蛋白,由肝臟合成,是反映凝血亢進和纖溶活力下降的指標,是血栓形成的前體物質,在T2DM患者中血漿FIB水平增加[19],可增加血漿黏度[20],血液處于高凝狀態,促進腎小球內微血栓的形成,加之損傷的內皮細胞能夠激活內、外源凝血途徑,導致凝血功能顯著增強[21],從而加速腎小球病變,最終進展為DN。高水平的FIB水平反映了體內不同水平的高凝狀態,且隨病程進展有增高趨勢[22],故FIB亦是糖尿病并發血管病變發生的重要指標之一。本研究對EDN、CDN組患者的D-D、FIB水平進行分析,結果EDN組D-D、FIB明顯高于對照組,CDN組DD、FIB明顯高于EDN組和對照組,說明DN患者尚未出現腎損害時即出現血漿D-D、FIB水平增高,隨病情加重升高更明顯,說明D-D、FIB的升高可能與DN的發生、發展密切相關。
本研究結果顯示,MDRD校正的GFR與D-D、FIB呈負相關,與UAER呈正相關,FIB、D-D與GFR呈負相關(r=-0.512、-0.798,P<0.05),UAER與GFR呈正相關(r=0.397,P<0.05),相關系數D-D高于FIB、UAER,FIB高于UAER。提示D-D及FIB在腎功能監測方面有較高的靈敏度,對糖尿病患者腎損傷早期診斷有重要的臨床應用價值。
因此,監測糖尿病患者的D-D、FIB水平,可早期發現血栓前高凝狀態,及時進行早期干預,即可通過適當抗凝、活血化淤等有效措施,改善患者血液的高凝狀態,防止或延緩DN的發生、發展,延長患者生存時間,改善患者的生活質量。
參考文獻
[1]Yamada T,Sato A,Nishimori T,et al.Importance of hypercoagulability over hyperglycemia for vascular complication in type 2 diabetes[J].Diabetes Res Clin Pract,2000,49(1):23-31.
[2]魏蓉,吳國亭.糖尿病的凝血與纖溶機制研究[J].同濟大學學報(醫學版),2003,24(4):295-297.
[3]王振義,李家增,阮長耿.血栓與止血基礎理論與臨床[M].2版.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525-526.
[4]Van Der Bom JG,Bots ML,Haverkate F,et al.Activation products of the haemostatic system in coronary,cerebrovascular and peripheral arterial disease[J].Thromb Haemost,2001,85(2):234-239.
[5] Zurbom KH,Duscha H,Gram J,et al.Investigations of coagulation system and fibrinolysis in patients with disseminated adenocarcinomas and non-Hodgkin′s lymphomas[J].Oncology,1990,47(5):376-380.
[6]霍梅,徐勇,葉素丹,等.血漿D-二聚體定量測定的臨床應用[J].血栓與止血學,2001,7(1):39.
[7]王敏敏,盧忠,謝琦.血漿D-二聚體測定臨床意義[J].臨床肺科雜志,2008,13(11):1515-1516.
[8]錢榮立.糖尿病臨床指南[M].北京:北京大學醫學出版社,2001:7-12.
[9]楊振華.臨床實驗室質量管理[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3:4951.
[10]黃友敏,周永勤,宋靜,等.全身炎癥反應綜合征患者血清抵抗素變化及意義[J].中華全科醫師雜志,2007,6(11):668-670.
[11]Verzola D,Gandolfo MT,Ferrario F,et al.Apoptosis in the kidneys of patients with type II diabetic nephropathy[J].Kidney Int,2007,72(10):1262-1272.
[12]鄭兵.血清胱抑素C與β_2-微球蛋白對糖尿病早期腎損傷的價值分析[J].中國誤診學雜志,2010,10(10):2301-2302.
[13]劉明旭,孫才,包穎.糖尿病腎病患者血清胱抑素C和尿微量白蛋白的測定[J].中國誤診學雜志,2010,10(6):1287-1288.
[14]張長庚,姚新潔,王文治.D-二聚體與CD146檢測在糖尿病早期腎損傷診斷中的意義[J].現代檢驗醫學雜志,2010,25(1):134-135.
[15]顧琳萍,崔為發.2型糖尿病微血管并發癥患者PAI-1、D-二聚體和vWF檢測的臨床意義[J].醫學綜述,2008,14(3):436-438.
[16]彭易清.D-二聚體檢測在2型糖尿病并發癥診斷中的應用[J].國際檢驗醫學雜志,2009,30(5):464-466.
[17]周博鋒.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血漿D-二聚體的檢測及臨床意義[J].廣西醫學,2009,31(6):847-848.
[18]李繼廣,任更普,張德.2型糖尿病患者血漿D-二聚體檢測及臨床意義[J].現代中西醫結合雜志,2005,14(23):3132-3132.
[19]劉麗,劉敏涓.2型糖尿病血管病變患者C反應蛋白、纖維蛋白原、D二聚體檢測的意義[J].血栓與止血學,2007,13(2):60-61.
[20]秦任甲.血液流變學研究進展與問題[J].中國醫學物理學雜志,2003,20(2):65-69.
[21]劉陽,薛秀梅,高月.糖尿病患者纖維蛋白原及D-二聚體測定的臨床意義[J].中國誤診學雜志,2006,6(12):2282-2282.
[22]孟秀娟.高敏C-反應蛋白和纖維蛋白原與糖尿病腎病相關分析[J].天津醫科大學學報,2010,16(2):342-344.
作者簡介:徐曉宏(1983-),主治醫師,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糖尿病腎病、腎小球疾病及腎間質纖維化等研究。
doi:·經驗交流·10.3969/j.issn.1671-8348.2016.18.035
[中圖分類號]R587.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1-8348(2016)18-2554-03
(收稿日期:2015-12-21修回日期:2016-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