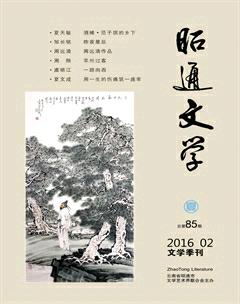路邊的小板房
一
春天的太陽就是特別勤,似乎剛打個盹,又早早地從山凹里探出頭來,俏皮地穿過那薄薄的窗簾,輕佻地撫摸著秋香那圓潤而富有彈性的臉蛋。秋香強睜開雙眼,陽光更放肆了,直騷弄著她那雙迷人的眼珠。秋香困倦地揉揉雙眼,打了個哈欠,還是困。剛才還鼾聲如雷的順子也被弄醒了,瞇著雙眼,適應了一會兒,側過身,一眼瞥見秋香那紅潤的臉蛋,猶如園子里剛綻放的桃花,帶著露水,在明媚的陽光下,是那么嫵媚,那么誘人。他不再犯困,睜大雙眼,貪婪地盯著:一頭烏云般的長發(fā)堆在枕上,閃著青春的光澤,困倦慵懶的杏眼懶懶地微瞇著。順子的下面騰地直立起來,熱血直往上涌,睡意全無,翻身壓了上去,在那緋紅的臉上狂吻起來。秋香的臉蛋更加紅艷,更加嫵媚了。她嬌羞地把男人推了下來,嗔怪著:“喂不飽的狗,我要煮早點了。”順子只好悻悻地砸吧著嘴皮,癡癡地望著秋香。秋香意味深長地瞅了一眼這個懊惱的男人,坐了起來,兩手攏了攏那齊腰的黑發(fā),輕輕地穿衣下床,悄無聲息地走進廚房。路過孩子的臥室,聽到孩子甜蜜的囈語,秋香幸福地笑了,輕輕地,唯恐弄出一點聲音,驚著這對可愛的小天使。
孩子們最愛吃的酸辣面擺上桌子了,手機鬧鈴歡快地叫了起來。霎時,呵欠聲、起床聲、洗漱聲匯成了歡快的早晨進行曲。
順子和兩個孩子胃口永遠是那么好,“滋溜滋溜滋溜”響過,碗底見空,兩個孩子似乎還沒吃飽,連湯都喝完了,還伸出舌頭舔了舔碗邊,才戀戀不舍地放下碗筷,背起書包,推開門。
“媽媽,再見!”
“媽媽,再見!”
“賽康,小心點,照顧好妹妹——格格,走慢點。”秋香的聲音從門縫里追了出來,淹沒在“叮叮咚咚”的腳步聲中。
“走啦——”隨著順子的關門聲,屋子頓時靜了下來。一切鮮活的東西都被這爺兒仨帶走了,留下秋香一人空落落地待在空蕩蕩的屋子里。
秋香把碗筷收在水盆里,雖然才四個碗,四雙筷子,秋香還是仔仔細細地把它們洗了又洗,抹了又抹,反正也沒事情可做。
秋香回到臥室,太陽光已經(jīng)照到臥室里的每一個角落了。秋香想睡個回籠覺,那耀眼的陽光照得她睡意全無。秋香只好把床單拉得平平展展,被子疊得方方正正,在床上呆坐了一會兒,感覺有些熱了,就走到客廳里,坐在沙發(fā)上呆呆地看著地板。秋香一眼瞥見飯桌下有幾根面條,自顧自地笑了笑:“這兩個臭娃娃,吃東西老是撒潑。”起身去拿掃帚掃了掃,卻把那里弄花了,閑著也是無聊,秋香干脆拿拖把來把地板再拖拖——雖然昨天才收拾得干干凈凈。
太陽已經(jīng)鉆進客廳里了,秋香有些困倦,像生了病一樣,渾身軟軟的,沁著汗。拿起手機看看,才9點鐘,還早呢,干脆洗個澡,洗個澡或許會有點精神。
秋香推開衛(wèi)生間的門,擰開水龍頭,把水調涼些,一頭鉆進去。水龍頭里的水有力地沖刷著秋香浸透著汗水軟綿綿的身體,秋香似乎有些精神了,漫無目的地揉搓著身體,思緒隨著水花飛濺著。這城里就是好,困了、熱了,可以沖個澡。想想在老家,忙活了一天,灰頭土臉的,能夠洗上一把熱水臉就是莫大的享受了。晚上鉆進散發(fā)著泥土味、汗臭味的被窩里,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死豬一般睡到雞叫二遍,懶懶地拿起滲著汗臭味的衣服,涼涼的,打個寒顫披在身上,極不情愿地爬起來,生火、煮好豬食,啃著冷洋芋,擔著籮筐進地了。要說洗澡,連想都不敢想,在秋香的記憶里,只有過一次,唯一的一次。那是在娘家做姑娘時,那天晚上,熱得實在受不了了,秋香和另外兩個好姐妹趁著夜深人靜,偷偷溜到村頭小溪里,在朦朧的月色里,脫了衣服,剛跨進清涼的溪水里,忽然響起了幾聲尖利而邪惡的口哨聲。三個姑娘嚇得把衣服抱在胸前落荒而逃,從那以后,她再也不敢去洗澡了。
沖夠了,也精神了。秋香拿塊干毛巾擦擦身體,下意識地走到衛(wèi)生間的鏡子前。秋香驚呆了:鏡子里的人兒更迷人了。烏黑的頭發(fā)順順溜溜地傾瀉在后背上,高挑的個兒,肌膚那么白,那么圓潤,生了兩個孩子了,奶子依然那么挺立,肚皮是那么光滑。秋香癡癡地盯著鏡中美麗的胴體,似乎不敢相信那是自己,那是電視里出浴的明星。秋香不由自主地轉動身體,欣賞著鏡中該鼓就鼓,該細就細的地方,陶醉了,她真想自己就是一個強悍的男人,撲進鏡中,把她抱住,周身上下啃個夠,啃得她嗷嗷直叫,啃得她幸福地呻吟。秋香呆呆地想著。
秋香走出衛(wèi)生間,來到客廳。這間房子真好,太陽正照在沙發(fā)上。秋香披條大浴巾,坐在有些發(fā)燙的沙發(fā)里,曬著太陽。懶懶地抓過手機,才9點半。時間怎么過得這樣慢?太陽也好像賴在家里不走了。在老家的時候,總嫌太陽溜得飛快,還沒疏完一棵蘋果樹的花,太陽就正頂了。秋香嘆了口氣,看著手機上不緊不慢的時間,想去逛一下街,可是,這城市也太小了,三年了,哪個角落都走膩了。想看看電視,順子說不能買電視,影響娃娃學習。秋香就呆呆地坐著,開始煩躁起來,她想起了家里的蘋果樹,要是以前,早就擔著一挑糞水進園子了,剪剪得了白粉病的枝條,拔拔樹根下的草草,那時間就像快車拉著,眨眼間就黑了。
秋香想想廣場上的那些年輕的,年老的,在震得地動山搖的音樂聲中,瘋狂地扭著肥碩的大屁股,那日子也許會好打發(fā)一點。秋香只能遠遠地看著,自己不會扭,也不好意思去扭。剛進城的時候,秋香還覺得那些人好無聊,大白天的浪費時間,浪費精力。現(xiàn)在想想,也怪羨慕她們,還是人家會過日子呀。
這時間怎么這樣慢呀?看看手機,那數(shù)字就像害了大病似的,半天才變動一個數(shù)字。秋香看了一眼,做飯還早,又情不自禁地拿起拖把拖一下地板,不知道拖哪里。地板已經(jīng)照得出人影來了。秋香走到廚房里,拿起抹布,又不知道抹哪兒,到處賊亮。秋香無可奈何地笑了笑,再看看手機,那些數(shù)字還是若無其事地磨蹭著。她又走進臥室,看看哪兒還要收拾一下。被子疊得整整齊齊的,床單平平展展的,打開衣柜,比服裝店里的還掛得整齊。
秋香無聊地回到客廳,坐不是站不是,在客廳里來來回回地走動著,沙發(fā)上的墊子理了又理,拉了又拉,又拿起手機看看,還是不到煮飯的點。想去串一下門,可是,三年了,連鄰居長什么樣都沒見著,大家回來就把門關得死死的。秋香開始莫名其妙地煩躁起來,無可奈何地踱到墻邊,墻上貼滿了賽康和格格的獎狀,秋香已經(jīng)看膩了。想想剛進城那會,成天像打仗似的。全職太太的秋香,早上天不見亮就起床給娃娃做早點,然后送娃娃去上學,再回家,等到11點鐘又去接娃娃,接回來煮好飯,娃娃吃了又送去,下午4點半又去接娃娃,接回來,兩個娃娃就開始做作業(yè),秋香煮飯,娃娃做完了,秋香的飯也做好了,招呼娃娃吃好飯,睡覺去了,秋香就繡著十字繡等順子,順子要很晚才回來,秋香就一直等著,順子回來了,秋香趕緊把菜熱熱,兩口子親親熱熱地吃著飯。吃完飯,嘮嗑一會兒,已經(jīng)11點過了,順子洗洗澡,和秋香鉆進了被窩。
一到星期六、星期天,秋香就帶著賽康和格格到望海公園去玩。兩個孩子在沙灘上玩得可歡了,一會兒挖地道,一會兒壘城堡。秋香生日那天,懂事的兩個娃娃還在沙灘上壘了一個大大的蛋糕,上面插滿了柳條,格格把秋香拉過去,說要給媽媽過生日,還要唱生日歌,還要秋香閉上眼睛對著蛋糕許愿,秋香幸福極了,她面對眼前的蛋糕,心里浮現(xiàn)出電視上過生日的情景,面前似乎擺著一個精致的大蛋糕,蛋糕上的蠟燭熠熠生輝。秋香還真的許了何愿,她默默地祝愿兩個寶貝快快樂樂成長,讀好書,考上名牌大學,找一個體面的工作。許完愿,格格要秋香吹蠟燭,秋香裝模作樣地對著柳枝吹去,調皮的賽康和格格一下子把柳枝拔完。格格還認真地問秋香:“媽媽,你許的是什么愿?”秋香也調皮了:“就不告訴你!”賽康和格格就把秋香掀翻在沙灘上,給她撓癢癢,一定要秋香說出來。秋香一邊笑,一邊在沙灘上滾來滾去的,娘三個就在潔白的沙灘上滾了一個下午。
有時候,秋香坐在石凳上,一會兒深情地望著一雙可愛的娃娃,沒想到,農村娃娃也能在城里讀書,星期天也能在公園里玩耍,這是她小時候做夢都做不到的呀;一會兒望著漣漪輕蕩的湖面,想不到自己一個出生在大山深處的姑娘,還能夠嫁到壩子里,還能夠嫁個知熱知冷的男人,還能夠住進城里過上城里人的生活,真是芝麻開花節(jié)節(jié)高呀。秋香憧憬著,娃娃考上大學,在城里工作,買上房子,她和順子也不回去了,就在城里享清福,給娃娃煮煮飯,吃完飯就像廣場上那幫老奶跳跳舞。秋香想到這里,不由得笑了,夕陽照在湖面上,映著秋香的面龐,是那么嫵媚。
玩夠了,該做飯了,秋香拉起賽康和格格,輕柔地給他們撣掉衣服上的白沙。
那時候,秋香充滿了幸福。城里的學校就是好,兩個娃娃每次考試都是雙百分,秋香不得不佩服男人有遠見。
秋香還記得一次家長會上,朱老師一個勁地夸娃娃,說娃娃聽話,學習習慣又好。朱老師把幾個城里成績糟糕的學生家長狠狠地批評了一通,說他們把娃娃丟到學校就不管了,一天只知道打麻將,娃娃的作業(yè)也不過問,這樣下去,會害了娃娃的。像人家賽康和格格的媽媽雖然從農村來的,文化也不高,可是人家多重視娃娃的學習,兩個娃娃次次考試都是雙百分。那幾個被批評的家長恨不得找個地縫鉆進去。秋香臉紅了,不好意思看老師,然而心里卻像喝了幾罐蜂蜜。朱老師硬是要秋香介紹一下經(jīng)驗,秋香推辭不過,只好站上講臺,低著頭,訥訥地說:“我沒文化,只讀過二年級,我和我男人吃夠了沒文化的苦頭,才丟掉家里的土地,把娃娃送到城里來讀書。我沒啥經(jīng)驗,種蘋果樹我倒是有經(jīng)驗,該剪枝了就得剪枝,不然就不會結蘋果,該疏花就得疏花,不然蘋果就不大,該灌水就得灌水,該施肥就得施肥,該打藥就得打藥,我一天都在園子里伺候著蘋果,所以我家的蘋果又大又好,能賣個好價錢。我知道,你要好蘋果,你就得當娃娃一樣伺候它,糊弄不得。”
秋香一驚,怎么說到蘋果上去了,講偏了,她不好意思地瞅了朱老師一眼,只見朱老師興奮得滿臉通紅,正用敬佩而贊許的目光看著她。秋香拉了拉衣角,接著說:“管娃娃,我也沒怎么管,就是早上做早點給他們吃,吃完了就送他們上學,放學了再接回去,我做飯,他們寫作業(yè),星期天,我就帶他們去望海公園玩,真沒怎么管,他們的作業(yè)我又認不得,沒法輔導,都是老師教得好。”秋香稀里糊涂的不知道自己說了些什么,羞澀地看著朱老師,臉漲得通紅。
朱老師快步走上講臺,激動地握著秋香的手,動情地對下面的家長說:“多好的母親呀,多負責的母親呀,說的真好,管孩子就像管蘋果樹,你不上心,它就不結果。多么樸實而深刻地教育理論呀,賽康媽媽,您才是真正的教育專家呀。家長們,看到了吧,人家的優(yōu)秀孩子是怎么培養(yǎng)出來的,人家就是用了心,盡了職,成天陪著孩子。這些事有多難,一點都不難,只要你心里裝著孩子,每天多陪陪孩子,孩子就感到快樂,就會有學習興趣,就會養(yǎng)成良好的學習習慣。可是,我們有些家長,寧愿在麻將桌上沒日沒夜地耗,寧愿在酒桌上推杯把盞,就是不愿意抽出時間來陪孩子。你們以為給孩子吃好穿好就是愛孩子嗎,就是盡到了父母的責任嗎?錯了,不陪孩子的父母就是不合格的父母。很多家長,一說陪陪孩子,就是找借口,什么工作忙呀,沒時間呀。我請問,你什么工作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在上班,都不回家吃飯,都不回家睡覺。完全是不負責任的借口,你們的時間都去哪兒了?都在魚竿上,都在麻將桌上,都在酒桌子上。家長們哪,孩子還在小,習慣的培養(yǎng)很重要呀,你現(xiàn)在說沒時間管,將來你想管也管不了。今天,賽康的媽媽一番話值得你們深思呀。”
不少家長把頭深深地埋在課桌的抽屜下。
晚上,秋香眉飛色舞地跟順子講家長會上的故事:“這城里人有什么了不起的,一個二個被老師罵了頭都抬不起來,我一個農村婆娘,還被老師說成是教育專家。”
順子摟過秋香,狠狠地親了一口:“婆娘,你辛苦了。”
賽康和格格兄妹倆的成績一直非常優(yōu)秀,幾乎包攬了每次考試年級上的一、二名,獎狀貼滿了客廳上的墻壁,比什么十字繡還漂亮,順子和秋香沒事就相擁著一張張地看那獎狀,從一年級的第一張看到最后一張,總是看不夠,就像看秋天果園里掛滿枝頭的紅通通的大蘋果。
這個學期,賽康和格格上了三年級就不要秋香接送了,秋香悶在家里,一天七不是八不是,心里空落落的,就像一只關在籠子里的小鳥。而自己感覺到連那籠子的小鳥都不如,小鳥雖然被束縛了自由,心里還在向往那自由自在的藍天。然而自己的藍天又在哪兒,待在家里,就簸箕那么大塊地方,收拾收拾,收拾了幾百次,仍然是那個老樣子,出去走走,一個人都不認識,就像一個孤魂野鬼,走得腳生疼,走得心里發(fā)毛。秋香漸漸感覺到,她和這個城市之間隔著一張看不見的大網(wǎng),她走不進去,這個城市不是她的藍天。秋香嘆了口氣,拿著手機,癡癡地望著,思緒回到了那些屬于她的歲月。
二
秋香出生在一個山區(qū)里,都說深山出美人,此話一點兒都不假。村子里的姑娘一個個水靈靈的,嫩生生的,秋香更是出落得楚楚動人。可惜,老天暴殄天物,秋香只得跟在爹媽后面背著個高高的竹籮風里來,雨里去,找豬草,背糞草,背洋芋,背蕎麥……秋香背洋芋回家后,放下背籮,看到隔壁大嫂蹲在屋檐下,靠著那個高高的竹籮把雪白的奶子從衣襟里掏出來,看都不看一眼左邊坐著抽水煙袋的大伯子,右邊坐著卷葉子煙的老公公,旁若無人地奶娃娃。兩個大一點的娃娃趿拉著老長的鼻涕,在面前滾來滾去。秋香瞥了一眼奶娃娃的大嫂,祖祖輩輩都是這樣,三五年后,自己也是這樣。
不過,秋香命特別好,山外邊一個叫順子的小伙子背著滿滿一夾背籮大蘋果在媒婆的帶領下來到她家,秋香成了壩子人。
結婚后,第一個兒子出生了。分家了,秋香和順子帶著不到一歲的兒子住進了攆出了老母豬的豬圈里。蘋果樹分給了順子的爹,大瓦房也歸順子爹住,順子爹說,這樣順子的弟弟才討得著媳婦。秋香理解老人的苦衷,什么也沒說,默默地把老母豬攆出去,把里面的糞草挑完,順子挑來了生石灰,兩口子把墻刷白了,安了個地爐子,把娘家陪嫁的大木柜、大木箱、鋪蓋行頭搬了進去。一個家就成了。
順子說,地太少了,三張嘴吃一個人的地,養(yǎng)不活,他出去打點工,苦幾年,蓋間像樣的房子。拖著半歲多的兒子,挺著個大肚子的秋香用蛇皮口袋改成一個背包,里面塞進一床鋪蓋和一身換洗的衣服,送走了順子。
順子爹自知對不起這個兒媳婦,老兩口盡力幫襯秋香,幫秋香帶著娃娃,秋香做活回來,順子媽總要抱著娃娃過來叫她過去吃上一口熱乎乎的飯。秋香吃了飯,搶著要洗碗,順子爹就說:“帶娃娃吧,一天沒有見著娘了,你媽洗了。”一家子逗著娃娃,娃娃咯咯咯笑著,一會兒爬到順子爹身上揪揪那山羊胡子,一會兒爬到順子媽身上,掀起奶奶的衣襟,要摸摸奶奶的老癟奶,一家人笑得上氣不接下氣,都說這娃就是一大活寶,大開心果。鬧騰累了,秋香就帶著娃娃回到豬圈里,娘兒睡了。有時,秋香睡不著,青春在體內騷動,秋香一想到漂亮的大房子,忍住了,摟著娃娃,迷迷糊糊地睡著了。
每到點種收成,身子骨還挺硬朗的順子爹就帶著小兒子幫秋香挑拿。秋香兩點一線,家里——地里——家里,路上遇到一些不懷好意的浪蕩年輕人,他們就挑逗秋香:“嫂子,夜里悶吧?”秋香紅了臉,唾了一口:“要死啦!”急急忙忙往家趕去。那些浪蕩小子偏不信這個邪,晚上就會借口到秋香家去。順子爹就提著把大鐮刀,黑喪著個臉,在外面哼哧哼哧地砍著蘋果樹樁樁,嘴里大罵:“看老子不砍死你。”那些小子見勢不妙,馬上屁滾尿流走了。村子里那些男人出去打工的婆娘,很多都有了風言風語。只有秋香純凈得像吊井里的清水,聽不到半句爛言。村子里的老頭老媽豎起大拇指,嘖嘖贊嘆,都說順子好福氣,討了個那么正經(jīng)的女人。順子爹媽走在村子里更是昂首挺胸。
順子來電話了,說他進了廠子,老板很好,一個月兩千多塊,除去生活費還剩一千七八,工資是半年發(fā)一回,已經(jīng)寄回來了。叫秋香上街去買身衣裳,割點肉,不要太苦了自己。秋香幸福得滿臉通紅,她囑咐順子,要吃飽,不要太累了,多吃點肉,不要把身體拖垮了。
秋香到郵電所里取了錢,辦了個存折,把錢存成死期,拿著幾百塊零錢,給順子媽買了一件厚實的棉衣,買了一套兒子的,給順子爹買了兩條煙,割了兩斤新鮮肉,回到家里,弄了一桌豐盛的菜,把順子爹、順子媽以及順子弟弟叫了去,一家人歡歡地吃了個夠。順子爹摟著孫子,興奮地說:“我孫子,你看你爸爸媽媽多好,長大了對你爸爸媽媽也要好喲。”
秋香成了村子里賢妻良母的典范,那些兒媳不孝順的老婆婆見了順子媽就酸溜溜地數(shù)落:“你家是哪輩子積的陰功,攤上這么好的兒媳婦,我家那個要趕上你家秋香腳丫巴,我睡著都要笑醒掉。”順子媽不做聲,只是呵呵笑著。
順子回來了,把秋香存的錢取了出來,蓋起了一樓一頂?shù)拇蟠u房。秋香搬了進去,恨得村子里的人牙齒癢癢的,咋個順子家就能蓋上大磚房?
順子說:“媳婦,苦了你了,那地就不要種糧食了,栽上蘋果樹,小蘋果樹不費事,你隨便管管,好好帶著娃娃。我再去打工,等蘋果樹長大了,我就回來種蘋果樹了。”秋香連連點頭:“好。”過了年,順子買來了樹苗,跟秋香一起栽好,又坐上了遠去的火車。
三
秋香地里的小蘋果樹漸漸長大了,碗口般粗。秋香勤快,成天在蘋果地里忙碌著,哪里有棵草,秋香都要仔細地除去。地總是鋤得松松的,就連每次進地踩上的腳印,她都要細細地挖松。每天進地,秋香都要隨身擔上一擔糞水,和上清水均勻地灑在樹下松軟的泥土里。順子爹是種蘋果的高手,他把自己的秘訣悉數(shù)傳給了秋香。修枝剪葉,壓條扭梢,疏花疏果,什么季節(jié)干什么活,秋香一絲不茍地做著,她那片蘋果樹老遠就認得出,樹干青皮水漉,葉子厚實墨綠,蘋果又大又紅,果型端正。她的果子從不起早貪黑地挑到市場上去賣,村里,鄉(xiāng)里的早就給她包了,價格高出市場上很多。同年栽的樹,同樣的面積,別人只賣三五千塊,秋香年年都要賣上一兩萬。看著這個聰明能干勤勞的媳婦,順子爹媽老是躺在床上睡不著覺的時候反反復復地贊嘆,咱們家修了陰功,順子積了德,才娶上這萬里挑一的好媳婦。
隨著蘋果樹瘋長,秋香的一雙兒女也像那蘋果樹的秋枝一樣騰騰往上冒。大的是兒子叫賽康,小的是女兒,叫格格,相差一歲,那時候,《還珠格格》正在熱播,順子爹給兒子取名叫賽康,想要超過爾康,女兒當然就叫格格了。賽康已經(jīng)7歲了,格格6歲,該是讀書的年紀了。秋香到村完小給賽康和格格報了名。順子回來了。
秋香問順子:“還沒過年咋就回來了?”
順子說:“娃娃讀書了,這可是咱家的大事情,不打工了,回來盤娃娃讀書。”
秋香急了:“你發(fā)什么神經(jīng)?不就是讀個書嘛,學校又近,而且還供早飯,現(xiàn)在的政策太好了。娃娃去學校,中午不回來,我不用操心做早飯給娃娃吃,正好在地里多做一會兒活路,你回來整啥子?”秋香心疼呀,順子現(xiàn)在可是廠里的小領班,一個月多領一千多塊,這回來一趟,最少也要耽擱兩個月,多可惜。她撒嬌說:“順子,你就放心去打工吧,我保證管好你的寶貝兒子,寶貝姑娘。”
順子很堅決:“不去打工了,娃娃放在農村讀書沒有出路。”
秋香不同意了:“不放在農村讀,難不成還送到城里讀?”
順子點了點頭:“對,就是要把娃娃送進城里去讀。”
秋香摸了摸順子的額頭:“順子,你沒發(fā)燒吧,送娃娃去城里讀,你進得去?聽說,要有關系的才進得去。再說了,住在哪里,哪個照管娃娃?”
順子告訴秋香:“娃娃讀書是大事情,是他們一輩子的大事情,城里的學校教學質量高,娃娃去了,學習好,能夠考上好一點的高中,然后考上重點大學,娃娃的前途就有了。不像在農村,老師們都住在城里,一大早上才上課,還沒到放學時間,就開著車回去了,不會輔導學生,就算在學校里,一天也是忙活學生的飯,沒有心思教書。農村學校的教學質量太糟糕了。”
秋香用那水汪汪的大眼睛望著順子:“你說的都有道理,可是這娃娃咋個整呢?”
順子似乎很有信心:“現(xiàn)在只要有錢,可以托人把娃娃整進城里,我們一家都搬進城去,你照管娃娃,我在城里打點工,能夠養(yǎng)活一家人呢。”
秋香不答應了:“順子,那我們家的損失可就大了,你在城里打工,工錢肯定少了很多,我跟著去了,這么好的蘋果樹,正大投產,一年兩三萬,可惜了。這樣吧,不如租點房子,讓他爺爺去照管,你繼續(xù)去打工,我種我的蘋果樹,盤娃娃掙錢兩不誤。”
順子這兩年在外面打工,錢也掙了不少,見識也長了很多。他柔聲地對秋香說:“他爺爺去照管娃娃,隔代人管不好,我好幾個朋友的娃娃就是丟給爺爺奶奶管,全管廢掉。盤娃娃要緊,娃娃廢掉,再苦好多錢都沒用,就這樣決定了。現(xiàn)在城里打工也容易,養(yǎng)活一家人沒問題,等娃娃讀大學,我們那點存款也夠盤了。”
秋香終就拗不過順子,含著眼淚把蘋果樹交給了順子爹,帶著娃娃跟著順子進了城。
順子花了錢,找了人,費了很多周折,娃娃終于進了城里最出名的縣二小。順子在老鄉(xiāng)的幫助下,找了一家托運部,早出晚歸,雖說辛苦點,一個月也能掙個三四千塊,生活不成問題。
四
晚上,秋香依偎在順子的懷里:“順子,娃娃大了不需要接送了,我閑得慌,找點事情做做。”
順子把頭搖得像撥浪鼓:“不行,不行!管娃娃要緊,你不要東想西想的。”
“可是,我閑得慌嘛。”
“你呀,真是個賤命,有福不會享,你不會出去游游街?”
“有什么游的?腳走得生疼。”
“那你就在家里乖乖呆著,好好照管一下娃娃。娃娃才是大事。”
秋香懶懶的,像生病了一樣,打不起精神來,這沒事可做的日子真是難熬呀。
鬧鐘響了,秋香實在不想起來,起來也難受,就喊著:“賽康、格格,媽媽不起來了,茶幾上有錢,你們自己去買點吃,媽媽起來也無聊,就多睡會兒吧。”
“媽媽,老師說了,外面小攤上的是垃圾食品,不準我們買了吃。”
“哎,真是的。”秋香只得爬起來煮早點,賽康和格格走了,秋香又陷入了七不是八不是的無聊之中。
“這樣悶下去,遲早要悶出病來。”秋香自言自語地說,“反正閑著也是閑著,還是出去走走。”秋香走著走著,不知不覺走到學校門口,校門口坐著很多人,這兒一堆,那兒一堆,全都是老頭老奶,有的在吹牛,有幾個在打撲克,還有兩個老頭在下象棋。他們都是送孫子的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反正回家也難跑,不如就在這里找點事兒做著——或者聊天,或者打牌。等放學了,接著孫子回家。老人嘛,在哪兒不是玩?
秋香不好意思混在這群老頭老奶堆里,年紀輕輕的,混在里面算一回什么事?人家是老了,而自己的,人家會怎么看,還不是游手好閑的?以前在村子里,游手好閑的年輕婆娘是要被人指著脊梁骨罵的。秋香可不想被人指著脊梁骨罵。她遠遠地看著那一堆堆老頭老奶。
“秋香,你咋來了呢?”
秋香大吃一驚,三年了,還沒有人在學校門口叫過自己。她轉過身一看,一個肥肥胖胖的女人,紅紅的卷發(fā),修了眉,涂了口紅。是誰呢?
“怎么,先來城里幾年,就裝洋了。不認識了。”紅卷發(fā)露出了鄙夷的神色。
秋香仔細地打量半天,終于認出來了,這不是村子里歪脖子核桃樹下李木匠的婆娘桂花嗎,簡直就不是一個人了。在秋香的記憶中,這個桂花仗著男人會做木工,掙得來點錢,成天不干活,東家竄西家逛的,村子里的口水都要把她淹死了。黑不溜秋的,那頭發(fā)就像秋霜打過的枯草,干巴巴地吊在頭上。
“哦,桂花嫂呀,你在這里整啥子?”畢竟見到了同村人,秋香來了精神,客氣起來。
“接娃娃。”
“你家的娃娃也整進城來讀啦?”
“是了嘛,看著家家的娃娃都整進城來讀,今年他爹也把他整進來了。”
桂花告訴秋香,她男人在工地上攬活做,今年把娃娃整進城來讀書,她就做了全職太太,專門帶娃娃。
“那就好,那就好。”這樣重視娃娃,秋香對桂花一下產生了好感。
“桂花嫂子,接娃娃還早呢,你咋就來了?”
“我嘛,送娃娃來了,我就去那里玩,等娃娃放學了,我就接了回去做飯。”
秋香真佩服桂花,人生地不熟的,竟然找得到玩的。
“走,秋香,跟我一起去,站在這里難等得很。”桂花熱情地挽著秋香的手臂。
反正閑著也無聊,而且遇到了老鄉(xiāng),秋香跟著桂花走去。
桂花帶著秋香穿過寬闊的二環(huán)南路,來到路邊的一間小板房前。剛到門口,一股刺鼻的煙味夾雜著腳臭味、狐臭味撲鼻而來,秋香不由得捂住鼻子。順子可不抽煙,她未曾聞過煙味兒,怎么這么濃,這么難聞,秋香本能地往后退了退,差點吐了出來。
“美女,來啦,等你好久了,硬是抓心抓肝的。”一個輕浮的聲音傳來。
秋香循著聲音望去,只見昏暗的小板房里擺著幾張麻將桌,里面的兩張已經(jīng)坐滿了人。幾個敞著上衣,露著胸毛的男人,穿著長短褲,趿拉著拖鞋,把一只腳橫放在塑料凳上,一副肆無忌憚而粗俗的樣子。幾個打扮得非常時髦的女人混在這些男人中間,是那么別扭。他們正稀哩嘩啦地搓著麻將。男人們嘴里叼著煙,有兩個女人也叼著煙,特別刺眼。一個女人打出了一張牌,浪蕩地叫著“老娘用過的二條,狗日的拿去擦嘴吧,省得逼嘴亂淌。”那男的淫笑著:“二條老子不要,爛婆娘,拿二筒來我摸。”很多人就放肆地笑了起來。
地上全是煙頭、紙巾、口痰。
秋香頭皮發(fā)麻,后背磣涼。這些時髦的女人竟然待得下去!
桂花已經(jīng)坐下去了,嫻熟地搓著麻將。一個禿頂?shù)哪腥松[瞇地盯著她,壞笑著:“爛婆娘,昨天老子要二筒,硬是緊緊夾著,不拿給我,害老子輸了個精光。”
桂花也不示弱:“活該你狗日倒霉,一張逼嘴什么都在淌,昨天還不算,今天老娘要叫你內褲都輸光。”
天哪,這是什么地方。秋香一分鐘都待不下去了,試探著問桂花:“嫂子,你玩吧,我走了。”
“你忙去賣呀,坐在這里,看著我打牌,這兩天我手氣好得很,等贏了錢,我們帶著娃娃進館子——哎,黑老幺,泡杯茶給美女。”
“是了,是了”。一個瘦的風都快要吹倒的黑不溜秋的男人馬上給秋香端過茶水來嘿嘿笑著:“美女,抽著玩吧。”
秋香聽得瘆人,后背起雞皮疙瘩,忙不迭地應道:“我不會玩。”
茶端來了,秋香也不好意思走了,只得找個塑料凳坐在門口,呆呆地望著桂花。
這個黑瘦的男人就是黑老幺。黑老幺原來是個游手好閑的人,規(guī)劃小區(qū),他把自己分得的地基賣了,拿著十幾萬,一下子覺得自己就是個富翁了,怎么用得了這么多錢?別人想方設法借錢蓋房子,他懶得蓋,天天賭錢,賭累了就喝酒,喝醉了就去找野雞,死水經(jīng)不住瓢舀,當小區(qū)里規(guī)劃好的房子如雨后春筍般冒出來時,他的十幾萬已經(jīng)全沒了。婆娘一氣之下,跑了。別人坐著收房租,他穿著馬籠頭一樣的衣裳在學校門口閑逛。新修建的學校越辦越紅火,接孩子送孩子的車多起來了,在門口溜達著等娃娃的人也多起來了。有些閑不住的人就蹲在路邊打牌。黑老幺畢竟是黑老幺,靈機一動,將政府給他的板房搭在路邊,取了個響亮的名字——老幺娛樂中心。
還真不錯,那些蹲在路邊的人有了個遮風擋雨的地方,也就慢慢走近小板房。一兩年后,老幺還真掙了幾個錢,購置了幾張麻將桌,把生意擴大了。
“哎呀,老子又拿一炮給你了,這爛婆娘!”
“狗日的,你放得起,你盡管放!老娘照單全收,把你狗日的贏去倒尿罐,老娘都不稱心。”
“咯咯咯”
“嘿嘿嘿”
“哈哈哈”
……
各種粗魯?shù)男β曄褚桓羲疁侠飺破饋淼哪景簦林锵愕男呐K,又疼又惡心。要知道,秋香是連半句葷話都不講的好女人。
秋香實在坐不住了,看看手機對桂花說:“時間不早了,接娃娃了。”
桂花一看手機:“哎喲11點半了,我要接娃娃了。你們玩吧。”
桂花滿臉放光,把幾張紅票子理好,塞進小手包里,出來招呼秋香。
“賊婆娘,贏錢就下剪刀,接娃娃,接個干雞巴,往天輸錢,娃娃抱著腳哭都不走,這賊婆娘。”幾個男人憤憤不平。
桂花根本不理這憤怒的聲音,挽起秋香的手臂向學校走去。
“桂花嫂,你咋個玩上了麻將,木匠哥準你玩?”
“我家木匠非常支持我玩,他說,在城里沒得事情做,又沒個熟人,會悶出病來的。玩玩麻將,時間好混。”
“秋香呀,以后就跟我一塊兒來這里。你不玩,就在那里看著,時間就好打發(fā)了。”這桂花心里可打著小算盤,有了秋香,以后她打起麻將來可就沒有什么顧忌的了,娃娃放學了,可以叫秋香去接嘛,大不了請她下幾次館子。
秋香連連搖頭:“不去了,不去了!”
秋香板著臉,嗔怪著:“真是土逼婆娘一個,你就坐在那里,又不玩,你那東西還會掉在那點。”
桂花接了娃娃,賽康和格格也剛好出來。桂花請他們下館子,秋香不想去。
桂花可不饒:“秋香呀,自從你進城來,我們三年沒見面了,今天在這兒遇上,你得給個面子,我們姐妹好好說說話嘛。”
秋香覺得再推辭,就是狗戴帽子不服人尊敬了,反正順子中午也不回來吃飯,就答應了桂花。
吃完飯,桂花說:“秋香,你順便把娃娃一起送去,我再去贏幾個狗日的,今天手氣太好了。”
秋香把三個娃娃送進學校,本想回家了,一眼瞥見路對面的小板房,想到回家去也難熬,不由自主地向小板房走去。
五
自從遇到桂花,秋香覺得時間好打發(fā)了。她經(jīng)常跟著桂花來到小板房里。桂花打麻將,她就在旁邊看著。時間到了,就去接娃娃。有時,桂花招呼秋香娘兒進館子。有時,桂花輸錢了,就賴著扳本。秋香就連桂花的娃娃接回自己家里。桂花很晚才來接娃娃。順子累了一天,想睡覺,可是桂花的娃娃還在這里,又不好意思睡。時間長了,桂花的娃娃干脆跟賽康睡在一起。順子看看有些不對勁,就叮囑秋香:“你少跟桂花來往,她這樣做,遲早會害了娃娃。”
秋香應道:“你就放心,我又不玩,我坐在那里看,耽誤不了管娃娃。”
秋香看著桂花實在不像樣了,也勸桂花,娃娃重要,少玩過頭了。桂花老是數(shù)落秋香,秋香呀,不要太護著孩子,要讓他們獨立,自理能力不強的娃娃,以后沒多大出息,你還能管他一輩子?秋香覺得這是歪理,是桂花在為自己打麻將找借口,可她又找不出更好的理由來說服秋香。
一天,秋香又來到小板房前,見桂花和兩個男人坐在麻將桌前,他們沒打麻將,秋香手里捻著一張麻將,無聊地轉動著。
“怎么不打了?”秋香好奇地問。
“三差一,這個狗日的黃麻子,今天這個時候還沒來,找他媽吃奶去了。”桂花沒好氣。
一個男人看到秋香來了,老鼠眼放著光,就像毒癮發(fā)作了的癮君子見到白粉一般,熱情地招呼:“美女,來,一起玩。”
“不不不。”秋香嚇得連連擺手,“我不會玩。”
桂花若有所悟:“是呀,秋香,你看了這么長時間了,也該會了,來來來,一起玩玩,等黃麻子來了,你再坐在那里看。”
“不行,我真不會。”其實,簡單的理牌,和牌,秋香看了這么長時間,也略知一二。她就是不沾那麻將的邊,生怕像桂花一樣。
“美女,一點面子都不給?”另一個男人顯然有些不太高興了。
“玩吧,就玩一會兒,你忍心讓我們三個干炕著。”桂花站起來拉秋香。
秋香再不好意思推辭了,勉強應道:“就玩一會兒,等你們的伴來了,我就不玩了。”
“行行行,大美女。”桂花像打了雞血似的興奮極了。
桂花對兩個男人說:“人家秋香第一次玩,可要憐香惜玉,讓著點。”
“要得要得,吃包子不算。”兩個男人就像餓了幾天的瘦狗見到了骨頭,迫不及待地把牌碼好。桂花系統(tǒng)地交代了秋香一些打牌的要領。
秋香摸著牌,這感覺真好,硬硬的,滑滑的,打了幾牌,腦子里除了牌,什么都拋到九霄云外去了。
真是牌落生人手,秋香連和了幾個滿貫。桂花直夸秋香手氣好。那兩個男人直嚷嚷:“真是高人不露相,還說不會,打的這么好——黃麻子這狗日的還不來。”
秋香理著贏著的錢,有些興奮,她還真希望黃麻子不要來了。
五點過,秋香說是要煮飯去了,不玩了,兩個輸了錢的男人哪里肯放她走?涎著臉:“美女,再玩一圈,再玩一圈就散了。”
秋香只得硬著頭皮玩了一圈。六點鐘了,秋香說什么也不玩了,站了起來,說娃娃沒帶鑰匙,可能還在外邊。兩個男人罵罵咧咧的把牌一推:“不玩算球了,掃興!”
桂花直夸秋香天生是打麻將的料,今天贏了這么多。秋香摩挲著手里幾張紅票子,心里也有幾分小激動。
秋香回到家,賽康和格格相互依偎著,蹲在門口,像兩只無家可歸的流浪貓,蜷縮在墻角。格格見媽媽來了,委屈地哭了起來:“媽媽,你去哪兒了?我們作業(yè)都做不成了。”
看著兩個可憐的娃娃,秋香有些內疚,發(fā)誓不再玩了,急忙摟過格格,一邊開門,一邊安慰:“格格乖,媽媽有點事耽擱了。”
秋香下定決心不再去了,想想桂花那娃娃,就像沒娘的孤兒一樣,悶聲不作氣的,干的事情讓人吃驚,偷桂花的錢,偷班里同學的東西,放學了就在學校門口打游戲機。老師三天兩頭請家長,可是桂花老說,沒時間去。老師也不管了。一想起這些來,秋香后背就發(fā)麻。不去了,堅決不去了!
六
秋香幾天都不去小板房了,待在家里,又陷入了莫名的無聊之中。呆呆地坐在沙發(fā)上,盼著太陽快點走,孩子快點放學。可春天就是讓人煩悶的日子,白天老長,那太陽像是故意跟秋香作對似的,老是賴著不走。秋香想起坐在小板房門前的時候,那時間好快呀!她伸出指甲,想剪剪,指甲刀已經(jīng)沒法夾到指甲了。秋香看著自己閑得粉嫩的手指,忽然想到了摸麻將的感覺,那感覺太美妙了,仿佛是一杯透心涼的珍珠奶茶,喝下去,所有的困倦和煩躁都飛到九霄云外了。秋香玩弄著手指,那感覺太美妙了,太誘人了。
在家里憋得發(fā)瘋,秋香又來到小板房里。那摸著麻將的感覺太爽了,時間好混,什么事都不用想。秋香自己對自己說:“還是來小板房里好消磨時間,自己堅決不玩,耽誤不了管娃娃。”麻將就像海洛因一樣慢慢地引誘著秋香。
“哎喲,美女,贏了錢就不來了,你也太那個了。”一個男人挖苦秋香。
“不是不是,我真的不想玩。”秋香紅著臉爭辯道。
“是看不起我們吧?”
“是老公管得緊吧?”
“嘻,真沒出息,現(xiàn)在的女人還被男人管著。
小板房里一句句刺耳的聲音就像一把把罪惡的毒箭一樣,把秋香體內那點人性本能的罪惡一點點的刺激出來,漸漸膨脹。
“來,玩一會,美女。”
那麻將嘩啦嘩啦的聲音太美妙了,太誘人了,狠狠地牽扯著秋香的心。管他的,秋香心里想,我只要把握好自己,就玩一會兒,該給孩子做飯,就去做,這也沒什么大不了的。自己控制好,絕不像桂花一樣,坐在麻將桌上,就像釘了釘子,挪不動,把握好,控制住,秋香暗下決心。桂花不是說過嗎,不會娛樂的女人就是傻女人,白來世上走一轉。
“我只玩到五點半,到點說走就走。”秋香賭氣似地睜著眼。
“隨你便,沒有哪個拿毛拴著你。”
秋香坐上麻將桌,摸著滑溜溜的麻將,這感覺太爽了。一切都拋在腦后了。
“媽媽,你怎么才來?我餓了。”格格一臉委屈。
“餓了,不會自己做飯,那么大的兩筒人了,還專門等著老丫頭。”秋香沒好氣地吼道。
秋香輸了錢,心情糟糕到了極點,第一次沖孩子發(fā)火。兩個娃娃嚇得不敢做聲,驚恐地看著秋香。
“拿去,買兩包方便面,自己吃去。”秋香甩出十塊錢,倒在沙發(fā)上,一動不動。
也怪自己,明明贏了三百塊錢了,說要回家給娃娃做飯。桂花就罵她:“你一贏錢就走,人家個個都在罵你,你不害羞,我還害羞呢。娃娃,娃娃,就你有娃娃。都讀三年級了,還慣著他們,不會讓他們自己學著做。我看你,遲早死在娃娃身上。”
聽著這么難聽的話,秋香賭氣不走了,橫下心來,老娘就不走了,奉陪到底!結果,形式馬上逆轉,秋香不但把先贏的三百塊輸完了,還倒輸了四百五十塊。越輸,秋香越急,越想扳本,心情越糟糕,麻將好像故意跟他作對,明明打一張就叫著清一色的雙滿貫,可是,那一張卻放了下家的炮,轉過去,對家自摸,上家也跟著自摸,落得個尾家。有一牌,秋香一手拿了三個托,一看,手里只有兩張條子,一個萬字,其余的全是字,只要對著兩對字就是字一色,贏他個一百五十塊。可這幾個雜種也太精了,就是不打字,老扣著,自己又摸不著字,最后黃牌。推倒牌一看,字全部在幾個雜種手中。秋香越想越生氣:老娘明天一定要去扳本。
娃娃吃了方便面,做完了作業(yè),呵欠連天,睡覺去了。好大一晚上,順子回來了,看到瓢朝天碗朝地的,飯也沒煮,秋香趴在沙發(fā)上,順子嚇慌了,關切地問:“婆娘,哪兒不舒服?趕緊去看看。”
秋香沒好氣:“沒有!”
“怎么啦。還沒到更年期嘛。”順子扳著秋香的雙肩,把她翻過來,一股刺鼻的煙味襲來。
“你抽煙了?”
“沒有!”
“去哪里了,那么大煙味兒?”
“沒去,煩死了!”
順子不再問什么,默默地煮了一碗面,挑坨冷油,放點鹽巴,稀里嘩啦吃了。順子似乎明白了什么,他不跟秋香吵架,怕影響著娃娃,壓低了聲音說:
“秋香呀,你這段時間不太對勁,頭發(fā)也懶得梳,好長時間不洗澡,你變得有些窩囊了。你是不是去什么不該去的地方了?要注意呀,娃娃要緊。”
秋香惱羞成怒,杏眼圓睜:“咋啦?我窩囊了,你重新討一個去,什么是不該去的地方?我去賣了,要咋個整?”
順子累了,不想吵架,更怕嚇著娃娃,也怕鄰居笑話,準備哪天放工早一點,好好跟秋香談談。
秋香依舊打著麻將,有時贏,有時輸,飯也懶得做,贏了錢就帶著賽豪和格格下館子。輸了錢,就讓賽康和格格泡方便面。
一天,秋香輸了錢,賴著扳本,已經(jīng)打到晚上7點鐘了。贏了錢的幾個賭友說什么都不打了,秋香只好怒氣沖沖地回到家。賽康吃著方便面,格格趴在桌子上睡著了,滿臉淚痕,下巴底下一灘口水。
秋香怒氣沖沖地質問賽康:“妹妹怎么了?”
賽康頭都不抬,也不做聲。
格格被驚醒了,見媽媽回來了,哭了起來,嗓子嘶啞:“哥哥欺負我,不分我方便面。”
“什么?有你這樣當哥哥的?”秋香暴跳如雷,一巴掌扇在賽康臉上。賽康嫩嫩的臉上瞬間出現(xiàn)了暗紅的巴掌印。他騰地站了起來,指著格格:“誰叫她告我的?”
“告你什么?”秋香余怒未消,“格格,怎么回事?”
格格一邊抹眼淚,一邊用嘶啞的聲音控訴:“哥哥幾天都沒交作業(yè)了,老師問為什么不交,他哄老師說,他肚子疼,沒有做。老師就相信了他。他哪里是肚子疼?明明是一放學就跟著幾個男生去打游戲,我就告老師,回來他就不分我面吃。嗚嗚嗚……”
秋香氣得臉色發(fā)紫,操起掃帚向賽康劈頭蓋臉打去,一邊打,一邊罵:“你這個死娃娃,黃毛還沒掉,奶水還沒干,就學會打游戲了。”
“啪啪啪”賽康被結結實實地打了一頓。
賽康出人意料地忍著,不哭也不躲,牙齒緊緊地咬著,兩眼倔強地盯著秋香,仇恨的目光直刺秋香雙眼。賽康一下子變得陌生起來。
“說,為什么要去打游戲?”
賽康緊盯著秋香,面前的女人似乎不再是他們美麗、溫柔、慈愛的媽媽,而是一個讓人討厭的丑陋的巫婆。他咬牙切齒,狠狠地從牙齒縫里里蹦出了幾個字:“你為什么一天只知道打麻將?”
秋香一驚,敢頂嘴了,敢編排老娘了,這個忤逆子,反了他了。桂花說的對,這孩子從小就不能慣著,慣多了,失去獨立性,大人一不管,就會這樣,今天非好好教訓他不可!
“啪!啪!啪!”
“你翅膀毛還沒硬,就敢編排我了,我是不是你媽?有你這樣說媽的?”
“啪!啪!啪啪啪!”
“你不配做我——媽!”賽康噙著淚,強忍著不讓它流下來,爬起來,推開臥室門,狠狠關上,反鎖著。
秋香又氣又委屈,她不明白,好好的孩子為什么會變成這個樣子。是跟城里的壞孩子學壞了嗎,她真后悔把孩子弄進城里來讀書。
秋香倒在沙發(fā)上抽抽搭搭地哭了起來。
七
秋香依然去小板房打麻將。
秋香正打的歡,手機響了。秋香一看,是朱老師的電話,忙說是娃娃老師的電話,示意其他幾個人出牌輕點。朱老師在電話里說:“賽康和格格這兩天不對勁,老是差作業(yè),上課無精打采的,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這次測驗,兩個娃娃下降得太快了。賽康語文才考69分,數(shù)學考了72分;格格呢,脾氣老大了,兩科都沒及格,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影響到孩子了。三年級可是關鍵呀,要注意呀,你有空來學校一下,我們交流交流一下。”
秋香心不在焉地聽著,胡亂出了一張牌。放了對家三滿貫。秋香狠狠地掛了電話。狠狠地罵了一句:“這個掃帚星,一個電話害老娘放了三滿貫。”
桂花憤憤不平:“這些雞巴老師,動不動就會訓家長,家長倒教得好娃娃,還要他們搓球!秋香,別理他,打牌!”
秋香心煩意亂,專門放大炮,輸了好幾百塊。她恨死了那個瘟神朱老師,一個電話害她輸?shù)裟敲炊噱X。
回到家,氣不打一處來,狠狠地訓斥著賽康和格格:“你這兩個不爭氣的死娃娃,一天只知道玩,玩,玩!一點都不理解大人的辛苦,花那么大的代價,把你這兩個死娃娃整進城里來讀書,不好好讀,你們上課發(fā)什么呆,不好好聽老師講課。說人說多了,養(yǎng)著你這兩個報應。不好好讀,長大了就像你爹一樣打工去。氣死我了,這兩個不爭氣的死娃娃。”
秋香越罵越生氣,揚起巴掌,“啪啪啪”,賽康和格格分別挨了幾巴掌。
格格第一次挨罵,還挨打,哭著躲進臥室里睡了,飯也沒吃。賽康照例咬著牙,兩眼露著仇恨的目光,不哭不鬧,躲進臥室,反鎖著門。
第二天,秋香又來到小板房。
“秋香,把那個啥子雞巴老師的電話拖黑掉,省得一天鬼喊吶叫的,煩死了。”
“是呀,昨天害老娘輸?shù)裟敲炊噱X。”秋香一邊憤憤地罵著,一邊把朱老師的電話拖進了黑名單里。
秋香自摸了個清一色,笑得合不攏嘴。桂花說:“你看,老師就是喪門星,一打電話,你就霉氣,今天手氣可好了。”秋香一邊點頭,一邊贊同:“就是,就是。”當她把錢收完,電話響了。桂花叫她不要接,干脆關機,手氣正好,不要觸了霉氣。秋香拿出電話,見是順子打來的,極不情愿地接了起來。
“秋香,你在哪里?朱老師說娃娃沒去上學。是咋個的?”
“什么,沒去上學?”
“大驚小怪的,娃娃在哪里玩一會兒,玩夠了,他就回來了。這些老師沒事找事做,把自己當做美國總統(tǒng)似的。”桂花喋喋不休,“接著打,娃娃會咋個?”
秋香有些慌亂,這兩個死娃娃會去哪里呢?可又一想,說不定在家里呢,等晚上回去好好收拾這兩個死娃娃,越大越淘人。秋香繼續(xù)打牌。
順子心急火燎地沖進來了:“秋香,你咋還在這里?娃娃還沒去上學,老師急得發(fā)火了,說打你的電話,正在通話中,你跟誰通話,通這么長時間。快點,我沒鑰匙,回家去看看。”
秋香只得跟順子回家。順子著急兩個娃娃,來不及埋怨秋香,飛也似地往家里跑。
順子搶過鑰匙,打開門,娃娃不在,一看,娃娃的臥室門開著。順子撲進臥室里,床上一片狼藉。床上放著一頁作業(yè)本,順子搶過來一看,紙上歪歪斜斜地寫著:
爸爸,對不起,我們要去遠處了。
親愛的老師,親愛的同學,再見了。我們也舍不得你們,你們對我們兄妹倆太好了。特別是朱老師,就像我爸爸一樣。我也好想讀書,將來考大學,找個好工作,掙很多很多的錢,孝敬我爸爸。可是我們讀不下去了。
我們的媽媽,不,她不配做我們的媽媽,那個女人成天只知道打麻將,不管我們,我們回家,沒有飯吃,我們就吃方便面,有時候,家里沒有錢,我們就什么都吃不上,餓著肚子。我們沒心思讀書,上課時,肚子餓得呱呱叫。我們恨那個女人,我們懷疑,我們不是她親生的。她一輸錢,就像只母老虎,拿我們出氣,就打我們。爸爸起早貪黑地做工,家里只有我們兩個,像沒媽的孩子一樣孤零零的。還隨時是那個女人的出氣筒。我們呆不下去了,在這個冷冰冰的家里,一天都呆不下去了。
昨天晚上,她又打我們了。我們想,哪一天她輸多了,會把我們拿去賣了。我們商量了一下,趁現(xiàn)在,她還沒發(fā)瘋,我們就離開家吧,到外面打工,等掙了錢,回來孝敬爸爸,讓爸爸跟她離婚,不要她了。
爸爸,我們愛你,你不要找我們,你找不到的。
再見了,老師,再見了,同學們。朱老師,我好想做你的娃娃。
賽豪、格格
×年×月×日
順子幾乎崩潰了,像一頭發(fā)怒的雄獅,發(fā)瘋似地沖了出去。秋香也徹底慌了神,跟在順子后面。
順子跑到客運站,像沒頭的蒼蠅亂竄,聲嘶竭力地喊著:“賽康——格格——”
“在那里!”秋香一眼看見了候車廳前的賽康和格格。
順子定睛一看,賽康和格格還戴著紅領巾,一個瘦高的男人戴著墨鏡,一手提著賽康的書包,一手搭在賽康肩上。后面是一個胖胖的女人,滿臉慈祥的笑容,一手提著格格的書包,一手拉著格格。格格睜著狐疑的雙眼。他們猶如親昵的一家人,正向一輛黑色的轎車走去。
“賽康——我的兒呀!”順子一下?lián)溥^去,摟住賽康,那一男一女丟下書包倉皇地逃向轎車。黑色轎車風馳電掣般,一轉眼不見了。
順子把賽康和格格緊緊地抱在懷中,雙腳發(fā)軟,靠在路邊的梧桐樹上,無力再邁出一步。梧桐樹已經(jīng)長出濃密的葉子,投下一片濃濃的綠蔭,擋住了晚春的驕陽。梧桐樹下的小花開得正艷,紅的、白的、紫的,映著格格紅撲撲的小臉。賽康緊閉著嘴,倔強的雙眼露出復雜的眼光,望著街上一群群放學的學生。他們的父母有力的大手牽著他們稚嫩的小手。有一個年輕的媽媽背著書包,彎著腰在跟孩子談著什么,孩子走路不老實,一蹦一跳地,不時發(fā)出“咯咯咯”的歡笑聲。秋香雙眼恍惚,呆呆地看著這一對對親昵的身影。
作者簡介:孫繼榮,昭陽區(qū)四小教師。
【責任編輯 趙清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