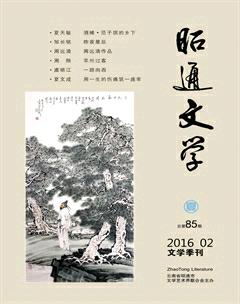碎
黑夜在掃帚的揮動下,一絲一絲地刷亮了。
“媽,你歇一會吧。”
“我不累,你先把那幾個洋芋吃了,趁熱!”
女兒無奈地搖搖頭,坐在一家商店的臺階上,打開一塊藍色頭巾包著的口袋,熱氣凝結成的水蒸氣籠罩在塑料袋中,打開口袋,一股洋芋特有的香氣中包含著濃濃的醬香撲鼻而來。細心的母親把三個小洋芋都一切為二,在中間夾上一層醬。吃著這醬香四溢,外皮金黃的洋芋,即使是在隆冬,坐在冰冷的臺階上,女兒的心里也是暖洋洋的。雖然母女倆昨天曾吵得天翻地覆。
昨天早晨,母親早早地出了門,想讓女兒多睡會兒,她比平時提前了一個小時起床,輕手輕腳地關上門,扛上長長的掃帚出了巷子。
夜是那樣的寂靜,特別是隆冬的夜。
女兒半年前下崗了,在環衛站找到了一份臨時工,負責清掃北門的一條街道,這條街道是北門的菜市場,連招聘的臨時工都不愿意打掃。腐爛的菜葉,惡臭的泥溝,宰殺牲畜的血漬……這一切都讓曾是地毯廠勞動模范的她連連作嘔。一個月下來,她瘦了整整10斤,不是勞動強度太大,而是——只要端起飯碗,看著桌上的菜,就不由自主聯想到菜市場的情景,頓時胃里就翻江倒海,無法下咽。可為了孩子,為了她的小浩——正上六年級的兒子,她必須堅持下去,像她這樣,已經43歲的下崗女工,找工作已沒有了選擇的余地。她需要這一千塊錢的工資,而且是那么迫切的需要。
女婿死了,死在了一條陽溝里,陽溝很窄,他的身子都還露在溝外,只是他的臉朝下,頭剛好淹沒在那像墨汁浸染過的漿糊一樣惡臭的陽溝泥中。女兒一滴眼淚都沒有流,只是請了幾個鄰居把他的尸體用一張板車拉回了家,用一盆又一盆的清水把他擦干凈,那惡臭的泥漿都無法掩蓋刺鼻的酒臭,他死前一定喝了不下兩斤的酒。擦干凈頭,再接著擦身子,擦完身子,接著擦那雙手,擦著擦著,她死命地拽起兩只手笑了,而且是放聲大笑:“你逞強啊!你發威啊!你來打我啊!有本事你就打啊!你不是就只有打婆娘,打兒子的本事嗎?你連我媽都打過了!你再來打呀!不打你就不是人!來啊!來啊!你給我打啊!哈哈哈哈……你終于死了!終于死了!老天長眼啊!我的詛咒顯靈了!顯靈了!”母親看著女兒瘋癲欲狂的樣子,嚇壞了,撲過去,一個巴掌扇了過去,女兒怔怔地看著母親,半晌才回過神來,哇地一聲哭了起來。母親摟著女兒,拍著女兒的背,喃喃地說:“哭出來就好,哭出來就好。”
母親掃得很仔細,路燈的光懨懨地照著這一半骯臟,一半潔凈的街道。攤位上攤主丟掉的蔬菜中也夾雜著一些能撿回家吃的,每每掃到這些蔬菜,母親總是如獲至寶地放入隨身攜帶的編織袋中。母親用一根布帶子縫在編織袋上,留一個口,然后再把布帶系在腰上,這樣就能掃地,撿菜兩不誤了。母親總得意地向女兒炫耀自己的“發明”,也給女兒做了一個這樣的袋子,只是女兒嫌拴著難看,就擱在墻角一直沒用。母親癟癟嘴嘆道:“掃地還窮講究個啥?天又都還沒亮,鬼老二來看你!”可自從女兒發現母親拴上這個袋子后家里幾乎不用買蔬菜后,女兒也終于在一個掃地的早晨系上了這個袋子。那天,母親為此樂了一整天!
掃著掃著,警車的警笛聲呼嘯著傳來,驚呆了黑夜,也嚇壞了母親。一輛白色的面包車從母親身旁飛馳而過,一個蒙面的男子從車上扔下一個黑色的口袋,還砸到了母親的掃把。母親一抬頭,剛好看到蒙面男子的眼睛,那兇狠的眼神讓母親覺得一股寒氣從腳底直沖向腦殼頂,正發愣,警車已開了過來,又從母親身邊呼嘯而去。那個黑色的口袋靜靜地躺著,母親很好奇地想打開看看,可眼前頓時閃過那個蒙面男子兇殘的眼神,母親又哆嗦起來,萬一那口袋里裝的是一個人頭或幾只斷手或斷腳,那該如何恐怖啊!母親盯著那個口袋,猶豫不決。母親試探著用掃把戳了幾下,里面的東西很硬,母親猶豫了很長時間,似乎聽到街上有人開門的聲音,才慌忙地一把扯開口袋,借著昏黃的路燈,母親驚呆了——竟是一口袋的錢,而且是清一色的百元大鈔,大概有幾千塊錢吧!也或許有幾萬!總之,母親活到68歲就沒見過這么多錢。母親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突然,有人輕輕拍了一下她的肩,“媽呀!”母親大聲地叫了起來,打破了這慌亂的夜。她一下把裝錢的口袋緊緊摟在胸口。
“媽,是我!你怎么了?”
“哎呀!嚇死我了,你這個死娃娃嚇死我了!”
母親一把扯住女兒,往家就跑。
“你為什么要跑啊?地都還沒掃完,掃把不要了嗎?媽,你怎么了!”
母親什么也不說,死命地攥住女兒的手,飛一般地跑回了家。關上門窗,拉上窗簾,母親拉亮了電燈,用那顫巍巍的手打開了黑色的垃圾袋。一捆捆紅紅的百元大鈔在昏黃的燈光下,散發著誘人的光芒。女兒一下子驚呆了,這得是多少錢啊!這輩子也沒見過這么多的錢!在銀行柜臺里都沒放著過這么多的錢!一捆就是一萬,銀行里就是這樣捆的。女兒一下跪在地上,抓起口袋一股腦兒倒在地上。一、二、三、四……整整十五捆,十五捆就是十五萬啊!十五萬,那得用多少年才花得完啊!母親趕忙拿起一捆數了起來,一張張紅色的鈔票在母親的手指頭間飛舞,母親突然覺得今天的口水似乎都要被蘸干了,那一捆錢還沒數完。女兒突然看見,在那一堆錢當中還有幾袋純白色,亮晶晶的顆粒。女兒拿起一包打開,聞了聞,有股刺鼻的氣味。女兒數了一下,有六袋,大概有家里用的一袋鹽巴那么重。女兒也不知道這是什么,就先把這六袋東西裝在了口袋里。“媽!”女兒喊了一聲,正在數錢的母親嚇了一跳,腿一軟,一屁股坐在了地上,那一疊錢也散了一地,“啊!錢!錢!”母親慌亂的在地上撿著,又是激動又是害怕。女兒突然吼了一聲:“媽!別撿了!”母親惶惑地看著女兒不知所措。女兒堅定地對母親說:“媽,這錢咱不能要!”“你瘋了吧!這么多錢不要,你以為是馬路邊的一分錢啊?還交給警察叔叔不成?”“媽,你聽我說,這么多錢,誰丟了誰不心疼?不著急啊?我們不能要這些不明不白的錢,要是人家是等著救命的錢呢?”“那,萬一是哪個有錢人丟的呢?路口五層樓高的那個廖家,上次他兒子不也是弄丟了二十萬嗎?你看人家,屁事都沒有,還逢人就講,舍點小財免災!二十萬啊!人家就一小財。二十萬擱我們家夠吃幾代人了!而且我又沒搶沒偷,憑什么拿去交了。俗話說,撿著當買著,金子銀子買不著!”“媽,撿的就永遠不會是自己的,我們人窮可志不窮。”“你還有什么志,好端端的一個勞模,現在都掃大街了,就差去要飯了。當初多少廠長、科長追著你屁股后面跑,你正眼都不看人家一眼,偏要跟那個花燈團那個拉二胡的,當初就罵你瞎了眼吧,你還不信,現在好了吧,年紀輕輕就守了活寡,我是哪輩子造的孽喲!”母親坐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淚地哭了起來。女兒被母親一頓數落,戳到了疼處,也再不言語。哭了一會兒,母親一骨碌爬起來把錢三下五除二地收進口袋轉身進了房間,臨關房門還扔下一句,“我不管,這錢是我撿的,我說了算!我就算不替我,不替你著想,我還要替我外孫著想。”外孫這個詞,讓女兒一下子閉了口,呆立在房中。
黃暈的燈光下,一家人坐在桌邊吃晚飯,小浩看著外婆和媽媽鐵青的臉色,又不言不語,知道她們一定又吵架了,故意講一些學校里開心的事逗她們笑,還神秘兮兮地對外婆說:“外婆,你知道我們學校最近發生了一件重大新聞嗎?我們班的黃習瑞同學昨天撿到了一張銀行卡,你知道那卡上有多少錢嗎?”母親的神色一下子變得緊張起來:“有多少?”小浩看著外婆的神情,得意地說:“你猜不到吧!哈哈!你一定想不到吧!有五十萬!”“這么多!他咋辦了呢?快說,快說!”“他交給了我們班主任,班主任又交給了校長,校長又打電話給警察局,后來說是一個外地老板的,人家報了案,后來知道是我們班的黃習瑞同學撿的,還給我們班和學校送了兩面大錦旗呢!上面寫著‘拾金不昧好少年!掛在教室里,其他班的好多同學都來我們班參觀呵!那陣勢可壯觀了!今天校會上又表揚了我們班,我們班的同學可長臉了。哦!我們班出名了!我以后如果遇到這樣的事,也一定要拾金不昧!”母親臉色一陣灰暗,女兒只顧低頭扒飯。
晚上睡覺前,母親來到了女兒房間,極不情愿地把那個裝錢的口袋丟在女兒床上。嘟囔著:“算啦,這錢我也要不起,人家說,不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我活到六十多了都沒做過一回虧心事,現在倒好,撿了那么多錢,這一整天我都提心吊膽,魂不守舍的,想來,我們是窮命,抱著錢就睡不好覺。你明天就拿去交給公安局的吧!”“媽,我們明天掃完地,一起去交!”
母親已掃到了街口,街燈把母親的身影拉得很長很長,掃帚像兩個張牙舞爪的厲鬼,在母親的影子左右跳動,女兒看著一陣心驚,半個洋芋滾落在地上。
“媽!你先回去吧!剩下的我來掃。”母親站住了,右手拄著掃帚,左手捶了幾下腰,嘆口氣道:“好吧,我近來的腰啊,老是不聽使喚,彎下去就難得直起來,真的是老嘍!”母親捶打著腰,在寂靜的街上,空聲氣響,一聲聲也捶打在女兒的心上。“媽,等我掃完地,我帶你去醫院看看!”“有啥可看的!我吃點去痛片就沒事了,沒必要亂花那些冤枉錢!那我先回去了,順便叫小浩起床上學。”“唉,你慢點!”看著母親蹣跚遠去的背影,幾滴淚落在了女兒揮動的掃帚上。
寒風吹過,那棵梧桐樹唯一一片樹葉也戀戀不舍地打著旋告別了枝頭,最后它撲落在掃帚邊,一下就被泥濘的掃帚掃到了那一堆垃圾中,這是這個冬天的最后一抹金黃啊,脆生生地就粉身碎骨了。
終于掃到了盡頭,女兒拖著疲憊的掃帚往家里走,剛走到街口,幾個手拿菜刀,鋼管的人,從巷子里沖出來,朝左邊飛奔而去,瞬間就消失在街角。一種不祥的預感突然漫上了女兒的心頭。叮——電話響了,女兒嚇了一跳,哆嗦著接通電話,從電話那頭傳來了鄰居方姐的聲音:“你在哪啊?快點回來!你家出事了……”“啊!”女兒慘叫一聲,沖進了巷子。
“媽!媽!”母親趴在家門口的地上,女兒把她的身子翻轉過來,頭上的血汩汩地淌滿了整個臉,一雙眼睛驚恐地瞪著天,剛要張口,一口鮮血從口中噴了出來。“他們……他們……要……要那個袋子……小……浩……去攔……我……想……救……他……那個……蒙面……眼……睛……”“媽呀!媽——救命啊!”母親凄厲的慘叫撕裂了黑夜,在慌亂中,她睜開一絲惺忪的睡眼,黎明猶如被封印的魔鬼從黑夜的眼中傾瀉而出。
母親死了,在救護車還未趕到的時候,女兒就已知道,她挺不過去了,那血像水庫開閘似的從母親頭頂的那個洞狂涌出來的時候,女兒就知道她活不了了。女兒在那一剎那變得萬分平靜,她似乎看到母親拉著她的手走過那條小巷,那小巷的青石板是那樣干凈,泛著青白的光澤,母親長長的辮子隨著母親起伏的步伐跳躍、掃動,發絲滑過她的臉頰,癢癢的,暖暖的,一抬頭,是爸爸,他笑盈盈地走了過來,牽起媽媽的手,快步地走了起來,女兒有些跟不上了,她說:“媽媽,走慢些。”爸爸卻在一旁說:“走快些!”他們飛跑起來,女兒的手被拽得生疼,一松手,爸爸媽媽穿過一個天井,不見了!
兒子也死了,他趴在臥室的門檻上,手里還攥著一塊黑色的塑料袋。那可憐的孩子一定以為有人要搶他家的東西,他要保護這個家!女兒歇斯底里地嚎叫了起來,像失去幼崽的母狼。
女兒醒來時已是第三天的早晨,陽光柔柔地、暖暖地照在病床上,她極不情愿地睜開眼睛,她覺得自己還在很累、很累,還遠遠沒有睡夠,可陽光刺痛了她的眼要她醒來。她看見了警察!一瞬間所有的場景像電影膠片飛速的剪輯手刃了她復蘇的大腦,心臟強烈的疼痛讓她雙眼涌出了淚水,她掙扎著猛地坐了起來哭喊著:“不——”再次暈倒在病床上。
當她再次醒來已是深夜,夜更加地柔和,沉沉地、靜靜地,仿佛它從沒有走遠,從沒有真正離開。女兒哭了,靜靜地哭,默默地流著淚,把傷口清理、打包、封存、加密,然后投進屬于自己的空間,再加上封印,在以后的每個夜深人靜時啟封、拆開、和著淚與血吞咽。
出院后,女兒每天八點準時來到北門派出所,默默地坐在所長辦公室門口,不哭也不鬧,什么話也不說,只是那樣靜靜地坐著,直到派出所的人下班,她又默默地離開。她的安靜讓派出所的民警們感到那樣地壓抑和心酸。
兩個月后,所長告訴她所有的涉案人員已抓獲,年齡都還不到16歲,是一群吸毒人員,她母親撿到的那十五萬是他們搶劫來的毒資,那六袋白色的東西是冰毒。由于當天早晨被警車追捕,才故意從車上丟下。因為都是未成年人,所以無法判死刑。他們當中有兩個都是孤兒,另外三個的監護人——也都是在外打工的單親家庭,從這三家也只爭取到了五萬七千元的賠償。
顫巍巍地接過那裝有五萬七千元的賠償金的口袋,女兒一句話都沒有說。她跪在地上給所長磕了三個響頭后爬起來就往外走。
街燈都已亮了,白晃晃的閃著空洞的眼,那市中心的第一高樓——皇上皇大酒店頂層四角的航空障礙燈緩緩地閃著迷離的眼,那四只眼睛誘惑著女兒蹣跚的腳步。她沒有坐電梯,她順著樓梯一層一層地向上爬著,每一級臺階像女兒一生中的一天,每上一級臺階就是女兒人生電影中的一張膠片,它們滾動著,播放著,交織著,所有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在其中上演……
終于走到了最后一級,三十七層樓的最后一級,女兒撲倒在地,她暈了過去。
女兒黎明睜開了一絲眼,緩緩地醒了過來,她打開了那裝有五萬七千元的賠償金的口袋,就像當初打開母親撿回來的那個垃圾袋一樣哆嗦著雙手。她一張一張地抽出來,一張一張地撕了起來,先是一分為二,再一分為四,再拋向天空,那紅紅的百元鈔票在風中一下就沒了,這讓女兒很生氣,百元大鈔啊!怎么能一下就沒了呢,她抓起了一沓狠命地撕了起來,錢鋒利的邊緣割破了她的手,鮮血染紅了鈔票,女兒看到了血,突然變得亢奮起來,她瘋狂地撕著,撒著。鮮血不僅染紅了鈔票,染紅了衣服,也染紅了黎明的眼……
女兒撕得很累,她似乎聽到了地面的狂躁,越過欄桿,她看見整條道路的人們都沸騰了,撿錢的人們阻斷了交通,吵鬧聲、叫罵聲、哭喊聲、呵斥聲……此起彼伏,她更加亢奮,她看到了人們抬起頭在尋找撒鈔票的位置,她看到了警車上跳下來的警察,她撕都不撕了,直接地撒,大把大把地撒……
當警察和酒店經理出現在天臺的時候,她撒完了最后一沓,然后沖著他們微微一笑,縱身跳下。
又是一年樹葉飄落的季節,那金黃的落葉飄到了馬路上,飄到了人們腳下,汽車下,自行車下,脆生生地碎了……
作者簡介:陳允想,昭陽區二中高中語文教師,愛好文學。2005年開始文學創作,寫散文、小說和兒童文學,在多種文學刊物上發表過作品,作品曾入選《昭通文學精品選》,散文作品榮獲省級征文獎。
【責任編輯 趙清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