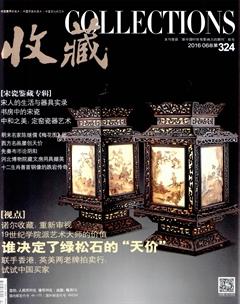先秦布幣論陰陽
馬肖
先秦錢幣,是指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前出現的貨幣,包括原始貨幣、金屬稱量貨幣和金屬鑄幣等,這是貨幣從產生到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根據不同的流通區域,逐漸形成了先秦四大貨幣體系,而布幣就是其中濃墨重彩的一章。布幣主要流通于三晉、兩周地區,其形制源于農具鏟。布幣又可分為空首、平首兩大類型,每個類型中根據其首、肩、足部的變化,又可以細分為若干品種。
尖足布中陽(圓頭陽)
僅就平首類中的尖足、方足布而言,其上面的文字往往是紀地文字,使我們能夠從幣文中推斷出鑄造地點。尤其是有些幣文中出現的帶有的“陰”“陽”之地名的(見圖),值得探討研究。如尖足之中有“晉陽”“陽曲”“陽地”“中陽”“壽陰”“大陰”等;方足之中最為常見的有“平陽”“安陽”“宅陽”,相對少見的有“?陽”“陽邑”及“平陰”“壤陰”等。古人認為山南水北為陽,反之為陰,這個概念主要與中原地區的太陽照射有關。黃河中下游地區在北回歸線以北,太陽會從南面照射,山的南坡陽光充足,稱為“陽坡”;而北坡曬不到太陽,稱為“陰坡”。而水在山間流淌,水的南面被山坡遮擋曬不到太陽,稱為陰;反之水的北面稱為“陽”。故中國的許多地名即由附近所處山水的位置而命名。
尖足布中陽(橢圓頭陽)
在先秦布幣上,“陰”字的變化甚少,不但沒有字形上的變化,也未見省筆現象,幾乎皆作“?”形。而“陽”字的變化較為豐富,在尖足布“晉陽”“陽曲”中,皆作“?”或“?”形,沒有“阝”部;“阝”是“阜”旁的簡寫。《說文解字》:“阜,大陸也。”其原形應是“?”,作群山連綿之形。石鼓文中的陽作“陽”,看來“阝”這個部首應該是指陸地上連綿的山。
尖足布陽地(倒三角陽)
尖足布“中陽”的“陽”字都有“阝”部,筆者采樣的18枚中陽布中,大多作“?”或“?”狀。類似的情況還出現在“陽地”(舊釋“文陽”)上,筆者采樣了9枚陽地布的幣文,只有一枚沒有“阝”部。以上提到的四種尖足布“晉陽”“陽曲”“陽地”“中陽”都沒有演化出相應的方足布。事實上,絕大多數尖足布品種都沒有進化出相應的方足布,有些品種只是進化到“類圓足”或“類方足”后即戛然而止;反之亦然,絕大多數的方足布品種根本就沒有相應的類圓足或類方足作為它的前身。
尖足布晉陽半(圓頭陽有點)
在方足布中幾乎所有的“陽”都有“阝”部,唯有通常被認為是宅陽異書的“乇陽”布,其“陽”字沒有“阝”部;“乇”通常作“?”或“?”狀,而宅陽的“宅”字寶蓋內的“乇”幾乎皆作“七”狀,二者迥然不同。僅此,并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乇陽”是“宅陽”之省筆。
尖足布陽曲(圓頭陽)
最有意思的當屬“陽”的“日”部之變化,在尖足布中,“日”部多作“○”狀,少數作“⊙”狀。對比青銅器的銘文,“月”字頻繁出現,如《大盂鼎》:“隹九月,王才宗周。”《宜侯?簋》:“隹三月辰才丁未”等。“日”字則非常少見,只在殷商帝辛時期二、四、六“祀邲其卣”銘文中,見有“肜日”“翌日”字句,其“日”字作“⊙”狀。可想當時在刻范之時,用刻具畫出圓形相對不易,于是“○”或“⊙”漸漸演化成“日”或“?”,進而演化為更為方便刻寫的“△”或“▽”。在方足布中,只有平陽布的“陽”字的“日”部有“○”或“⊙”的寫法。在筆者采樣的252例平陽布中,“○”或“⊙”的寫法有18例,僅占約7%。在尖足布“陽地”中,筆者采樣到的9例,有8例的“日”部從“▽”,只有一例作“日”狀。
尖足布大陰半(正三角陰)
文字的演變是一個漫長漸變的過程,從“⊙”到“▽”,從無“阝”到有“阝”,究竟經歷了多久,不得而知。從“○”狀的平陽方足布,相比從“▽”陽的陽地尖足布,究竟哪一個出現得更早一些呢?從文字上看,“○”要早于“▽”;從形制上看,尖足要早于方足。如果錢幣文字的差異僅僅籠統地以“版式”論一帶而過,未免過于草率,這種差異可能是時間造成的演變,也可能是空間造成的國別差異。
尖足布壽陰(正三角陰)
至于“陰”字,無論是尖足布“壽陰”“大陰”,還是方足布“半陰”“壤陰”,皆作“?”或“?”狀,未見有省去“阝”部的情況。“陰”字在石鼓文當中作“?”狀;秦篆作“?”狀,其右半部分皆與“全”或“?”“?”差異較大;不似“陽”字右半部分“昜”在各種寫法中有明顯的演化關系。
方足布宅陽(碗頭陽有橫點)
在文字變化上,平陽方足布最為復雜,不但“陽”字變化多端,連“半”字的寫法也有多種。“陽”字的“日”部有如下多種寫法:“○”“⊙”“?”“?”“?”“▽”“△”。其中“△”為平陽布所特有的,這種寫法的“?”(陽)字與平陰布的“?”(陰)字容易被混淆。“?”字的“△”應當源自“?”(月)的象形字,其變化自“?”→“?”→“?”→“△”,這與平陽布之“△”在根源上存在著區別。平陽布之“△”可能根本就是“▽”的誤寫,以致訛訛相傳,竟成定式。事實上,“△”式寫法在平陽布中所占比例不小,在筆者采樣到的252例中有54例,約占21.5%。
方足布平陽(圓頭陽)
平陽,地望在今山西臨汾,韓國建都于此120余年。后來,在秦國東進的過程中,平陽被趙國短暫占據;秦趙長平之戰后,不但平陽落入秦國之手,連上黨也被秦吞并。因而趙國未必有暇鑄造平陽布。在趙國通行尖足布“晉陽”“陽曲”之時,韓國極有可能已經在平陽開始通行平陽方足布,由于鑄造時間跨度較久,形成了豐富的書寫方式。韓滅鄭之后徙都新鄭,鑄宅陽方足布,其“陽”字沒有“○”“⊙”或“△”這兩種寫法,大多為“▽”與“?”這兩種在平陽布中常見的寫法,且整體風格與平陽布一脈相承。
方足布安陽(倒三角陽頭分筆)
韓、趙、魏三晉諸國以布幣作為主要貨幣。韓國極有可能行使單一形態貨幣,方足布由于大小適中,重量適中,使用最為方便,漸漸為鄰近的趙、魏所學習;魏國的河東地區、趙國的晉中地區漸漸開始通行韓式的方足布。趙鑄幣種類繁雜,其布幣形制總無定式,自尖足演化至類圓足、類方足之后,進而演化至方足的品種不多。目前歸類為趙鑄的方足布除了安陽、平陽、襄垣、壤陰、同是、北亓、藺、祁、鄔等外,其余并不多見。直至戰國后期,趙境北擴數千里,軍事重點有兩個,一是北拒匈奴,二是西拒強秦。由于軍費開支巨大,極有可能在趙境內統一發行安陽方足布,以穩定經濟。時至今日,安陽布不但存世極多,而且出土范圍廣泛,且未有第二種可與其數量相埒的布幣。可以大膽推測,安陽布可能是趙國于戰國晚期統一全國幣制之后的產物。安陽布的大小、文字一致性極強,“陽”字均作“?”態。所謂折二型安陽布,鑄造工藝上與小型安陽布迥異,可能是邊境發行的早期地方性貨幣。
方足布虐陽(倒三角陽長“阝”)
魏國的幣制最為混亂,這與其疆域最為散亂直接相關。魏國疆域曾一度擴展至黃河以西,陜西洛水以北大部,據有上郡、西河郡近70余年,此階段以通行釿布為主。魏惠王時期,約公元前340年前后,魏國“盡失河西之地”且“東敗于齊,南辱于楚”,其河東之地與都城大梁(今開封)所處的黃河以南及河內地區被韓國領土分割開來。這種情況持續了約半個世紀,直至河東地區完全被泰國吞滅;而歸類于魏國的方足布,諸如“皮氏”“莆子”“?陽”等的地望皆屬于這一地區。?陽(或作虞陽),地望在山西平陸縣,屬于河東地區,其“陽”字皆作“?”狀,亦符合安陽布之“陽”字的特點,當屬魏在戰國后期的鑄幣。在公元前293年的“伊闕之戰”中,秦大敗魏韓聯軍,魏將河東之地盡數割與秦國,魏地方足布的流通可能至此畫上了句號。雖然有的書里還提到魏國在河內地區(黃河中段以北)鑄行有幾種方足布,諸如涿(亦釋渝、?)、鑄、向邑等,此地與韓上黨地區毗鄰,而上黨是韓國方足布的通行之地。從幣制沿革看,魏幣完全自成一系,魏久占河西之地,其河西釿布與安邑釿布及梁布皆為橋足布系列,與尖尼、方足布系列迥異。
方足布壤陰(正三角陰)
方足布平陰(正三角陰)
責編 陶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