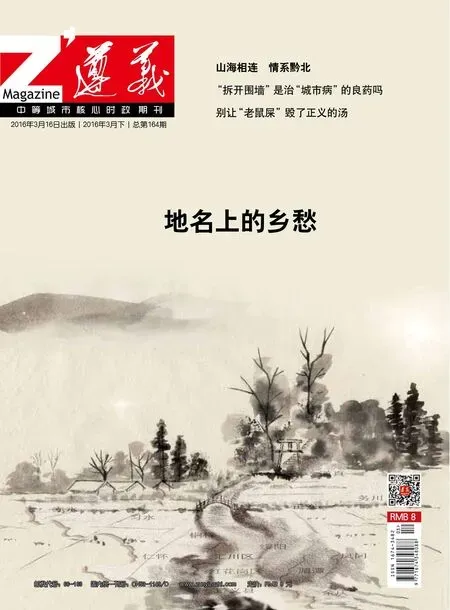朱穆伯:正氣長(zhǎng)存
文丨李 碧
朱穆伯:正氣長(zhǎng)存
文丨李 碧
朱穆伯是中共貴州地下黨員,國(guó)立貴州大學(xué)中文系教授。曾先后執(zhí)教于南開大學(xué)、貴陽(yáng)省立一中、浙江大學(xué)并兼任該校圖書館館長(zhǎng)等。他重基礎(chǔ),重品德教育,常說:“文人最重品德,沒有品德的人,就沒有高尚的靈魂,也就寫不出好的文章”。

貴陽(yáng)教育界在上世紀(jì)30年代有“三怪”,他們是田君亮、李俶元和朱穆伯三先生。
“朱大圣人”
朱穆伯,遵義市人。上世紀(jì)20年代在北京大學(xué)讀書,他的老師是章太炎的門生黃侃,其孤高傲世的性格,博學(xué)精研的精神,頗受黃侃的影響。朱穆伯受北大學(xué)風(fēng)的熏陶,對(duì)于古今中外圖書,凡能得到的都要瀏覽,有的還要精讀。他也喜歡魯迅的作品,認(rèn)為魯迅的小說和雜感之類,既受了西方和日本文學(xué)的影響,也是從《左傳》《史記》這些著作里學(xué)到的高明手法。
在20年代和30年代初,朱穆伯曾在貴州大學(xué)和貴陽(yáng)一中教歷史和倫理學(xué)。他教西洋史,全是用英文本。朱穆伯對(duì)訓(xùn)詁學(xué)、詩(shī)詞均有研究,十分自負(fù),人們戲呼為“朱大圣人”。他的七絕《贈(zèng)弟子》一詩(shī)頗有代表性:“紛紛易過百年身,舉世幾人識(shí)道真。力去陳言奈末俗,可憐無補(bǔ)費(fèi)精神。”
在貴陽(yáng)一中執(zhí)教時(shí),他與田君亮、李俶元等知名教師交情甚篤,常因討論學(xué)術(shù)問題互不相讓,竟至撩衣?lián)]拳,氣平后又和好如初。貴陽(yáng)人戲稱為“三怪”。
田先生和朱先生在一中教書時(shí),有一天,省主席王家烈去視察學(xué)校,校長(zhǎng)王從周在教務(wù)室擺起茶點(diǎn),等教師下課后來聽王家烈講話。朱穆伯回貴州時(shí),王家烈還沒有當(dāng)上師長(zhǎng),是周西成、毛光翔先后離去后,才繼任省長(zhǎng)兼二十五軍軍長(zhǎng)職務(wù)的。朱進(jìn)入教務(wù)室,走到王的面前,用手撫弄其頭及下頷,譏諷地說:“紹武(王的名號(hào)),你來干什么?”王強(qiáng)作不介意地說:“穆伯,你還是當(dāng)年那樣的老脾氣。”就這樣無可奈何地敷衍過去了。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朱穆伯對(duì)國(guó)民黨政府的消極抗日極為不滿,一次,到遵義體育場(chǎng)參加群眾大會(huì),當(dāng)眾痛斥當(dāng)局“黨不擋,政不正,法不罰”。遵義當(dāng)局對(duì)其無奈,反欲利用其在文化教育界的影響,拉其加入國(guó)民黨。國(guó)民黨省黨部派原頗為其器重的學(xué)生當(dāng)說客,朱穆伯說:“我不是沒同你們說過,君子不黨,鳥獸不可同群。你請(qǐng)我入國(guó)民黨,豈不是同我開玩笑!”說客饒舌加勸,朱穆伯罵道:“你小子侮辱我,再不滾蛋,我要用腳踹你了!”
1935年1月,紅軍長(zhǎng)征進(jìn)駐遵義。據(jù)張震將軍回憶,1月9日,毛澤民與徐老(徐特立)一道“到遵義知名進(jìn)步人士劉伯莊、朱穆伯、余選華等家做統(tǒng)戰(zhàn)工作。由于他們和紅軍指戰(zhàn)員深入宣傳黨的政策,遵義城鄉(xiāng)出現(xiàn)一片物價(jià)穩(wěn)定、買賣公平、市場(chǎng)繁榮的景象”。
國(guó)民黨蔣介石的中央嫡系部隊(duì)于1935年入貴陽(yáng)時(shí),朱穆伯已回到遵義。一般中學(xué)的校長(zhǎng)怕他罵人,不聘他任教,朱穆伯因一時(shí)生活困難,只得把部分藏書廉價(jià)出賣,換幾個(gè)錢維持生活。其實(shí),當(dāng)時(shí)中學(xué)里的高年級(jí)學(xué)生還是很希望他去講課的,也希望其學(xué)生余正邦去講課。1936年,朱、余二人均在遵義師范任教。11月間,國(guó)民黨逮捕了幾個(gè)地下黨員和一些教師、學(xué)生,朱穆伯不顧一切,勇敢地奔走于各界人民之間。在一次集會(huì)上,他慷慨陳詞,要求釋放所有被捕青年。
抗日戰(zhàn)爭(zhēng)開始后第二年,遵義地下黨聯(lián)合群眾開辦“快讀書店”。書店從延安、重慶和桂林購(gòu)進(jìn)《資本論》《聯(lián)共(布)黨史簡(jiǎn)明教程》《新華日?qǐng)?bào)》和《解放》《群眾》等書刊。朱穆伯都一一讀過,尤其是讀了毛澤東的《論新階段》《論持久戰(zhàn)》等小冊(cè)子,投井下石,思想上發(fā)生了變化,曾一度想去延安學(xué)習(xí)。1938年,他向地下黨負(fù)責(zé)人楊天源、謝樹中懇切地陳述了對(duì)舊中國(guó)的認(rèn)識(shí)和對(duì)共產(chǎn)黨、八路軍的希望,要求加入中國(guó)共產(chǎn)黨。經(jīng)過貴州省工委負(fù)責(zé)人之一的鄧止戈批準(zhǔn),一個(gè)狂放不羈的學(xué)人,由此走進(jìn)了無產(chǎn)階級(jí)先鋒隊(duì)的組織行列。朱到貴陽(yáng)將此事告知田君亮先生,田問:“今后還要不要罵人?”朱回答說:“照常罵,一旦不罵那些家伙了,會(huì)引起國(guó)民黨的懷疑。”據(jù)楊天源說:“組織上認(rèn)為朱穆伯的狂士、名士風(fēng)度,不必改變,要這樣,才能繼續(xù)和上層人物接觸,也不為人注意。”
教書育人
國(guó)立浙江大學(xué)由杭州遷江西泰和,又遷廣西宜山,1939年,再遷到遵義和湄潭。竺可楨校長(zhǎng)和史地系主任張其昀等在遵義尋找校址,約請(qǐng)朱穆伯協(xié)助。浙大文學(xué)院長(zhǎng)梅光迪是北大老教授,其他教授如陳劍修等也是“北大人”,他們均推薦朱穆伯到浙大任教。先是去湄潭縣永興鎮(zhèn)浙大先修班,后又轉(zhuǎn)回遵義任浙大圖書館館長(zhǎng)。
他在永興鎮(zhèn)時(shí),附近有放敞豬的,有一位不熟悉農(nóng)村情況的人,說這是原始社會(huì)人畜共居的生活方式。朱認(rèn)為這種說法有傷群眾的感情,批評(píng)了這位朋友歷史社會(huì)知識(shí)太差。他說,清乾隆下江南時(shí),有“夕陽(yáng)芳草照游豬”的詩(shī)句。這種“游豬”就是貴州人說的放敞豬。他還幽默地說:“這只游豬游到這鄉(xiāng)下來了。”說得在座的人哄堂大笑。從此,這位朋友再也不亂開“黃腔”了。
1940年夏天的一個(gè)晚上,皓月當(dāng)空,朱穆伯和一群青年在城外散步,其中有一個(gè)是從西安回來的地下黨叛徒,表面上偽裝革命。當(dāng)大家走到一條新辟公路上時(shí),這叛徒見到一副挖出的棺材,猛叫一聲,嚇得倒退幾步。朱冷笑著說:“青年人要敢于面對(duì)血淋淋的現(xiàn)實(shí),怎么看到一副棺材就嚇成這樣?”這個(gè)叛徒知道是諷刺自己,從此懷恨在心,暗暗中傷“朱穆伯有問題”。1942年冬天,國(guó)民黨中統(tǒng)特務(wù)強(qiáng)迫一學(xué)生到朱穆伯作客的人家去,請(qǐng)朱出去講句“要緊話”,妄圖加害于他。但朱已提高警惕,大聲地說:“講什么話,就在這里講!”這個(gè)學(xué)生被吼走了。第二天,朱找到遵義專員高文伯,這位專員也是“北大人”,朱揭穿昨夜的陰謀,高表示“恐怕是出于誤會(huì)”。就這樣敷衍了事。憑借他的聲望和地位,而遵義地下黨又是搞的單線聯(lián)系,國(guó)民黨特務(wù)機(jī)關(guān)也就無可奈何了。
朱穆伯喜歡讀龔自珍的一首雜詩(shī):“陶潛詩(shī)寫說荊軻,想見停云發(fā)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俠骨恐無多。”特別是最后兩句,每當(dāng)有所感觸時(shí),他就擊節(jié)吟誦起來。他常說,教書多年的人,見到成千上萬(wàn)的學(xué)生從青年成長(zhǎng)到走向社會(huì)作事,從他們的神態(tài)氣色,往往可以看出一人的成敗得失和誠(chéng)樸、聰明或奸詐。他還說,汪精衛(wèi)、陳公博之流,都是聰明而有才學(xué)的人,可是偏偏成了民族敗類,跑到南京當(dāng)漢奸去。
朱穆伯一天酒后登上回龍寺,賦詩(shī)一首,其內(nèi)容主要是為那位“北大人”、當(dāng)漢奸的陳公博而寫的。詩(shī)云: “雀鼠方急稻粱謀,婺女空懷漆室憂。漫道楚弓還楚得,聊憑春酒遣春愁。幾度登樓長(zhǎng)佇望,寒云落日枕江流。”
朱穆伯在浙大圖書館任職期間,還兼任遵義縣中高中部的國(guó)文和英文課。他在講《離騷》時(shí),對(duì)學(xué)生說,你們中間有的人是讀書鍍金的,高中畢業(yè)回鄉(xiāng),就有資格回到鄉(xiāng)鎮(zhèn)上當(dāng)個(gè)小官了。如果你們持這樣的思想和愿望,是不可能理解《離騷》的精義的,更不能理解屈原愛國(guó)的高貴品質(zhì)。他的這番話少部分學(xué)生聽起來刺耳,但多數(shù)純潔進(jìn)的青年卻受到深刻的教育。
朱穆伯還對(duì)那些在純文藝上用功的青年們說,你們要聽我講課,那就要把知識(shí)面放寬,把精神境界擴(kuò)大,單純從文藝作品中去學(xué)文學(xué),終究是根底淺薄,沒有多大出息。不要單純讀中國(guó)書,還應(yīng)當(dāng)讀外國(guó)哲學(xué)家的著作和邏輯學(xué)。
朱穆伯師承章太炎、黃侃,深知基礎(chǔ)教育的重要,常教學(xué)生要高處著想,低處著手,循序漸進(jìn),要精讀名家名著,由博而約;寫作詩(shī)文,要有書卷氣,脫盡市井俗氣,書卷氣猶如人的浩然氣,浩氣不存,正氣不中;亦重品德教育,常說:“文人最重品德。”沒有品德的人,就沒有高尚的靈魂,也就寫不出好的文章。
1944年冬天,日本侵略軍打進(jìn)黔南,國(guó)民黨在貴陽(yáng)的黨、政、軍大員都主張一火燒毀這座城市。在貴陽(yáng)的大學(xué)都紛紛外遷,貴州大學(xué)潘家洵教授到了遵義,以“北大人”關(guān)系邀請(qǐng)朱任貴州大學(xué)教授,朱欣然應(yīng)邀。在貴大講《聲韻學(xué)》時(shí),是以錢玄同在北大的講義為底本,
參照諸家見解,編出《聲韻學(xué)十講》,這是朱穆伯一生中專心致志從事著作的開始。以他的博聞強(qiáng)記,學(xué)有所宗,正是他開花結(jié)果的黃金時(shí)代,不幸天不假年,溘然長(zhǎng)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