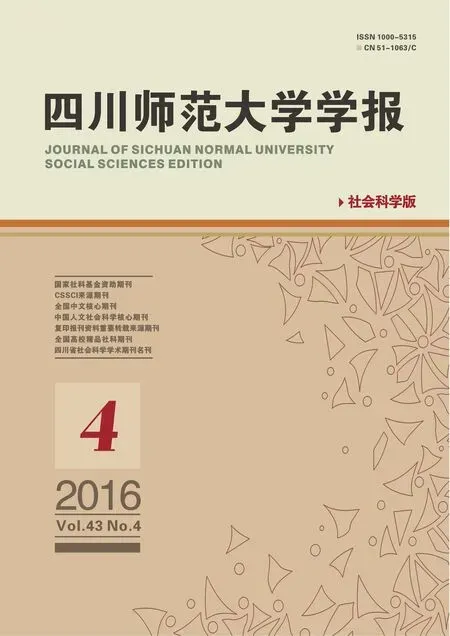救國與娛樂:抗戰(zhàn)時(shí)期成都戲曲行業(yè)面臨的輿論壓力及其應(yīng)對
車 人 杰
(四川大學(xué) 歷史文化學(xué)院,成都 610064)
?
救國與娛樂:抗戰(zhàn)時(shí)期成都戲曲行業(yè)面臨的輿論壓力及其應(yīng)對
車人杰
(四川大學(xué) 歷史文化學(xué)院,成都 610064)
摘要:抗戰(zhàn)爆發(fā)后,戲曲作為成都大眾主要娛樂方式,面臨著地方報(bào)紙以“救國”為名義的強(qiáng)烈批評,戲院被建構(gòu)成一種與“救國”話語相對立的形象。在“救國”話語的壓力下,成都的戲曲行業(yè)一方面以演出“抗敵”戲曲來遮蔽其“娛樂”性質(zhì),另一方面則以參與募捐來化解“救國”與“娛樂”的對立。然而,戲曲行業(yè)的相關(guān)努力,無法扭轉(zhuǎn)大眾娛樂在社會輿論中的不利處境。以“救國”的名義,大眾娛樂被改變了,但這種改變終究有一定限度。因?yàn)閭鹘y(tǒng)戲曲為大眾提供娛樂休閑的基本作用一旦消失,傳統(tǒng)戲曲的生存必將面臨危機(jī)。
關(guān)鍵詞:抗戰(zhàn)時(shí)期;戲曲行業(yè);成都;戲院;娛樂;救國;輿論壓力
近年來,在“新文化史”、“微觀史”等研究取向的影響下,史學(xué)界對中國傳統(tǒng)戲曲在近代的發(fā)展演變已有較為深入的探討①,其中政治在戲曲演出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頗受學(xué)者關(guān)注。既有研究表明,抗日戰(zhàn)爭時(shí)期是政治介入戲曲演出活動的“黃金時(shí)期”。在這一時(shí)期,“政治開始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介入到民間文藝中”,“戲曲的娛樂功能的主導(dǎo)地位被政治教化功能所取代”[1]105;國家“利用民族危機(jī)和高舉愛國主義的旗幟”,最終在相當(dāng)程度上“控制了大眾娛樂”[2]145-146。相關(guān)研究無疑為理解戲曲與近代政治、社會的關(guān)系提供了新的視角,豐富了大眾文化史的研究實(shí)踐。不過,抗日戰(zhàn)爭時(shí)期何以成為政治介入戲曲演出活動的“黃金時(shí)期”,仍值得進(jìn)一步探討。當(dāng)我們分析政治對戲曲的介入時(shí),除了關(guān)注介入的主體(如政府、政黨等)、介入的具體行動(如具體措施、規(guī)章條文等)外,政治權(quán)威(authority)的樹立也不應(yīng)忽視,具體表現(xiàn)為知識界與輿論界對政府干預(yù)戲曲演出的“鼓噪”與支持以及戲曲行業(yè)主動或被動的接受與“配合”。相較而言,既有研究對于政府如何加強(qiáng)控制戲曲演出論之甚詳,而對政治權(quán)威在大眾娛樂中的樹立及其影響關(guān)注相對有限。本文試圖從抗戰(zhàn)時(shí)期成都地方報(bào)紙對本地戲曲娛樂的批評入手,探討“救國”作為政治權(quán)威如何在大眾娛樂中得以確立。我們可以看到,戲曲演出并非天然就是“抗日宣傳”的有效工具,而一定程度上是在外部壓力下戲曲演出者趨利避害的自主選擇。然而,觀眾看戲的首要目的仍在于娛樂,以戲曲作為“教化”和“宣傳”的工具,盡管有其時(shí)代的特殊性,然其完全忽視戲曲的娛樂功能,終將影響到戲曲本身的生存空間。
一戰(zhàn)時(shí)社會輿論對戲曲行業(yè)的批評
20世紀(jì)的前30年是成都傳統(tǒng)戲曲演出事業(yè)發(fā)展的“黃金時(shí)期”。1906年,第一家近代戲院“可園”在成都創(chuàng)辦,標(biāo)志著成都的戲曲行業(yè)開始走向市場化;1912年,近代川劇界最有影響力的戲班“三慶會”在成都建立,則是近代川劇發(fā)展史上的里程碑[3]132[4]143。此后經(jīng)過20多年的發(fā)展,到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前夕,成都市內(nèi)已形成了一個(gè)較為繁榮穩(wěn)定的戲曲演出市場,“聽?wèi)颉备钱?dāng)時(shí)成都市民重要的娛樂休閑方式。然而,抗日戰(zhàn)爭的爆發(fā),根本改變了成都戲曲所處的外部環(huán)境。隨著抗日救亡成為國家與社會的基本共識,“救國”被樹立為至高無上的政治權(quán)威,戲曲演出的娛樂屬性在國家和社會層面都面臨巨大的外部壓力。由于戲曲是一種面向大眾的藝術(shù)形式,因此對于戰(zhàn)時(shí)戲曲業(yè)而言,來自社會輿論的壓力可能并不亞于來自政府方面的高壓與管控。
戰(zhàn)時(shí)成都戲曲業(yè)所面臨的社會輿論壓力主要來自新聞媒體。作為當(dāng)時(shí)四川省內(nèi)發(fā)行量最大的報(bào)紙,《新新新聞》的評論頗具代表性。一方面,《新新新聞》強(qiáng)烈的地方化、平民化和商業(yè)化特征,使得其十分關(guān)注成都的戲院與戲曲演出;另一方面,從報(bào)社人員的教育背景看,《新新新聞》的主筆皆川籍人士,全部具有專門學(xué)校以上的文憑,有的人還具有留學(xué)經(jīng)歷,這又為該報(bào)有關(guān)戲曲娛樂的評述染上了明顯的精英色彩②。在整個(gè)抗戰(zhàn)期間,《新新新聞》針對成都戲曲娛樂的批評可以說是“一以貫之”,但在戰(zhàn)爭的不同階段,其批評又具有各自不同的特點(diǎn)。由此,《新新新聞》對成都戲曲娛樂的評論,可以作為觀察知識分子對于大眾娛樂態(tài)度的一個(gè)窗口。
1937年7月25日,即“蘆溝橋事變”爆發(fā)后的第18天,《新新新聞》首次出現(xiàn)批評本地戲曲娛樂的聲音。其刊載的漫畫《馬路上的看客》為:馬路邊貼著“本園重金禮聘京滬超等馳名文武花旦今夜登臺玉堂春”的廣告下“人頭攢動”,而“抗敵宣言”前卻只有“看客”一人[5]。漫畫無疑是想用對比和諷刺的手法告訴人們,“玉堂春”之類的戲曲演出對成都人的吸引力超過了“抗敵宣言”這種“現(xiàn)象”是不對的,其潛臺詞則是“救國”與“娛樂”不能兼容。
“救國”與“娛樂”為什么不能兼容呢?批評者們的解釋是,“娛樂”意味著輕松,與“救國”的氛圍不符。《新新新聞》“七嘴八舌”欄目的一位評論者聲稱:“靡靡之音”本身不會亡國,而它卻是亡國的“征象”,“我們卻不該有這種征象,在這種非常時(shí)期,我們要來的悲壯,激昂,亢奮一點(diǎn),與普遍的抗戰(zhàn)情緒取得聯(lián)系”[6]。因此,隨著淞滬會戰(zhàn)爆發(fā),全面對日抗戰(zhàn)的形勢逐漸明晰,戲院等體現(xiàn)出的“娛樂”景象和氛圍,與“悲壯”、“激昂”、“亢奮”的“抗戰(zhàn)情緒”之間的“矛盾”日漸尖銳起來。1937年8月29日,《新新新聞》再度刊載漫畫:“某某大戲院”門口車水馬龍,顧客如織。漫畫作者還特意給漫畫取了一個(gè)諷刺的標(biāo)題“共赴國難”,實(shí)則批評戲院生意的繁盛與抗戰(zhàn)主題不相容。
一開始,批評者們的“矛頭”指向了去戲院看戲的人。在他們看來,這些抗戰(zhàn)時(shí)期還看戲的人們“神經(jīng)”顯然不夠“銳敏”。1937年9月,抗日話劇《保衛(wèi)蘆溝橋》在成都上演,一時(shí)反響巨大,然而《新新新聞》的一位評論家卻借題發(fā)揮,批評平日喜愛看戲的民眾道:那些看了《保衛(wèi)蘆溝橋》后哭的人是“神經(jīng)衰弱”,因?yàn)樗麄冇^看《蘇三起解》也“一樣會哭”,可“長城,吳淞正演看一齣真刀真槍的戲,場面比這更偉大,情節(jié)更逼真,然而卻沒有人哭過”;這些人“哭過之后”,“出了戲場又哭(笑)嘻嘻,而且仍然□看公子多情,小姐贈巾的戲,去看窮漢淘金,騎士救美的戲”[7]。地方文人王怡庵則于抗戰(zhàn)爆發(fā)后的第一個(gè)“九一八”到來之際,撰文批判成都人已經(jīng)快要淡忘“九一八”是什么日子了,因?yàn)椤皧蕵穲霾皇且廊挥腥藵M之患,包車汽車停滿了各娛樂場門外么”;王怡庵認(rèn)為,此類現(xiàn)象表明,作為“重要后方的都市”的成都,“尋不出全面抗戰(zhàn)的精神來,找不到前方已經(jīng)血戰(zhàn)很久的后防應(yīng)該如何緊張的態(tài)度來”[8]。
盡管遭到批評的是看戲的人,但戲曲行業(yè)難免“池魚之殃”。一封“讀者來信”呼吁:“奢華”的“太太小姐們”把她們“穿華服,吃美食,搓牌雀,看戲劇的錢,拿來出點(diǎn)到前方去,慰勞勇猛的將士,救濟(jì)不幸的同胞”[9]。另一位“讀者”則干脆呼吁:對娛樂場加“國難捐”,理由是“十二個(gè)娛樂場,日夜裝滿”,“娛樂場這么多人,何不抽點(diǎn)娛樂捐”,“他們及時(shí)行樂的,如九牛拔一毛,少吸一根紙煙就得啦”,而且“想來他們也樂為,并且也成全了他們娛樂不忘救國的志愿”[10]。“看戲”作為一種娛樂消費(fèi),在抗戰(zhàn)時(shí)期不僅不正當(dāng),甚至還“奢侈”,戲院則是“不愛國”的“有錢人”們愛去的“奢侈”場所;既然勸說“奢侈”的人們不去看戲效果不大,那么社會輿論的壓力轉(zhuǎn)向制造“奢侈”的戲曲行業(yè)似乎“順理成章”。
于是,進(jìn)入1938年后,批評者的矛頭由看戲的人轉(zhuǎn)向了戲曲行業(yè),報(bào)紙上針對戲曲行業(yè)的批評與“建議”可謂“五花八門”。有人主張將“劇團(tuán)”趕到農(nóng)村去,因?yàn)樗鼈兇蛑皭蹏麄鳌钡恼信疲瑢?shí)際上卻“禍國害民”,為“都市所有的大人先生,豪商富賈,揮霍浪費(fèi)”,“純系為了交際娛樂混目,終日到戲院去愛國”[11]。有人主張對戲曲行業(yè)抽收捐稅:“一切荒淫的事,均征收特別捐”[12]。有人對戲曲行業(yè)的“繁榮”耿耿于懷,因?yàn)槌啥紤蛟簲?shù)量之多,只會證明本地“笙歌管弦,朝秦暮楚,不似戰(zhàn)時(shí)狀態(tài),直如升平氣象”[13]。“國恥日”的到來也會勾起對戲院的不滿,因?yàn)閼蛟涸凇皣鴲u日”不僅不停演,還減價(jià)招徠觀眾,以至于把參加“火炬游行”的人都“勾引”過去了[14]。1938年10月,廣州、武漢相繼淪陷,戰(zhàn)局的緊張使人們更加“痛心疾首”:“戰(zhàn)爭愈進(jìn)步,奢侈娛樂也隨之而進(jìn)步,不管大武漢怎樣的危急,它們困在戲院的,仍然困在戲院”[15];“昨天廣州失陷的消息傳來,但我看幾個(gè)娛樂場所完了的時(shí)候,人像蛆一樣擁出……啊,你看,將來縱然武漢放棄,娛樂場一定還是滿座……一切亡國的現(xiàn)象一定還是照常”[16]。面對“木包一樣毫無國家民族觀念”的人們,“依然天天過花天酒地的生活,依然天天看戲看電影”[17],批評者們似乎已“無計(jì)可施”,干脆直接向政府呼吁:“我真不明白,我們的成都當(dāng)局,怎么在這樣緊急的關(guān)頭,還不取締這些消滅抗敵情緒的事業(yè)一樣?”他們甚至要求“一律禁止”無關(guān)抗戰(zhàn)的舊劇和影片,將戲院等“一律收歸公有”[18]。
對于戲曲行業(yè)而言,如果之前的批評只是無關(guān)緊要的“七嘴八舌”,到1939年,隨著成都面臨日本戰(zhàn)機(jī)轟炸的威脅,防空疏散成為了社會熱點(diǎn)話題后,這些“七嘴八舌”突然變得“有力”起來。1939年2月12日,《新新新聞》刊載漫畫《疏散人口》,在漫畫中,四位“衣著時(shí)尚”的男女(從右到左)分別說:“我要去看悅來!”“我喜歡聽京戲!”“我去聽揚(yáng)琴!”“聽說智育今晚換片。”③[19]以“疏散人口”為題,顯然有影射戲院阻礙防空疏散的意思。
隨后而來的疏散使得“戲園、影院生意一落千丈”[20]21,但這并未使其逃脫被批評。因?yàn)閼蛟菏恰拔斩际杏虚e階級人們的有效場所”,只要把它停業(yè),“享樂的紅男綠女自然會無聊而離開城市生活”[21]。1939年5月26日,《新新新聞》的“小鐵椎”直接建議當(dāng)局“停止娛樂場所營業(yè)”,因?yàn)椤霸S久不聞空襲警報(bào),人心似乎又有些痺麻了,警備疏散,趦趄不前”,已經(jīng)疏散的人又回到了城里面,“而娛樂場所的客座,又密不通風(fēng)了”,許多人“眷戀城市,不肯疏散”,“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所以政府應(yīng)立即責(zé)令娛樂場所停業(yè),“使那些醉生夢死者無所留戀亦無可留戀”[22]。省主席王纘緒最終“順應(yīng)”輿論的呼吁,將戲院一律停業(yè),“以杜荒嬉而策安全”④。為此,成都戲院停業(yè)近兩個(gè)月。同樣的情形又出現(xiàn)在1940年的夏天,在成都又面臨防空疏散問題時(shí),有人再次指責(zé)戲院,稱:“迄今為什么尚有一部分人不去疏散,我覺得仍然是娛樂場所的吸引力太大了”,因此,“應(yīng)當(dāng)照過去的辦法,從取締娛樂場所實(shí)行起來”[23]。戲院于是再度“自動疏散”[24]。
1942年以后,日機(jī)停止了對成都的大規(guī)模空襲,防空疏散問題得以緩解。抗日戰(zhàn)爭長期處于相持狀態(tài),戰(zhàn)爭對于普通民眾的生活而言已屬常態(tài)。與此相應(yīng)的是,抗戰(zhàn)前期針對戲曲行業(yè)的許多批評逐漸淪為“老生常談”,最終在報(bào)紙上“銷聲匿跡”。戲院的門票價(jià)格成為了抗戰(zhàn)中后期備受批評者們關(guān)注的問題。早在1939—1940年戲院在防空疏散后恢復(fù)營業(yè)時(shí),報(bào)紙便希望戲院減少票價(jià)[25][26]。然而,抗戰(zhàn)中后期,隨著成都物價(jià)的不斷上漲⑤,戲院不斷提升票價(jià),于是報(bào)紙便代平民“發(fā)言”,批評戲院漲價(jià)是發(fā)“國難財(cái)”。
1942年9月,影劇業(yè)⑥大幅提高票價(jià),“市民望政府取締”[27]。10月,署名“尖兵”的作者評論娛樂場的票價(jià)說:成都是“后方的重鎮(zhèn)”,“然而許多人只是昏昏夢夢□□,每一娛樂場所,場場滿座,有些未開場就‘免戰(zhàn)高懸’,人滿為患”,因此,“娛樂場的老板,卻呵呵大笑,隨時(shí)提高票價(jià),叫戲迷影迷挨大竹杠。戲院座票更是因?yàn)閼蛎該頂D,不僅發(fā)生黑市,而且黑市之價(jià)極為驚人。一張數(shù)元的座票,暗盤要賣到四五十元,否則戲迷便哭天無路,戲癮難熬”,人們甚至為求得進(jìn)入娛樂場而常常大打出手,于是尖兵提醒當(dāng)局:“為了疏散,為了使人們不要荒淫,本市是否需要這樣多的娛樂場?是否該請他們疏散下鄉(xiāng)?”[28]戲票不僅與當(dāng)局較為忌諱的“黑市”發(fā)生了聯(lián)系,還能釀成“治安問題”,實(shí)在是戲院的一大“罪狀”。一個(gè)月后,他又批評說:“一般物價(jià)都在下跌當(dāng)中,而有些東西卻偏要漲價(jià),事情之怪,無以復(fù)加。”“戲園電影院更因?yàn)槎祆F季,影迷戲迷痰迷增太多,尤其無聲無臭一再漲價(jià)——但這與窮人無關(guān)。”[29]
1943年11月中旬,影劇業(yè)聯(lián)合在成都各報(bào)發(fā)出啟事,說明其票價(jià)高漲的原因⑦。有人作文反駁稱:“電影戲劇之能協(xié)助抗建,乃在普通觀眾,深入民間,以期文字宣傳之不逮,若以純粹商品化,圖謀厚利,則全失其功用與價(jià)值”,現(xiàn)在“一票輒以數(shù)十元,即中產(chǎn)階級亦不勝其苦,至于公教人員,文化人士,則望洋興嘆歟”,至于影戲院方面所“辯解”的“生意不好”,這位批評者卻認(rèn)為那是其自身的問題所致;他指出,全國的影戲院都面臨相同境遇,但成都三十八到四十元的票價(jià)已達(dá)全國最高,因此影戲院方面應(yīng)該“好好反省”自己,而政府則應(yīng)出手限價(jià)[30]。是文發(fā)表后,有人在報(bào)紙上刊文“響應(yīng)”,要求限制票價(jià)“不能超過十八元”,否則“未免有失政府威信”,定價(jià)之后,“應(yīng)強(qiáng)迫實(shí)行,敢有違者,照章處罰,或令其停業(yè)”[31]。影劇業(yè)的漲價(jià)與限價(jià)問題,可供我們從側(cè)面觀察抗戰(zhàn)時(shí)期大后方的經(jīng)濟(jì)與社會生活,觀察戰(zhàn)爭給人們生活帶來的影響。批評者們反對票價(jià)上漲,固然有為民生考慮的成分,但他們不愿意戲曲行業(yè)“贏利”的心態(tài),亦有以致之。實(shí)際上,這仍然屬于其自抗戰(zhàn)以來一貫的對于“娛樂”的批評態(tài)度。
二戲曲業(yè)的應(yīng)對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隨著“救國”成為最重要的政治訴求,報(bào)刊輿論建構(gòu)出的“娛樂”與“救國”相悖的話語,導(dǎo)致“娛樂”本身的正當(dāng)性喪失。“看戲”既與“救國”沖突,則戲院的生意自然會受到嚴(yán)重影響;諸如“奢靡”、“妨礙疏散”乃至“發(fā)國難財(cái)”之類的“罪名”接踵而至,甚而可能招致政府的打壓。對此,戲曲行業(yè)當(dāng)然不會“等閑視之”⑧。不過,從另一個(gè)角度來說,盡管在戰(zhàn)時(shí)社會輿論中的處境不利,但這一時(shí)期的戲曲未必沒有機(jī)遇。抗日救亡運(yùn)動既然是“全民參與”的事業(yè),則“救國”的話語必然進(jìn)入普通大眾的娛樂口味中。換言之,帶有“救國”色彩的戲曲,也是大眾喜聞樂見的。因此,采取適當(dāng)?shù)男袆訁⑴c抗日救亡運(yùn)動,既可抒發(fā)愛國熱忱,也能用來改善在輿論中的不利處境,還能促進(jìn)自身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對于戲曲行業(yè)來說,應(yīng)當(dāng)是一舉多得的好事。
對于戲曲業(yè)來說,參與抗日救亡,最為切合自身實(shí)際的方式仍然是演戲。戲曲演出的重要功能是娛樂,然而自清末起人們就已經(jīng)意識到,戲曲演出可以成為一種“社會教育”,因?yàn)椤跋碌壬鐣荒茏x書識字者,全藉觀劇以印證歷史教育于腦筋”,故“欲知下等社會為何等樣人,試先問演者為何等樣戲”[32]。即使到了抗戰(zhàn)時(shí)期,戲曲依然“負(fù)有導(dǎo)揚(yáng)國家文化和啟迪民族意識的偉大使命”[33]1,3。演戲是“社會教育”的觀念,無疑是當(dāng)時(shí)官方、知識界及戲曲界的共識。教育部轉(zhuǎn)發(fā)各地的一份文件指出:“查戲劇一道,可以褒貶善惡,移風(fēng)易俗,不獨(dú)為娛樂之一,在社教工作中,實(shí)居重要地位。”⑨“川劇大王”張德成也說:“戲劇對于國家民族政治風(fēng)化社會人心至為重大。”[34]11
問題的關(guān)鍵在于,抗戰(zhàn)時(shí)期應(yīng)演出什么樣的戲曲?其實(shí),抗戰(zhàn)前后在成都戲院里表演的許多“傳統(tǒng)”戲目,本身已是清末戲曲改良運(yùn)動中重新編寫或改寫的“改良”戲。這些劇本雖然以古代歷史故事為主題,但戲中多灌輸了“正義”、“愛國”、“忠誠”的觀念[35]367[36]251。但是,這些“改良戲”的題材和教育功能,在戲曲行業(yè)的批評者看來,顯然已無法應(yīng)付抗戰(zhàn)的需要了,因?yàn)檫@些戲曲“是封建社會的產(chǎn)物,表現(xiàn)封建社會的各種各樣的思想”,“貫穿了大部分舊型戲劇的宿命論的觀念、奴隸思想、男尊女卑,舊型戲劇所表現(xiàn)的民眾是與國家與民族不發(fā)生任何關(guān)系的”[37]10,30-32。鑒此,他們提出“現(xiàn)在別來什么風(fēng)花雪月,神仙鬼怪的戲文,多演一點(diǎn)民族抗戰(zhàn)的戲”的主張[6]。
原有的戲目既然難以適應(yīng)抗戰(zhàn)宣傳的需要,“時(shí)裝戲”的出現(xiàn)似乎順理成章。所謂“時(shí)裝戲”,即在清末出現(xiàn)的表現(xiàn)現(xiàn)實(shí)生活題材的新編戲曲,因其穿戴“時(shí)裝”而得名。“時(shí)裝戲”的編劇方法,“大致和傳統(tǒng)戲差不多,上場引子下場詩,唱作念舞都有,一般不用布景,演員表演也多用傳統(tǒng)手法”[38]130。川劇的“時(shí)裝戲”出現(xiàn)于辛亥革命時(shí)期,30年代又涌現(xiàn)了以寫“時(shí)裝戲”劇本見長的劉懷緒,其創(chuàng)作之“時(shí)裝戲”劇本中,與抗日話題相關(guān)的劇本即有《槍斃田玉成》、《蘆溝橋姐妹花》、《槍斃殷汝耕》、《漢奸之妹》和《抗日英雄王銘章》等,此外尚有《南口之戰(zhàn)》、《王上將殉職》等劇本[35]529-532。



有時(shí),戲曲藝人們在一些“新編小戲”、“連臺本戲”與“傳統(tǒng)折戲”中加唱“新段子”,反而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抗敵效果”。如由古代故事改編的《新打神》一戲,故事情節(jié)正當(dāng)高潮時(shí),演員突然加唱一句“猛想起前方正吃緊,要打就該去打日本兵”[40]13。1939—1942年,在“三慶會”會長肖楷成領(lǐng)銜下,連臺戲《濟(jì)公活佛》在悅來戲院演出,“場場滿座,久演不衰”;某次戲院突然停電,肖楷成“靈機(jī)一動”,突然加了段“抗日”臺詞,引起喝彩,于是此后都在《濟(jì)公活佛》的“適當(dāng)?shù)胤健奔由弦欢芜@樣的臺詞,“收到抗日救亡、宣傳和藝術(shù)鑒賞完美的融合效果”[44]191。其實(shí),這種演出方式仍屬于傳統(tǒng)戲曲演出中“抓哏”的范疇,其之所以成功,在于契合了戲臺表演與觀眾互動的游戲與娛樂性質(zhì)[45]5。不過,劉成基將《濟(jì)公活佛》的這種做法視為川劇發(fā)展中的怪現(xiàn)象[38]132。我們不知道他批評的出發(fā)點(diǎn)是什么,或許是批評其仍然是舊的題材,“固步自封”,或許是這種加唱“新”段子的做法“不倫不類”。
應(yīng)該說,通過演出“民族抗戰(zhàn)”戲曲,戲曲行業(yè)在“抗日宣傳”上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也在為自己營造“抗日”、“社會教育”的社會形象,但顯然收效不佳。一方面,輿論的反映表明,戲曲的批評者們似乎并未領(lǐng)情;而另一方面,“抗戰(zhàn)戲曲”看來也無法在戲曲舞臺上站穩(wěn)腳跟。到1941年初,成都的戲曲舞臺已退回了原樣,戲院“排演的戲目,也不過是些古代的忠孝節(jié)義故事而已”[46]。在新的時(shí)代背景下,傳統(tǒng)戲曲的“社會教育”功能已無法滿足趨新知識分子們的要求,相對于“社會教育”的場所,戲院在大多數(shù)時(shí)間里被視為“娛樂場所”,批評者們難以容忍“娛樂場所”在抗戰(zhàn)時(shí)期的繁榮,因此不斷批評。
相較于上演“民族抗戰(zhàn)”的戲劇,參與抗戰(zhàn)相對容易的方式是參與各式各樣的募捐。募捐當(dāng)然可能是出于愛國熱忱,但也可藉此樹立其參與抗戰(zhàn)的形象,規(guī)避諸如“奢侈”、“不愛國”等負(fù)面評價(jià)。成都募捐支援前線的活動始于蘆溝橋事變后不久,隨著戰(zhàn)事日益激烈,抗敵氛圍開始濃重,戲院也參與到捐款的行列中。
舉行公演是戲曲行業(yè)募捐的重要方式。由于戲劇表演對人們的吸引力,往往能得大量門票收入,而戲院則將所得門票收入拿出捐獻(xiàn)。1937年10月4日,新聞報(bào)道春熙大舞臺“募捐救難民”,稱其“鑒于滬戰(zhàn)爆發(fā),受災(zāi)同胞急待救濟(jì),本娛樂不忘救國之旨,遵影劇業(yè)公會之發(fā)起各院園募捐救濟(jì)災(zāi)區(qū)同胞”,“以一日所得全數(shù)捐助災(zāi)區(qū)同胞”[47]。10月6日,成都各戲院遂舉行“演劇捐”,“貢獻(xiàn)一日所得,以盡國民一份子之職責(zé)”,戲院一日的收入,包括“月餅費(fèi)”被一并捐給前線[48]。
“游藝大會”也是一種重要的募捐形式。所謂“游藝”,即不局限于一種藝術(shù)形式,往往傳統(tǒng)戲曲、話劇乃至音樂多種形式同臺演出。如1938年11月13日,新又新大戲院舉行的游藝大會,成都京、川、話劇的名角王泊生、賈培之和白楊等“義務(wù)助演”,還邀請“外籍音樂名家演奏”[49]。戲院往往充當(dāng)“游藝大會”的演出場所,戲院里的戲班則參與其中[50]。由于匯聚諸多藝術(shù)形式,而且名家薈萃,因此,“游藝大會”對于不同藝術(shù)口味的觀眾頗具有吸引力。大會的舉辦者和戲院為吸引觀眾,在廣告上也頗費(fèi)心思。如新又新大舞臺舉行游藝大會的廣告聲稱:“內(nèi)容精彩,意義深厚,愛國兼可看戲,買票等于捐衣,機(jī)會難得,愛國同胞幸勿交臂失之。”[49]這里將“愛國”與娛樂巧妙地聯(lián)系在了一起,以收到良好的宣傳效果。而“熱血劇團(tuán)”募捐寒衣的游藝大會廣告則稱:“多買一張票,多制一件寒衣,多增一份抗戰(zhàn)力量。”[50]


盡管如此,參與募捐并未根本改變批評者們對戲曲行業(yè)的不滿情緒。盡管沒有否定戲曲行業(yè)的募捐,但這并未消減對娛樂的批評。1937年10月以后,盡管新聞相繼報(bào)道成都的各戲院演戲募捐,但同時(shí)期報(bào)紙上仍充斥著要求征收“娛樂捐”、“奢侈捐”的呼聲。人們并不認(rèn)同“愛國兼可看戲”,戲院的募捐活動不足以遮蔽其在批評者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娛樂”標(biāo)簽。正因?yàn)閼蛟菏菉蕵穲鏊治敲炊嗟挠^眾看戲,其募捐被視為理所應(yīng)當(dāng),甚至應(yīng)該成為正式的稅收。
由此不難理解,一旦戲院參與捐款不“積極”,將會陷入怎樣的輿論“風(fēng)暴”中。1939年度的“寒衣”捐款,戲院最初表現(xiàn)得不太“積極”,為此招來諸多批評。人們原本認(rèn)為,戲院積極捐款“理所應(yīng)當(dāng)”,因?yàn)椤懊嬷鹘恰蹦苡H自征寒衣,不僅“定能收到很大成績”,而且“還能表示他們并不是在‘隔江猶唱后庭花’”[53];退一步講,戲院“既無其他負(fù)擔(dān),對此項(xiàng)協(xié)助加捐之事,想不致多所拒絕”[54]。然而,“有一二影戲院堅(jiān)不接受”,輿論對此大為不滿,于是痛斥這些戲院的“老板”們“究竟是何居心”:“寒衣捐之附加在入場捐上,出錢者仍為觀眾,與劇院并不相干。”如果是怕影響營業(yè),那么這些老板們應(yīng)該對前線將士心懷感恩之心才對,因此,“若要以停業(yè)相要挾,要停便停,何必惺惺作態(tài)”,停業(yè)“不會少了一只耳朵和眼睛”,如此“做作”,只能證明其“愚昧與鄙陋”,“希望大多數(shù)劇院,股東們切莫跟著他們采取一致行動”[55]。隨后輿論對戲院施加強(qiáng)大壓力,11月5日的新聞報(bào)道要求:“正當(dāng)商人,勿予附和,否則政府盡可實(shí)施強(qiáng)迫予以制裁。”[56]有人則聲稱:自影戲院復(fù)業(yè)之后,演映的都是“明目張膽的妨礙抗戰(zhàn),消磨抗戰(zhàn)意識”的作品,現(xiàn)在居然拒絕加收寒衣捐,還“以停業(yè)相威脅”,因此“要停就停”,只有“行尸走肉的涼血動物”才希望他們復(fù)業(yè)[57]。影劇業(yè)反對增加寒衣捐,也可能是因?yàn)闀澅荆@然批評者們沒有或者不愿考慮這點(diǎn)。最后在輿論壓力下,各戲院只得“深悟大義”,“自愿接受寒衣會所定捐款征收方法,于昨(十)日起復(fù)業(yè)也”[58]。在此類“捐款”造成的“風(fēng)波”中,戲院不僅沒有改善其在輿論中的“不良形象”,而且還可能形塑一種類似于“發(fā)國難財(cái)”這種在大后方輿論中頗為負(fù)面的形象。
三“救國”與“娛樂”的平衡
臨近戰(zhàn)爭結(jié)束的1944年,成都的各戲院依然“常告客滿”[59]93。同一時(shí)期游歷成都的黃裳,也提到成都的戲院,“每天總是客滿,里邊全是茶余酒后來欣賞這鄉(xiāng)土藝術(shù)的人,裙屐連翩,情況是相當(dāng)熱烈的”;不過,黃裳本人對“鄉(xiāng)土藝術(shù)”的那份“欣賞”,在他定居重慶后卻消失了,“時(shí)時(shí)經(jīng)過劇院門口,聽見金鼓的聲音,心情激動,殊不愿再聽這離亂之音”,他甚至哀嘆:“滄海波瀾,戰(zhàn)亂未已,這種蜀音,簡直發(fā)展成為全國的聲音了。”[60]303
黃裳的“失望”以及《新新新聞》在整個(gè)戰(zhàn)爭期間持續(xù)不斷的批評聲音,似乎表明,戰(zhàn)時(shí)針對戲曲娛樂的批評并未達(dá)到批評者們所希望達(dá)到的“效果”。這些批評既沒有影響一般民眾看戲的“熱情”,也沒有撼動戲院的“繁榮”,甚至沒能讓“救國”的戲曲占據(jù)戲院的舞臺。只有在與“防空疏散”相結(jié)合時(shí),對戲曲行業(yè)的批評才一度“抑制”了娛樂。更多的情形下,報(bào)紙對戲曲行業(yè)連篇累牘的“批判”可謂“孤掌難鳴”,得不到觀眾、戲曲業(yè)及政府的“響應(yīng)”,這無疑給原本充滿熱情的批評者澆上了失望的“冷水”。
對于戲曲行業(yè)的批評者而言,批評戲曲行業(yè)的目的是為了動員民眾“救國”。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隨著民族危機(jī)日益加深,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竭盡全力動員民眾參與抗日救亡運(yùn)動。娛樂活動天然帶有的“放松”性質(zhì),既不符合知識分子們?yōu)榭谷站韧鏊鶢I造的“悲壯”氛圍,更不符合知識分子們心目中抗日救亡所應(yīng)具有的“緊迫感”,這無疑是其受到這些知識分子排斥的主要原因。對于身處成都的地方知識分子而言,成都地方的“特殊性”無疑使得其更加排斥“娛樂”。戰(zhàn)爭爆發(fā)后,原本僻處西南內(nèi)地的成都成為了“重要后方的都市”,因此,成都在“戰(zhàn)爭進(jìn)行當(dāng)中負(fù)著如何重大的責(zé)任”,本來“不待國家要求,是應(yīng)該自己明白的”[61]。然而,成都地理上遠(yuǎn)離戰(zhàn)爭前線,救亡危機(jī)本不易為本地民眾所感知。戲曲行業(yè)的“繁榮”,意味著“在這重要后方的都市中,尋不出全面抗戰(zhàn)的精神來,找不到前方已經(jīng)血戰(zhàn)很久的后防應(yīng)該如何緊張的態(tài)度來”[8]。所以,批評“沉迷”看戲的民眾,批評戲曲行業(yè)的“繁榮”,是地方知識分子希圖扭轉(zhuǎn)地方社會風(fēng)氣,從而動員民眾抗日的一種方式。
無可否認(rèn)的是,戲曲行業(yè)的批評者頗有愛國熱情,而報(bào)章中聯(lián)翩累牘的“呼吁”與“規(guī)勸”,更是把新聞媒體對社會的監(jiān)督與引導(dǎo)責(zé)任發(fā)揮到極致。然而,過于強(qiáng)烈的優(yōu)越感和使命感,最終使得批評者們事與愿違。這些人大多視抗戰(zhàn)時(shí)期還要去看戲的民眾為“木包一樣毫無國家民族觀念”的人[17],他們“不可救藥的神經(jīng)衰弱”[7],而自己顯然“神經(jīng)銳敏”。他們以自己的一套“標(biāo)準(zhǔn)”來要求一般民眾,呼喚“悲壯”、“激昂”、“亢奮”的氛圍,期待民眾也“將神經(jīng)練銳敏一點(diǎn)”,不要“天天去看戲”。至于戲院和戲班,即使出于生存需要演戲,也只能演出“民族抗戰(zhàn)”的戲。概言之,這些批評者不僅要求所有民眾一起“愛國”,同時(shí)還要按照被他們限定的方式“愛國”。
然而,知識分子們引領(lǐng)“救國”話語,規(guī)訓(xùn)民眾生活的“雄心”終究無法實(shí)現(xiàn),針對戲曲行業(yè)和看戲觀眾的批評更是難以達(dá)到預(yù)期目的。將“救國”與“娛樂”建構(gòu)為一種“此消彼長”的對立關(guān)系,注定了這些批評無法為觀眾、戲曲行業(yè)真正接受。歸根結(jié)底,娛樂作為大眾的一大精神需求,并不能因?yàn)椤熬葒倍桓救∠τ趹蛟汉蛻虬鄟碚f,戲曲演出的首要目標(biāo)是得到觀眾的認(rèn)可,投其所好。這種關(guān)系受外界社會變化和政治發(fā)展的影響較小,也不因?yàn)閼?zhàn)爭的發(fā)生、發(fā)展而發(fā)生根本的不同。盡管隨著抗戰(zhàn)話語的深入,戲曲演出中的“抗敵”因素本身也會富于吸引力。如時(shí)人的回憶中,“最受歡迎的戲”全部是與抗戰(zhàn)相關(guān)的戲,也并非完全是“無的放矢”[62]45。然而,大眾的娛樂“口味”中不可能只有“抗日”因素。對于觀眾來說,戲劇演出的意義不僅僅是被教化,更重要的還是休閑與放松。戲劇理論家劉念渠認(rèn)為:“萬萬千千的觀眾不盡是有正確判斷力的,他們不能因?yàn)樵诳箲?zhàn)期間沒有抗戰(zhàn)宣傳戲劇就不去看戲;也有人不愿意花五角錢看一次話劇,情愿在三天之前就定了座位去聽名伶的拿手好戲。”[37]33劉的本意是“告誡”話劇界人士要加緊編寫“抗戰(zhàn)宣傳戲”,但卻從另一方面說明休閑娛樂之于一般觀眾看戲的意義。其實(shí),戲曲所提供的休閑,不僅未必分散人們對抗戰(zhàn)主題的關(guān)注,反而能放松人們因戰(zhàn)爭而緊張的神經(jīng)。針對成都戲曲娛樂的大多數(shù)批評都流于情緒化,缺乏可操作的具體建議。批評者們動輒呼吁“停止娛樂”,既忽略成都戲曲行業(yè)的現(xiàn)實(shí)處境,又無視戰(zhàn)時(shí)娛樂可能具有的積極意義,更缺乏切實(shí)可行的具體辦法,實(shí)際上淪為了尷尬的道德說教,只能反映出部分精英知識分子對于大眾娛樂的偏狹態(tài)度。
不過,抗戰(zhàn)時(shí)期針對戲曲娛樂的批評,雖然未達(dá)到批評者們希望達(dá)到的效果,但并非全無作用。“川劇大王”張德成表示,川劇能吸引眾多觀眾“并非偶然”,因其曲牌眾多,能將“喜怒哀樂”“傳神入化”,同時(shí)因其“辭藻佳麗”而“雅俗共賞”;不過,“值此發(fā)動為世界和平正義而戰(zhàn)的今日,各種地方劇曲,都應(yīng)該站在自己的崗位上,負(fù)起偉大的責(zé)任,完成偉大的使命,川劇當(dāng)然不能例外”[34]11。張氏的言論像是為戲曲行業(yè)“辯解”,也可作為戲曲界人士的一種“表態(tài)”。盡管無法完全迎合批評者們的種種“要求”,但戲曲行業(yè)采取了諸如演出抗戰(zhàn)戲曲和參與募捐等實(shí)際行動加以應(yīng)對。作為抗戰(zhàn)社會動員的組成部分,針對戲曲行業(yè)的批評,推動了“救國”作為最高政治權(quán)威在大眾娛樂中的形象樹立。
對于戲曲行業(yè)而言,這些批評更重要的意義在于促使戲曲從業(yè)者進(jìn)一步思考,如何更好地處理藝術(shù)與現(xiàn)實(shí)、演出者與受眾之間的關(guān)系,從而使傳統(tǒng)藝術(shù)形式在不斷變化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下得以延續(xù)。作為一種面向大眾的藝術(shù)形式,戲曲演出與現(xiàn)實(shí)結(jié)合是戲曲藝術(shù)應(yīng)有的“題中之義”。對于戰(zhàn)時(shí)戲曲行業(yè)而言,“救國”無疑是必須予以回應(yīng)的時(shí)代命題。然而,如果單純將戲曲作為“救國”工具,忽視戲曲藝術(shù)應(yīng)為觀眾帶來的藝術(shù)享受,或者單純以“娛樂”為出發(fā)點(diǎn),無視戲曲藝術(shù)應(yīng)與時(shí)俱進(jìn)、關(guān)注現(xiàn)實(shí)的社會責(zé)任,都會造成戲曲藝術(shù)的嚴(yán)重異變。概言之,對于傳統(tǒng)戲曲而言,“救國”與“娛樂”,應(yīng)實(shí)現(xiàn)某種形式的“平衡”。
對于抗戰(zhàn)時(shí)期的一些戲劇界人士而言,選擇戲曲作為抗日宣傳的“武器”,主要是因?yàn)椤芭f劇”的觀眾與演員眾多;至于演出的戲目,則必須重新“注入新內(nèi)容”,“新內(nèi)容必須適應(yīng)抗戰(zhàn)宣傳的需要,吻合抗戰(zhàn)情勢的發(fā)展”,他們“希望做到每一地方每一劇場的每一場演出都是抗戰(zhàn)宣傳的新劇本”[37]28,29,37。然而,過于強(qiáng)烈的工具理性,使得這些“改造舊劇”的努力陷入了困境。事實(shí)證明,傳統(tǒng)戲曲中灌輸過多的“抗戰(zhàn)內(nèi)容”與“現(xiàn)代思想”,往往造成戲曲形式與內(nèi)容嚴(yán)重失調(diào),嚴(yán)重影響戲曲本身對觀眾的吸引力。1939年,成都春熙舞臺上演改編后的《血染黃州》,一向主張改造“舊劇”的劉念渠觀看后卻認(rèn)為其“主題不明確”,布景海派戲和話劇的雜糅風(fēng)格頗“不著調(diào)”,聲響效果采取話劇的形式則顯得“不倫不類”[37]52。1945年,劇作家鄭沙梅將川劇經(jīng)典曲目《紅梅》改編為話劇形式上演,結(jié)果卻引得觀眾一片“倒彩”,為此劇作家洪深撰《哀紅梅》一文反思:對于文藝作品的評價(jià),應(yīng)兼顧其創(chuàng)作“企圖”和演出“效果”[63]285。戰(zhàn)后的1946年,田禽反思抗戰(zhàn)時(shí)期的“戲劇運(yùn)動”時(shí)指出:“抗戰(zhàn)初期的創(chuàng)作,大多單純的重視了宣傳作用,而忽略了宣傳必須與藝術(shù)統(tǒng)一的真理。”[64]9一些川劇界人士則認(rèn)為,抗戰(zhàn)結(jié)束后,川劇已經(jīng)陷入了“危機(jī)”中,除卻動蕩的時(shí)局影響外,更重要的是由于在電影等新藝術(shù)形式的沖擊下,傳統(tǒng)戲曲形式本身嚴(yán)重“異化”,從而導(dǎo)致其觀眾基礎(chǔ)的喪失。劉成基在評論抗戰(zhàn)后成都戲院里的“時(shí)裝戲”時(shí)更嚴(yán)厲地指出:“它(時(shí)裝戲)既不同于早年間的時(shí)裝戲,也沒有半點(diǎn)川劇藝術(shù)在其中。它在文藝舞臺上預(yù)告人們:川劇要垮臺了!”[35]547
對于傳統(tǒng)戲曲而言,政治宣傳與教化的系統(tǒng)介入始于清末戲曲改良,興盛于抗日戰(zhàn)爭時(shí)期,并最終在共和國時(shí)期達(dá)到極致,其中得失利弊可以見仁見智。然而,如何在教化與藝術(shù)之間求得“平衡”,對于整個(gè)戲劇界而言,至今仍是一個(gè)值得探討的課題。而對于像川劇這樣具有地方性特色的戲曲形式而言,如何在順應(yīng)時(shí)代潮流的同時(shí),保留自身的藝術(shù)特色,維持并擴(kuò)大觀眾基礎(chǔ),則更是事關(guān)自身生存與發(fā)展的長遠(yuǎn)大計(jì)。
注釋:
①近十年來史學(xué)界關(guān)于戲曲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韓曉莉《戰(zhàn)爭話語下的草根文化——論抗戰(zhàn)時(shí)期山西革命根據(jù)地的民間小戲》,《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程美寶《清末粵商所建戲園與戲院管窺》,《史學(xué)月刊》2008年第6期;魏兵兵《“風(fēng)化”與“風(fēng)流”:“淫戲”與晚清上海的公共娛樂》,《史林》2010年第5期;姜進(jìn)《越劇的故事:從革命史到民族志》,《史林》2012年第1期。近年來,關(guān)于近代四川戲曲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蔣維明《移民入川與舞臺人生》,成都科技大學(xué)出版社1998年版;鄧運(yùn)佳《中國川劇通史》,四川大學(xué)出版社1993年版;馬睿《晚清到民國年間(1902—1949)政府對四川地區(qū)戲曲表演活動的介入與控制》,四川大學(xué)2007年碩士學(xué)位論文;周鼎《“世界亦舞臺”:民初成都的戲劇與文人——以《娛閑錄》(1914—1915)劇評為中心》、李賢文《川劇界對抗戰(zhàn)的反映(1937年7-12月)》,兩文均收入姜進(jìn)、李德英主編《近代中國城市與大眾文化》,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王笛《茶館、戲園與通俗教育:晚清民國時(shí)期成都的娛樂與休閑政治》,《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又收入王笛著《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社會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09年版;王笛《國家控制與社會主義娛樂的形成——1950年代前期對成都茶館中的曲藝和曲藝藝人的改造和處理》,韓鋼主編《中國當(dāng)代史研究》(一),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88-119頁。
②有關(guān)《新新新聞》的相關(guān)情況,詳見:王伊洛《〈新新新聞〉報(bào)史研究》,四川大學(xué)2006年博士學(xué)位論文。
③“悅來”即“悅來戲院”,“智育”指“智育電影院”。
④參見:《成都市政府轉(zhuǎn)四川省主席令》,成都市檔案館:民國成都市政府檔案,全宗38/4/5459。
⑤據(jù)研究,成都的物價(jià)自1940年始呈幾何增長態(tài)勢,零售物價(jià)指數(shù)在1937年為103,到1940年為615,而到1945年竟達(dá)214343。參見:譙珊《抗日戰(zhàn)爭時(shí)期成都市民消費(fèi)生活水平研究》,《社會科學(xué)研究》2003年第3期。
⑥時(shí)人所提到的“影劇業(yè)”指的是“影劇業(yè)同業(yè)公會”,是成都的電影行業(yè)與戲曲行業(yè)聯(lián)合成立的同業(yè)組織。參見:《影劇商團(tuán)結(jié) 組織同業(yè)公會》,《新新新聞》1933年4月15日第9版。
⑦據(jù)說該啟事是針對“卯金刀”《請?jiān)u一下》而發(fā)出的“鄭重聲明”。見:萬承松《讀回答影劇業(yè)聯(lián)合啟事有感》,《新新新聞》1943年11月24日第8版。由于報(bào)紙散佚的原因,筆者未曾找到《請?jiān)u一下》一文以及影劇業(yè)所發(fā)出的“聯(lián)合啟事”。
⑧事實(shí)上,抗戰(zhàn)時(shí)期的一些藝術(shù)界人士極力撇清藝術(shù)與娛樂的關(guān)系。參見:史東山《對于藝術(shù)的認(rèn)識:藝術(shù)的真正目的所在決不是供人娛樂》,《國訊》1942年總第297期,第9-10頁。
⑨參見:《民國成都市政府檔案》,成都市檔案館:全宗38/4/5766。
⑩戰(zhàn)時(shí)《新新新聞》尚有數(shù)則新聞涉及“時(shí)裝戲”,大多“語焉不詳”。如1938年10月2日有報(bào)道稱:“影劇同業(yè)公會昨會商,雙十節(jié)各院演映抗戰(zhàn)戲”,此“抗戰(zhàn)戲”或可算“時(shí)裝戲”,但未知具體演出戲目,也無后續(xù)報(bào)道(見:《東鱗西爪》,《新新新聞》1938年10月2日第7版)。1938年11月,華瀛舞臺開業(yè),所演戲曲中有號稱“第一部抗敵新戲”的《民族英雄抗敵史》(見:《新新新聞》1938年11月16日第6版)。1939年10月,由“川、平、話、評”各劇聯(lián)合的“成都市戲劇界協(xié)會”成立,并舉行公演,內(nèi)有《日本的間諜》、《民族光榮》兩戲,根據(jù)劇名判斷應(yīng)屬“時(shí)裝戲”(見:《成都市戲劇界協(xié)會定期成立》,《新新新聞》1939年10月5日第7版)。





參考文獻(xiàn):
[1]韓曉莉.戰(zhàn)爭話語下的草根文化——論抗戰(zhàn)時(shí)期山西革命根據(jù)地的民間小戲[J].近代史研究,2006,(6):90-105.
[2]王笛.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M].北京:社會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09.
[3]成都之戲園[M]//傅崇矩.成都通覽.成都:成都時(shí)代出版社,2006.
[4]蔣維明.移民入川與舞臺人生[M].成都:成都科技大學(xué)出版社,1998.
[5]佚名.馬路上的兩種看客[N].新新新聞,1937-07-25(14).
[6]圣·彼得.消夏瑣記[N].新新新聞,1937-08-04(10).
[7]圣·彼得.戲劇還是戲劇[N].新新新聞,1937-09-07(10).
[8]王怡庵.從九一八說到全面抗戰(zhàn)[N].新新新聞,1937-09-18(11).
[9]周茂.希望太太小姐捐奢侈費(fèi)救國!以盛妝美食打牌看戲的錢 慰勞戰(zhàn)士救濟(jì)災(zāi)民[N].新新新聞,1937-10-05(11).
[10]慧.請娛樂場實(shí)行加國難捐[N].新新新聞,1937-11-11(8).
[11]湊熱鬧.成都市的怪現(xiàn)象[N].新新新聞,1938-02-18(8).
[12]打更匠.抽取摩登捐[N].新新新聞,1938-02-20(8).
[13]快快覺醒[N].新新新聞,1938-08-15(8).
[14]名學(xué)士.紀(jì)念國恥 鼓勵娛樂[N].新新新聞,1938-09-20(8).
[15]后防的一角[N].新新新聞,1938-10-21(8).
[16]名學(xué)士.節(jié)約運(yùn)動到現(xiàn)在[N].新新新聞,1938-10-25(8).
[17]名學(xué)士.怎樣驚醒木包的迷夢[N].新新新聞,1938-10-27(8).
[18]申小卒.醉夢的人們醒來吧![N].新新新聞,1938-11-11(8).
[19]佚名.疏散人口[N].新新新聞,1939-02-12(□).
[20]成都市文史委.抗戰(zhàn)八年成都紀(jì)事[G]//政協(xié)成都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成都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一輯.1985.
[21]沈冰齋.疏散辦法的我見[N].新新新聞,1939-05-11(8).
[22]停止娛樂場所營業(yè)[N].新新新聞,1939-05-26(5).
[23]秤主.幾個(gè)防空問題[N].新新新聞,1940-06-12(8).
[24]娛樂場所自動疏散[N].新新新聞,1940-07-07(5).
[25]尖兵.娛樂場所復(fù)業(yè)問題[N].新新新聞,1939-08-16(8).
[26]秤主.娛樂場所恢復(fù)營業(yè)[N].新新新聞,1940-04-21(8).
[27]影劇業(yè)提高票價(jià) 市民望政府取締[N].新新新聞,1942-09-03(7).
[28]尖兵.娛樂場的票價(jià)[N].新新新聞,1942-10-16(8).
[29]尖兵.畸形[N].新新新聞,1942-11-23(8).
[30]章華祺.回答影劇業(yè)聯(lián)合啟事的一封信[N].新新新聞,1943-11-21(2).
[31]萬承松.讀回答影劇業(yè)聯(lián)合啟事有感[N].新新新聞,1943-11-25(8).
[32]光緒三十一年研究所第一次開議[N].四川學(xué)報(bào),1906,(1).
[33]趙容予.改良地方劇與充實(shí)軍中文[J].政工周報(bào),1944,14(10).
[34]張德成.漫話蜀劇[J].戲劇新聞,1939,(8-9).
[35]鄧運(yùn)佳.中國川劇通史[M].成都:四川大學(xué)出版社,1993.
[36]譚清泉.黃吉安[G]//任一民.四川近現(xiàn)代人物傳:第一輯.成都:四川大學(xué)出版社,1987.
[37]劉念渠.戰(zhàn)時(shí)舊型戲劇論[M].重慶:獨(dú)立出版社,1940.
[38]胡度.川劇藝聞錄[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
[39]春熙舞臺表演胡阿毛 日內(nèi)公演[N].新新新聞,1937-10-01(10).
[40]成都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成都市志·川劇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
[41]劉念渠.戰(zhàn)時(shí)中國的演劇[J].戲劇時(shí)代,1944,1(3).
[42]電影戲劇業(yè) 捐一日所得 制寒衣送前線[N].新新新聞,1938-10-18(10).
[43]李一非.舊劇的整理與運(yùn)用[J].戲劇新聞,1939,(8-9).
[44]廖友陶.肖楷成與“三慶會”[G]//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西南地區(qū)文史資料制作會議.抗戰(zhàn)時(shí)期西南的文化事業(yè).成都:成都出版社,1990.
[45]陳建森.戲曲與娛樂[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6]唐澤稜.一年來的成都市(續(xù)完)[N].新新新聞,1941-01-06(7).
[47]春熙舞臺募捐救難民[N].新新新聞,1937-10-04(10).
[48]有錢出錢有物出物 各界愛國情緒高揚(yáng)[N].新新新聞,1937-10-07(10).
[49]新又新大舞臺“游藝大會”廣告[N].新新新聞,1938-11-13(6).
[50]九十五軍熱血劇團(tuán)公演廣告[N].新新新聞,1938-10-30(7).
[51]名學(xué)士.婦女寒衣募捐游藝會以后[N].新新新聞,1938-11-23(8).
[52]名學(xué)士.開支愈少愈好[N].新新新聞,1938-11-24(8).
[53]周正之.征募寒衣一點(diǎn)意見[N].新新新聞,1939-10-04(8).
[54]東鱗西爪[N].新新新聞,1939-10-04(7).
[55]劇院拒絕加收寒衣捐[N].新新新聞,1939-11-02(10).
[56]娛樂寒衣捐問題未解決[N].新新新聞,1939-11-05(10).
[57]電影應(yīng)該停業(yè)[N].新新新聞,1939-11-07(8).
[58]東鱗西爪[N].新新新聞,1939-11-11(8).
[59]成都社會概況調(diào)查[J].社會調(diào)查與統(tǒng)計(jì),1944,(4).
[60]黃裳.關(guān)于川劇[G]//曾智中,尤德彥.文化人視野中的老成都.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9.
[61]誦數(shù).在后方的人應(yīng)該怎么干[N].新新新聞,1937-09-01(14).
[62]李笑非.憶抗戰(zhàn)時(shí)期成都三益公藝員軍訓(xùn)連[J].四川戲劇,1990,(3).
[63]洪深.哀紅梅[M]//洪深文集:第四卷.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
[64]田禽.中國戲劇運(yùn)動[M].上海:商務(wù)印書館,1946.
[責(zé)任編輯:凌興珍]
Save the Nation or Entertainment: the Pressure of Public Opinion and Its Response to the Traditional Opera in Chengdu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CHE Ren-jie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China)
Abstract:As the major public entertainment in Chengdu, the traditional opera was facing a strong criticism in the name of national salvation from the local newspapers after the outbreak of anti-Japanese War. The theater was constructed as an opposite side of the national salvation. Under the pressure of national salvation discourse, the traditional opera industry in Chengdu tried hard to perform the anti-Japanese opera on one hand, in order to mask its entertainment property.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lso devote to the raise funds to resolve the conflict between national salvation and entertainment. However, all the exertion couldn’t reverse the unfavorable situation in the public opinion. In the name of national salvation, public entertainment was changed, but this change was limited. The entertainment, as the basic fun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opera, was once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opera may face a crisis of survival.
Key words: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traditional opera industry; Chengdu; theater; entertainment; national salvation; the pressure of public opinion
收稿日期:2015-12-04
作者簡介:車人杰(1990—),男,四川雅安人,四川大學(xué)歷史文化學(xué)院中國史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yàn)橹袊F(xiàn)代史。
中圖分類號:J809.26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1000-5315(2016)04-016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