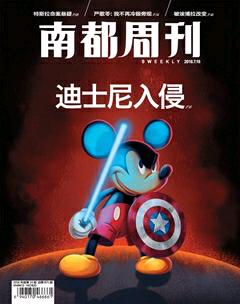被埃博拉改變
小菲

2014年8月15日,利比里亞首都蒙羅維亞,一位母親在埃博拉隔離病房里照顧孩子。
菜市場里賣著煙熏猴子肉
在利比里亞的首都蒙羅維亞,一片泥濘的土地上坐落著露天農貿市場。市場里人聲鼎沸,隨處可見簡陋的攤檔,海運箱改裝成的臨時貨品柜,還有載滿內衣或者木薯塊的手推車。潮濕的空氣里有一股燒煤的煙味,還混合著香料的芬芳和垃圾腐敗的臭味。被雨水沖刷而成的淺水洼里,赫然躺著一條已經泡得發脹的死狗。
再往里走光線變得昏暗,那里擺著一溜放著肉類的案臺:炸魚、鰻魚,爬著蒼蠅的羊頭。旁邊還有叢林肉,剛開始有點難辨認是什么,但肉堆上一只蜷著手指的猴子的手給出了提示。
早在2014年西非暴發埃博拉疫情之前,利比里亞已經遭受重創—貧窮、腐敗、饑荒。叢林肉是廉價蛋白質來源,卻把那里的居民跟可怕的埃博拉病毒聯系到了一起。兩年前的疫情始于靠近幾內亞的一個邊遠村莊,當地的森林遭到掠奪性砍伐后,村里一個幼童接觸了攜帶病毒的動物,很可能是野生果蝠之類的。接著疫情很快蔓延開了,超過28000人染病,其中11000是利比里亞人。
如今利比里亞已經禁止叢林肉買賣,但在蒙羅維亞的數百個農貿市場,每天仍在販賣這種非法肉類。麗貝卡·科里亞是一個肉檔主,她面前擺著被切成四塊的煙熏猴子,她說:“我賣這個已經20年了,但我沒有得埃博拉。”

2015年1月28日,利比里亞首都蒙羅維亞,一名利比里亞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正穿上防護服。
每10萬人里只有1個醫生
盡管埃博拉疫情引發了恐慌,但仍有很多利比里亞人并不清楚埃博拉病毒的傳播機制。在疫情暴發之前,利比里亞全國有400萬人口,卻只有少得可憐的50名執業醫師,沒人知道現在醫生的數字還剩多少。利比里亞是世界上第八窮的國家,它被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列為脆弱國家。對于一個如此弱小和分裂的國家,控制疾病幾乎是不可能的。
如今,距離埃博拉疫情的高峰期已經過去一年半了,匯集到這里并最終控制住疫情的一大批外國疾控專家、保健工作人員和危機響應小組都已經離去。但病毒不斷抬頭。在西非首次宣布埃博拉疫情結束之后,2015年5月又有10例新發病例,其中3例在利比里亞。專家認為病毒能夠在感染癥狀消退后的幾個月里持續通過性傳播。
生態健康聯盟的新病種專家、世界衛生組織顧問威廉·凱勒什說:“有些地區很可能會出現感染病例。”他認為可以像地質學家描繪地震風險地圖一樣,制作一張傳染病風險地圖。風險最高的是那些土地用途新近被改變的地區,比如利比里亞這種因為貧窮和戰亂,樹木被大量砍伐,人們深入叢林捕食野生動物的地區。他說:“我們要做好預案。為了應對可能發生的地震,建筑標準被更改了。我們也應該做點什么來應對可能發生的疾病。”在疾病高風險地區進行更好的教育和推廣早期篩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防止疫情暴發。
今天的利比里亞在防疫工作的很多方面仍然跟埃博拉疫情前一樣準備不足。盡管利比里亞已經淡出了人們視線,但流行病學家認為新的疫情再次暴發是有可能的。一旦疫情死灰復燃,就不僅是西非的問題了。全球商旅可能讓疫情前所未有地蔓延各地。
留作種子的糧食都被吃掉了
在蒙羅維亞郊區的金斯維爾,列維·里爾威利蹲在他小棚屋的泥地上,指著四周擁擠的棚屋說:“這里很多家庭的生活都很苦。在埃博拉流行期間,你甚至不能出門訪友。留在自己家,也不能伸手去碰其他人,連擁抱自己的孩子都不可以。人人都感到非常害怕。”在埃博拉蔓延時,飛往蒙羅維亞的航班都全部取消了, 跨國貿易辦公室關閉,學校和市場也都不開門。最終,人人留在自己家里。農民們吃完家里儲備的糧食,開始吃原本打算來年播種的種子,吃完種子之后就沒有東西可吃了。
里爾威利踢著腳下的泥土說:“我大部分家人都死于埃博拉,11個人。”
埃博拉仍然像幽靈一樣盤亙在蒙羅維亞。在大西洋和梅蘇拉多河交匯處的貧民窟西點,一所學校在疫情時被征作臨時治療中心。一場大雨過后,學校周圍的小巷里滿是雨水和污水。一個當地婦女就在學校旁邊用鐵桶給一個小女孩洗澡。疫情暴發后學校被清洗干凈,地板重新鋪過,還粉刷一新,跟小巷周圍破敗不堪的建筑形成鮮明對比。但學校幾乎是空的,學生們大多避而遠之。

2015年1月24日,利比里亞首都蒙羅維亞,一名男孩頭頂炸魚在街上售賣。
埃博拉響應小組發不出薪水
隔壁的理查德·科伊科伊是西點埃博拉響應小組的成員,在疫情爆發期間,他負責把染上疫情的病患送到救治中心,也會把罹難者的尸體運走。在疫情最開始的疾控戰略失敗之后,國際專家們支持了像科伊科伊這樣的當地埃博拉響應小組,是這些小組在遏制疫情擴散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埃博拉響應小組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當地815名醫護人員,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疫情過后這些小組大多解散了,幸存下來的工作人員也找了新的工作。
科伊科伊的小組理論上保留了下來,他們還有一條熱線電話。但就像西點很多居民一樣,他感到被遺忘了。 他問道:“我們現在要把患病的人送去哪里呢?就在昨天,我們收到了一例埃博拉疑似病例報告,但是我們組沒有辦法跟進。連我自己的薪水都被拖欠兩個月了,所以我現在才坐在這里。”
1月,就在利比里亞第三次宣布埃博拉疫情結束幾個小時后,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在附近的塞拉利昂發現一例病例。到了3月,一名埃博拉幸存者傳染了另外一個人,繼而又傳染了10個人,其中8人不治身亡。而管理部門在兩名患者死亡之后才知道這件事。威廉·凱勒什說:“我們知道埃博拉病毒仍然在西非傳播。事實上,沒有新的人類感染病例,并不意味著疾病已經消失。”
九成農田在疫情中荒棄
從蒙羅維亞出來的高速公路上,一輛卡車突然急轉方向墜落路邊。卡車撞入了路邊一個擁擠的院子里,撞壞了房屋。人們沖向冒著蒸汽的卡車殘骸,混雜著女人們的尖叫聲。
利比里亞一位農業專家佩德勒·克雷格正在洛法州調研糧食安全問題,他看到車禍連忙跑過去看,他喊道:“人還活著!”盡管這是個奇跡,克雷格看起來卻頗為憂慮。顯然司機知道卡車的方向盤有問題,但他還是冒險把車開上路了。他解釋說:“有很多人愿意做同樣的工作。”
往后的幾公里路也修得很好,但是在發展項目結束的地方,路況馬上變差了。克雷格還在回想那個卡車司機:“人們是自愿那么做的,為了維持生計沒有別的辦法。”雙向的車流都小心地繞開路上的坑坑洼洼,車子一直在上下顛簸。
最后車子經過了一個舊營地,以前那里住著內戰流離失所的人。盡管洛法州曾經是該區的糧倉,在內戰期間農業卻減產了四分之三,而且至今沒有恢復到戰前水平。利比里亞如今大部分糧食依靠進口。現在洛法州的很多農民收成的糧食僅夠自己糊口,碰上糧食減產或者缺乏必要儲存設施,他們自己都要購買昂貴的進口糧食。克雷格概括說收割前的“雨季”是缺糧的原因。
今年,糧食缺乏有演變成饑荒的趨勢。在埃博拉疫情的高峰期,隔離措施讓農民無法參加傳統的合作社耕作,連續幾周目睹身邊的人不斷生病和死亡,促使很多人逃離了該區。

2015年1月27日,利比里亞首都蒙羅維亞,一名護工在由于埃博拉病毒肆虐而關閉的幼兒園內。
一個西非政府間合作組織,馬諾河聯盟農業和食品安全項目組的成員肯耶·巴萊說在2015年春播期間,洛法州大概90%的農田都被丟荒了。
在通向洛法州主路邊的一個小村子加拉買里,應克雷格要求,鎮長召集了一些人來座談。一個叫墨菲·史密斯的農民第一個發言:“這里的事情越來越糟了。”很多人清理了土地上原先的自然植被,但是又沒有種子去種農作物。和洛法州里大多數人一樣,史密斯一天只吃一頓飯,通常在深夜做飯,才不至于因為饑餓睡不著。
鎮長嘎麥·托克帕是個瘦削的女士,她身穿綠色傳統裙裝,她說:“我們在清理灌木叢,但是我們缺少作物種子。”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說他們上一次在當地分發賑濟糧是在2014年12月,通過合作伙伴基督復臨會發展與救濟局操作的。類似的分包工作很常見,也容易導致權責不清。要么那些賑濟糧從未分發放到位,要么是參與座談的人都在說謊。無論是哪種情況,當地居民都還在生存線上掙扎。托克帕聽說沿路的另一個鎮北巖,收到了救濟金和糧食。史密斯問道:“為什么他們不能勻一點給我們呢?”
起不到長期效果的救援工作
在北巖鎮的檢查站,路上拉起了一條繩子,旁邊是清洗桶。因為埃博拉病毒通過液體傳播,經常洗手是一個有效的預防方法。鎮長科魯巴·阿格維站在一棵巨大的棉花樹下避雨。一位婦女坐在旁邊的樹根上照顧一個枯瘦的嬰兒。阿格維說:“沒有,世界糧食計劃署沒有在這里分發過食物。”當地政府也沒有發過救濟糧。“我們壓根兒沒有得到任何幫助。”
沿途的薩拉耶鎮也是同樣的情形。鎮上人口眾多,但居民生活并未恢復正常。當地農民弗洛默·班納說:“你能看到載著食物的世界糧食計劃署卡車開過,但他們不停這個鎮。”(而根據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的檔案記錄,他們于2014年12月在薩拉耶鎮分發過食物。)班納認識的人里沒有人收到過賑濟糧,他說:“我們都不知道賑濟糧去哪里了,有傳聞說去了北巖鎮。”
農業司地區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多米格·科利正在往家里走,他在路上停了下來,說:“農民要得到糧食并不難,因為現在是收割季節。如果他們告訴你自己很滿意,是因為他們覺得從你這里得不到好處。”但他說不出多少農民已經返回了自己的土地,又或者多少農民有種子播種。他說:“埃博拉疫情之后就沒給我發過汽油,我還要自付油費去考察農場。”這限制了他下鄉考察。
克雷格說:“我曾在天主教救濟會工作,看見過工作人員偷竊食物。朋友們都住在很大的房子里。因為薪水足以負擔我的生活,我安于工作。但他們說我很愚蠢。”數十年的貪腐和缺乏社會監管,社會價值觀已經扭曲,誠實反而變成了不可靠的品質。
盡管克雷格的家人在疫情中保持了健康,但他仍然過得很艱難。利比里亞的嚴重危機—戰爭和埃博拉,引發了持續的混亂。政府和國際救助預算花掉了,卻沒有起到長期效果。比如,埃博拉疫情期間分配給利比里亞的382輛救護車, 根據總務署最新的統計只剩下268輛,其余的不知所終。
就利比里亞糧食問題詢問不同的人,聽到的回復都很糟糕。盡管利比里亞現在并不算經歷大饑荒—大饑荒的標準是每天有萬分之一的死亡率—但據糧食和農業組織最保守的估計,多達63萬利比里亞人沒有足夠的食物。世界糧食計劃署說該國超過一半的人口在糧食安全線邊界或者之下。
即便在最好的狀況下,實時數據也很難獲得。伊麗莎白·格里芬研究基金會一位負責全球衛生安全和傳染病的國際項目經理加文·麥格雷戈-斯金納說,利比里亞極其缺乏準確的統計數據。他坦承:“這表明國際社會的努力正在土崩瓦解。數據不應如此難獲取,肯定是哪里出錯了。”通常,在災難響應的最初24小時內,救災人員會挨家挨戶去問災民他們需要什么。然而在利比里亞,災難發生兩年后,一個全面的評估卻都還沒完成。他說:“人們都不知道該從哪里著手。”

2015年1月25日,利比里亞首都蒙羅維亞,民眾在海灘休閑。
去年夏天,在曼哈頓大都會博物館的頂層,全球衛生響應和恢復聯盟的協調員邁克爾·麥克唐納率領一組救災專家在此討論西非問題。該小組從聯合國國際埃博拉重建會議中分離了出來,隨便提起一個30年內發生的災難,小組里都能找出去過災后重建的人。
把權責下放給當地居民,是最近在救災人員中流行的想法。世衛組織埃博拉響應負責人彼得·格拉夫說,讓當地人監控潛在的埃博拉受害者,并進行防疫宣傳,是埃博拉疫情最終得以遏制的原因。 “埃博拉證明了本土化的決策過程在疫情響應上是很有效的。”
采用上述策略的其中一個組織是國際關懷項目。卓林·穆林斯在埃博拉疫情暴發時任該組織的利比里亞負責人,他介紹說他們與700個鎮的領導和傳統醫師合作,為居民提供有效的衛生建議。因為是由當地人,而非外國的專家或者承包商在民眾中進行宣傳,人們相信他們的建議,這些城鎮中95%的人都沒有埃博拉感染病例。
而且權責下放到社區還可以減少他們對國際援助和本國政府的依賴性。援助方式發生任何變化,都會受到來自當地政府和原有援助提供商的阻力,特別是當涉及到資源變化時,會觸及既得利益者。顯然,慣性的力量阻礙了西非的災難救援工作。利比里亞弱小又分裂,以至于傳統的危機響應不奏效。
健康合作伙伴組織利比里亞負責人布賴恩·墨菲-尤斯提斯說:“如果你跟我一樣相信,埃博拉病毒瞄準的是一個破碎的衛生系統,那只有重建并長期鞏固衛生系統才能奏效,除此以外任何方法都不行。”到今天為止,約三四成的利比里亞人口缺乏醫療保障,跟疫情發生前相比沒有任何改善。而現在國際醫療援助的預算被用在了新的國際危機—寨卡病毒上,只剩下一個埃博拉治療中心還在運作。墨菲-尤斯提斯說:“埃博拉進一步打擊了人們對衛生系統的信心。”他說新的嚴重衛生問題已經開始出現。在疫情暴發時,“大規模的預防接種活動被推遲,以免公眾聚集。”傳染病藥物分發被打亂了,導致了諸如耐多藥結核病的死亡率增加等問題。
國際投資讓事情有了一些改善。格拉夫說:“實驗室容量擴大了”,盡管還做不了一些先進的檢測。在3月利比里亞埃博拉疫情抬頭時,一位專家還要飛往當地指導基因測序工作。當地醫療工作者接受過分診和快速識別埃博拉早期癥狀的培訓。但墨菲-尤斯提斯指出,從長遠來看未來依舊不樂觀。
就拿洗手這么簡單的事情來說,記者隨機訪問了幾個利比里亞人,發現捐贈給他們的肥皂都已經用完了,捐贈的水桶則散落各處,被改作裝菜或者裝碗筷用途。
格拉夫說:“從統計上看,幸存下來的人口中可能爆發更多病例。”他指著道路旁邊的鎮子說:“這些地區應該要預備著埃博拉卷土重來。”

2015年2月1日,利比里亞首都蒙羅維亞,兒童在為一個芭比娃娃整理頭發。利比里亞政府表示該國已接近“消滅”埃博拉病毒,大部分民眾的生活陸續恢復正常。
防疫出路在哪里?
去年在蒙羅維亞的可口可樂廣告展望了利比里亞的未來,一個廣告牌上印著:“我相信,利比里亞會更好更幸福”,另一塊廣告牌上寫著:“我期待明天會更好”。還有一塊廣告牌上是埃博拉幸存者的照片,高舉雙手作出表示勝利的V字,眼睛直視鏡頭,廣告語是“我成功了,我相信”。
就在一塊廣告牌旁邊,埃博拉的幸存者珍內·蓋圖從醫院的窗戶望向外面的暴雨打在停車場的救護車上,她剛開始接受心理輔導。她說:“疾病奪走了我的丈夫。發病4天后他就去世了。我們剛剛將他下葬,我兒子的皮膚就開始發燙。”蓋圖把年僅3歲的兒子從鄉下帶到了蒙羅維亞求醫。“我們當時坐在出租車上,兒子就在我的膝蓋上咽了氣。我緊緊抱著他的尸體,不讓人知道那是埃博拉病毒。”蓋圖隨后致電了首都負責處理埃博拉病例的醫療隊,但沒有人出現。在接下來的幾天里,她就跟兒子的尸體一起待在蒙羅維亞一棟空房子里。最終她也病倒了,自行前往了一個救治中心,等待死亡的到來。但她沒有死。她說:“我活下來了。但我感覺像變了個人,變得跟別人不一樣。現在連我自己的親人都不要我了。”主治醫生的助手伊曼紐爾·巴拉遞給她一張紙巾。巴拉跟同事在醫院里的無國界醫生組織門診工作,治療幾百個埃博拉幸存者的身心問題。
巴拉說:“埃博拉幸存者被嚴重污名化了。在埃博拉治療中心接受救治的患者經歷了可怕的事情。但離開治療中心,這些幸存者面臨的挑戰才剛開始。”他在大廳跟另一位幸存者阿莫斯·杰西打招呼。當巴拉介紹說自己的很多病人也在接受其他組織的援助,杰西插話說:“實地調查一下,親自問問幸存者他們是否得到了救濟。疫情過后的生活比埃博拉病毒本身還要糟糕。”
(來源:《大西洋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