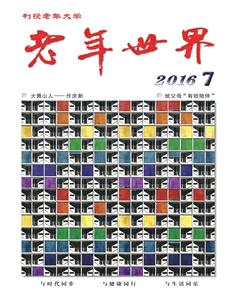溫家寶的地質往事
安鐘++汝羅昊
青年溫家寶
我喜歡層巒疊嶂的山峰。我們常在沒有人煙的地方工作,每次上山,除了幾個地質人員外,很少能見到人。有時,騎著牦牛或駱駝要走上一天。我一邊走一邊唱,把從小學會的歌曲都唱上一遍。空曠的山野,只有我的歌聲在山谷里回響。——溫家寶
“我至今還記得他在祁連山野外考察時攀著繩子過河時的樣子。兩條腿搭在繩子上,雙手握著繩子交替往前移動,整個人在繩子上搖搖晃晃。”
73歲的廣州海洋地質調查局退休干部蘭方手拿《溫家寶地質筆記》對記者說。他曾是溫家寶在甘肅地質局區測二隊的同事。
自3月26日在全國發行上市后,《溫家寶地質筆記》一書廣受好評。這本近52萬字的書稿,以憶文和筆記結合的獨特方式記錄了溫家寶1968年至1985年的地質往事。
隊里來了個研究生
“這人叫溫家寶,是北京地質學院畢業的研究生,還是個黨員。”
1968年春節剛過,地處酒泉的甘肅省地質局區測二隊新來了一位穿著藍色卡其隊服、身形清瘦的年輕人。聽到隊友們的議論,劉霄祥開始留意這位新來的同事。
劉霄祥與溫家寶在甘肅同事多年,曾擔任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參事。當時,區測二隊有近四百人。1965年之前,甘肅省地質局原有一個區域測量隊。1965年,為支援三線建設,黑龍江、寧夏的一批地質隊員來到甘肅酒泉,重新組合成立了區測二隊。隨后,每年都有一批大中專學生和技術人員分到隊里。
劉霄祥說:“我們隊里大部分技術人員是大中專畢業生,研究生以前還沒有過,隊里的黨員也很少。憑著這個身份,他本來可以分到高校或者研究所工作,為什么要到我們這里?”
85歲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地質大學(原北京地質學院)原校長趙鵬大,在擔任校長期間經常聽到學校老師聊到學生時期的溫家寶:“當時國家號召支援三線建設,號召年輕人去西部,到最艱苦的地方去,溫家寶是響應國家號召去甘肅的。”
溫家寶在書中還回憶了自己從北京啟程到甘肅時的情形:1968年初,剛過完春節,告別父母,“在一個寒冷的夜晚,我擠上了從北京駛往蘭州的列車。”行李很簡單,“一個裝衣物的帆布箱、一套用兒時曾用過的油布捆綁的被褥、兩個裝滿書籍的木箱。列車在逆風怒號中開動了。我此行是前往甘肅省地質局報到,那將是我從事地質工作的新起點。”
在長達六年的野外地質工作經歷中,蘭方和溫家寶在工作上互相協作,生活上同甘共苦,一個鍋里吃飯,一頂帳篷里休息。他說,家寶很大的特點是愛學習、愛看書。晚上常點蠟燭苦讀,看各種各樣的書。
風雪中的地質筆記
見證那段歲月的,還有《溫家寶地質筆記》所引用的45本筆記。
在書中,所有的野外地質筆記簿影印件,文字工整,幾乎沒有涂抹的痕跡,手繪地質圖像印刷一般清晰。
40多年前,甘肅地質局發的野外記錄簿是紅色的本子,業內人把它簡稱為“野簿”。野外考察隊員每次在野外考察,要在記錄簿上畫地質圖、標明巖層結構、地理坐標等。
這45本筆記并非溫家寶全部的筆跡資料。溫家寶在書的自序中寫道:“可惜的是,由于單位多次變動、個人多次搬遷,我的一些地質筆記、圖標資料、手稿及標本等散失了。”
“吃別人嚼過的饃不香。”溫家寶第一次引起馬海山的注意,就是因為這句話。“當時我就覺得這個年輕人很不一樣。他很認真,為了一個考察點,多遠多難走的路他都要去。”
1970年,溫家寶分到馬海山擔任組長的區測二隊五分隊礦產組,正式參加野外考察。
馬海山回憶,溫家寶每天上山都要做記錄。晚上,給素描圖、剖面圖著墨,還要總結分析各種資料。
蘭方說,在當年分隊組織的野外原始資料展評會上,家寶的野外記錄文字工整,文筆流暢,看上去像印刷一樣整潔,深得好評,一直是大家學習的楷模。
在書里,溫家寶解釋了為什么自己把找煤放在那么重要位置:那時,許多農民溫飽無法解決,一天只能吃兩頓飯,燒火做飯多用麥草、玉米秸,寒冬臘月,取暖煨炕也多用牛糞、秸稈等。有人進入祁連山北坡,砍伐極為珍貴的松柏涵水林帶,或河溝中的灌木林。
夢里常回祁連山
溫家寶在書中說,“我難忘祁連山的找礦歲月,懷念昔日的同事,牽掛著甘肅的發展。”
1995年6月、2002年9月、2009年10月,溫家寶到甘肅出差期間,都曾專門抽時間看望過去的老同事。
據媒體報道,2002年9月溫家寶在酒泉看望老同事時說:“多年來我一直想著大家。”
他看到原政治處主任白志榮,問他,“您心寬人好,是我的老領導。對了,您吃飯還擱醋嗎?”
多年來,溫家寶一直保持著與老同事直接或間接的聯系。
2005年,住在長春的老同事張庸接到溫家寶的一封來信,隨信寄了兩千塊錢,請他轉交一位叫周振環的老同事。
溫家寶在信中說:“知周振環身患重病,甚為掛念,特寄上兩千元,以助他治病之需。”
張庸和周振環都是溫家寶在甘肅地質局第二區測隊的同事,周振環曾和溫家寶一起出野外考察。
摘自《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