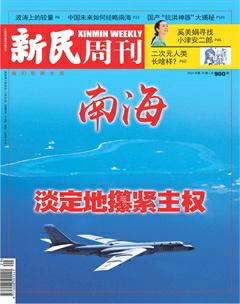南海博弈,美國的“如意算盤”
西方的國際法體系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同時也伴隨著16世紀以來近代具有掠奪、侵略、擴張、奴役性質的殖民主義運動,逐步地由簡單到復雜、有實踐到理論地發展起來。由于制定這種“國際游戲規則”者是走出家門到外面“撈世界”的主兒,因此不可避免地將一些損人利己的做法,借助國際法貼上公正、公平和正以的標簽。
軍事斗爭背后是文化博弈
最近在同一位留學西方十年的博士交流時,他將17世紀之前和之后島嶼先占和管轄權標志的行為方式演變做了詳細梳理。比如最初,人們放上一些船錨之類的東西,以示島嶼有主,以后是插上旗幟,再以后是放個十字架或舉行一個簡單的宗教儀式等等。而現代國際法大致就是建立在西方近代幾百年這種實踐基礎上,甚至部分還淵源于古羅馬物權法。
于是問題來了。問題一,殖民主義時代的西方是到東方來“撈世界”的,東方國家是“被撈者”,“撈世界”者制定的游戲規則對“被撈的世界”會是福音嗎?問題二,以壓倒優勢的武裝力量支撐的“撈世界”者制定的“游戲規則”對“被撈世界”會公正嗎?問題三,“撈世界”的制定的“游戲規則”適合于東方的“被撈世界”嗎?比較西方的島嶼先占儀式的習慣性標準和管理行為,東方國家自古有自己的習慣性先占行為標準和管理行為,從未舉行過符合西方先占的“標準”儀式——比如太平島上不存在基督教的十字架遺跡,只有觀音廟、土地公廟。比如“九段線”的宣示和管理等等。若以西方為標準,即可顛覆東方世界已成共識的先占行為和管轄權,將原有的國家領土肢解,從而帶來混亂。這就是我們東方世界在被迫接受和使用國際法時,時刻必須意識到的問題。
因此,“南海仲裁案”除了學者們已經指出的種種法律上的荒謬外,根本上是用基于西方歷史和近代殖民主義實踐的國際法個別條款,否定基于歷史習慣法而已成東方世界共識的國家領土形成的規則和現狀。從文明對峙的角度看,是強勢的西方文化對東方傳統秩序的又一次破壞性解構,而這種破壞所引起的后果就是混亂和沖突。
東方的百年抗爭過程伴隨著東方世界的文化解構和領土解構的過程,在意識形態方面,各種西方思潮已經占據優勢位置,傳統思想不是被消滅就是被邊緣化。意識形態解構雖然發生在精神文化世界,但是,同這種文化解構相向而行的是伴隨而來的國家領土解構。如果說文化解構于無形,具有隱蔽、麻醉、難以抗拒的特點,且已無可奈何地、部分地被東方世界接受,那么對于重視土地的、有著數千年農耕傳統的中國來說,主權和領土的解構就是對生存的直接威脅和根本上的侵害。近代史就是中國這樣的傳統農耕民族被威脅被侵害被肢解的歷史。雖然,市場經濟和海外貿易已經成為當下國家主導性經濟結構,但源于對耕地依賴的強烈領土主權意識作為重要文化遺產、作為應付西方文化解構最頑強的底線被繼承了下來。國際法中“民族自決”也好、“地區自治”也好,至今無法動搖這一底線。
西方國家在瓦解近鄰宿敵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過程中,使用過娓娓動聽“民族自決”和“地區自決”,當然最終還是通過暴力解決。奧斯曼帝國被解構的歷史表明,當國際法與國家利益捆綁時,會倫為國家政治角逐的工具,這種環境下國際法就成了玩偶,帶有先天缺陷的國際法更是與公平、公正、正義毫無關系。西方近代史表明,文明化的侵略者往往是玩弄國際法的大師。
回顧南海的歷史沿革、特別是二戰結束后,中國擁有南海諸島主權從無異議到出現爭端以至發展今天的動蕩不安,背后起支配和推動作用的就是上述兩個因素,即西方文化借助國際法對中國領土主權的持續解構,以及國際法同國際政治中遏制中國的國際群體的無恥合流。目前,這個裁決居然把中國的歷史性權益“解構”得無影無蹤,更為荒唐的是指鹿為馬,稱太平島是礁不是島,引來中國人憤怒的同時,也引來世人一片嬉笑。荒唐到極致便是荒唐制造者的自我毀滅,“南海仲裁案”確實是連美國都不好意思演下去的鬧劇,仲裁結果也確實是“一張廢紙”,對其說“不”理所當然。
中美開戰論純屬炒作
從東西方文化沖突背景再進入具體國際政治領域,南海問題的實質是美國借助周邊侵占南沙群島的國家遏制中國,而越南、菲律賓等國想借助美國對華戰略維持侵占的局面。這次南海仲裁案背后真正的較量是中美,盡管菲律賓在前臺的表演得聲嘶力竭,直奔國際仲裁法庭鬧騰,充其量只是美國的一個棋子。
面對中國在南沙填海造島、增強維護南海主權的力度,美國不敢也不愿大打出手,又不能不加阻撓,這一輪目的是讓中國在外交上陷于被動,在國際社會惡心一下中國,同時為自己干預南海打造國際法上的合理性。形象地講,在中美對峙中,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與中國加強南海主權維護力度迎頭相撞,美國新設立了一個法律火力點,以后會憑借這個新設陣地不斷開火,而對中國來說,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完全有能力奉陪,也增設法律火力點對射而已。雙方在進行法律交鋒時,軍事既是背后決定性的支撐力量,也是輔助性的配合手段。
美國清楚,欲將一紙仲裁,讓中國人視為祖產的南海聽任被人奪走,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一定會激怒飽受百年割地賠款之苦的中國。在國際仲裁法庭即將宣判前夕,美國知道玩笑開大了,被激怒的中國說不定有過激的行為來回應胡鬧性質的仲裁結果,美國有點心虛,于是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柯比呼吁不管仲裁結果如何,各方保持克制。之前在6月18日,“里根”號航母編隊和“斯坦尼斯”號航母編隊在菲律賓海、而非南海進行聯合演習,演習完畢,“里根”號航母編隊接替“斯坦尼斯”號航母編隊進入南海,而非兩支航母艦隊同時進入南海,防止被激怒的中國在軍事上有報復舉動。所以,南海雖在軍事上呈現劍拔弩張之勢,但主動權在中國手里。美國惡心一下中國,且自認為威懾目的已經達到,也會罷手。中國也以三大艦隊百余艘軍艦集結軍演,以示決心,且已將“南海仲裁案”結果視同廢紙,南海現狀無實際損失。這次仍如先前預測的那樣,中美南海亮劍,有驚無險。所謂中美戰爭一觸即發,純屬炒作,聳人聽聞。美海軍部長仲裁結果出來后立即來華溝通,也是一種得了便宜就收手、息事寧人的姿態。
中美雙方在仲裁出來前都已有克制的表現。在1990年代臺海危機時,美國出動兩個航母編隊逼近臺灣海峽,而這次雖然也來了兩個航母編隊,但一個部署在南海,一個部署在南海外圍,可見美國不想把事情搞大搞糟。反觀中國方面,盡管調動北海、東海、南海三大艦隊在南海舉行軍演,但地點不在南沙群島,而選擇西沙群島附近的區域。原是應由國防部或南部軍區、海軍司令部,或至少南海艦隊司令部出面的通告,卻由海南省三亞海事局來發布軍演通告。在仲裁出來前夕,中美如約進行的“環太軍演”亦照樣舉行,這些都是雙方釋放不愿把事情搞大、和平解決分歧、嘗試建立新型大國關系的意愿表示。
警惕“薩德”暗度陳倉
在“南海仲裁案”結果出來前幾天,美韓宣布正式在韓國部署“薩德”導彈系統,表面看,在時間上是配合美軍航母編隊在南海方面行動,具有分散中國南海注意力、牽制中國南海方向行動的企圖,其實質甚至直撲中國命門——在中美角逐的大棋盤上,美國似有在南海外交上虛晃一槍,而真正落子是在東北方向的“薩德”導彈部署上。
“薩德”導彈配備的X波段雷達對韓國防衛毫無意義,卻對中國核威懾、核反擊構成極大威脅。導彈防御效能一直是導彈防御辯論的焦點,中段目標識別是關鍵問題。為提高突防概率,導彈攻擊除真彈頭外,同時還要發射誘餌、箔條等以便迷惑對方,因彈道導彈中段是在大氣層外飛行,較輕的氣球誘餌和較重的彈頭具有相同的飛行軌跡,從彈道軌跡上無法區分彈頭和誘餌,而且進攻方還可采取各種技術手段使得誘餌具有和彈頭類似的雷達和紅外特征,加大了中段目標識別的難度。
由于誘餌很輕、很便宜,可以大量裝備,因此如果防御方無法區分彈頭和誘餌,即使攔截彈可以在合適的時間到達目標導彈彈道上合適的位置,打擊到真彈頭的概率也將會非常低。美國官方也承認中段目標識別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只要美國導彈防御系統的效能維持在較低的水平,成功攔截中國報復性核彈頭的概率就很低,中國就可以維持對美國的核威懾。
韓國的X波段雷達可以看到中國戰略導彈的主動段和主動段結束后釋放彈頭和誘餌的過程。根據動量守恒定律,導彈釋放較輕的誘餌時速度改變量很小,而釋放較重的彈頭將引起較大的速度改變。如果韓國雷達可以看到誘餌釋放過程,那么美國反導系統就可以根據導彈速度改變而輕易地分辨出彈頭和誘餌,徹底解決這一難題。在和平時期,部署在韓國的X波段雷達可以用于觀測中國戰略導彈(特別是潛射導彈)的發射試驗,積累彈頭和誘餌的雷達特征數據,這有利于提高反導系統目標識別的能力。另外,這也迫使中國進行核反擊前需先行摧毀韓國領土上的“薩德”導彈系統,這樣多一輪的先行打擊也就讓美國贏得了足夠的預警時間。總之,前沿部署的X波段雷達可以提高把真實彈頭從誘餌中識別出來的能力,使美國反導系統效能得到大幅提升,中國對美國的核威懾將被抵消。這才是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實質性威脅。
所以,“南海仲裁案”進入高潮,所有人注意力高度集中在看南海“風景”時,美國卻在韓國部署“薩德”導彈系統,是否有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之嫌?
一個“南海仲裁案”,一個“薩德”導彈部署,客觀上菲律賓和韓國被美國拉上外交戰車,暫時離間了中國與這兩個國家的關系,特別是部署“薩德”導彈系統,異常兇狠的一招,軍事上直接搖撼中國安全的基石,外交上瞬間讓中韓關系跌入冰點,也算一時得手。接下去看中國方面如何化解了,化解也是可能的。當然,美國的做法也會引起這兩個國家內部紛爭,引出國內反對卷入中美沖突的那股勢力,引發兩國內部沖突,當然,這美國可就不管了。
至于歐洲方面,也許是看在北約同盟的份上敷衍一下美國,也許是真想幫美國一把,在6月6日新加坡舉行的香格里拉會議上,法國聲稱要推動歐盟加入南海巡航,雖是口頭表態,在講究姿態為主的外交方面,中國在南海問題上陡增了來自歐洲的壓力。但是接下來歐洲發生的事件,至少會拖延歐洲介入南海的時間,或許法國的倡議只能是雷聲大、沒雨點,過過嘴癮。
“南海仲裁案”結果表面看對中國不利,實際中國的各種潛能已被激活,只要掌握好節奏,事態不難往有利于中國的方面傾斜。(作者系著名海權戰略學者、上海政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