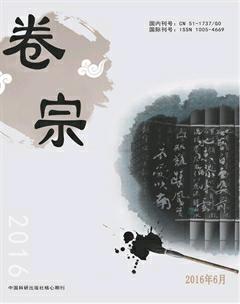略談藏傳佛教尼眾寺院的制度及經濟情況
摘 要:女性作為一個群體,在社會中有很重要的的地位,然而,在藏族地區,女性剃度出家以從事宗教活動為生存意義的這種人生觀,對大多數藏族女性個人的價值取向產生著一定的影響。藏傳佛教出家女眾作為一個特殊群體,近幾年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在收集。分析、查閱近幾年來有關藏傳佛教出家女性資料的基礎上,對尼眾寺院的制度及經濟情況進行了一些梳理。
關鍵詞:尼眾寺院;制度;經濟
1 藏傳佛教僧尼
僧尼,就是出家受戒的女性,來源于梵文“比汗尼”,藏語稱為“覺姆”。公元7世紀佛教傳入吐蕃,當時本教占統治地位。雖然在松贊干布時期曾修建了許多寺院,但不曾有女性出家修行的行為。公元8世紀以后,吐蕃第三十八代贊普赤松德贊大力扶持佛教,建寺度僧,使得吐蕃時期出現了僧尼,開始有了女性出家修行者,形成了藏傳佛教史上最早的比丘尼僧尼。但是與現在不同的是,那時出家者多為貴族女性,是一個積善養德、修行養生的群體。藏民族是以信仰藏傳佛教為主,隨著時代的變化,信仰也會被時代替代或更新,而藏傳佛教在藏族人心中并沒有被其他事物所代替,修行時她們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出家為尼是藏族女性光宗耀祖的事。有句諺語:“三個男兒一個僧”,女性出家也是如此。藏族女性出家的原因我們可以從她們的宗教信仰、家庭生活和自身婚姻狀況來分析說明,有一部分僧尼是受過教育的,一部分是由于交不起學費而中途退學,一部分入寺前是文盲,入寺后不自覺地接受了藏傳佛教的教義教規,在生活中嚴格要求自己,棄惡揚善。
女僧們學習的經文主要是顯宗方面的,包括《因明論》、《中觀論》、《智慧論》、《俱舍論》、《戒律本論》五部經典著作。此外,除了學習經文外,僧尼們還要不斷地學習藏文,以提高自己的藏文水平。漢語在寺院不太受到重視,由于廣播新聞的傳播,雖然僧尼們不重視漢語學習,但大多數僧尼都具有一定的漢語口語和聽力能力。另外,據筆者了解到,現代文化的傳播,一些僧尼還學起了英語,有些僧尼可以用流利的英語跟外國人進行對話。這表明僧尼們的文化多樣性。在民眾中一般有大的佛事時,僧尼由于學識不夠,所以不會請她們進行大的佛事,這就決定僧尼生活的單調與清貧。只有超度亡人時請僧尼們去念經,但這樣的機會很少。一般是通過考試的僧尼才有機會去念經。最常做的佛事是閉齋。除了超度亡人閉齋外,還有在藏歷年4月14日、15日、16日,9月21日、22日、23日閉齋,在閉齋期間,第一天1點進食,第二天整天不能進食,第三天4點半才能進食。群落僧尼的生活模式,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較多,例如年齡小的阿尼,下午的時間可以跑出去玩耍。由于飲食起居需要自己自理,在生活品質方面,不用的阿尼會因為經濟狀況不同而呈現差異,反映在飲食、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僧尼們在這種斷炊苦修中,努力去通曉明理,得到“正覺“。守持齋戒的目的,在于超度亡靈以及禳災驅禍等。
2 尼眾寺院的制度
作為一個教團組織就必須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內部組織和制度。寺院作為宗教最直觀的外在實體,是宗教信仰的表達場所,集合信仰、經濟、教育、政治于一體,是繼承和傳播宗教文化的重要組織機構。而一套行之有效的內部組織和制度是寺院有序教團組織得以維持和完善的基礎。尼眾寺院的制度,1959年以前為一時期,稱為“過去”;1982年以后為一個時期,稱為“現在”(1959—1982年寺院處于關閉、禁止狀態)。過去與現在相比,尼眾寺院的制度和戒律大體相同,但過去入寺者大多為父母做主,而且過去尼眾寺院無人數限制,年齡在10歲以上就可入寺。現在有了信教自由的權利,多數是經個人自愿申請、父母同意、寺院“錄取”之后,再由當地宗教局審批認可后可入寺。經批準開放的各寺,“錄取”是有定額限制的,而且必須是年滿18歲以上的女性才可以申請。
尼眾的組織結構比較簡單,現在一般有三五人組成“寺院管理委員會”,兩年改選一次。每個尼眾寺院都有一個住持,一個經師,一個管理員,其他是教師。堪布—相當于活佛,是尼眾寺院中的最高學者,但只有寧瑪派極少數人可取得此學位。措欽—也叫住持,主管全寺學習修行。洛本 —即經師、教官,負責教讀、講解經文典籍。翁則—負責寺廟的經濟收支、生活、建設等管理工作。格古—又分為涅巴格古和曲本格古兩種,其中涅巴格古是翁則的助手,而曲本格古負責大小法事的安排,佳瑪——負責尼姑寺的茶飯等日常事務除了這些內部組織,尼姑寺還按照藏傳佛教的慣例,對尼姑們的剃度、飲食、起居及日常生活作了較為嚴格的規定。可見,尼眾寺院有著嚴密有序的內部制度,從而使得尼僧們零散、個體的信仰及其宗教情感均得以規范和一致化,這些組織制度又是按照藏傳佛教的內部要求和慣例制定的,這樣使內容和形式相得益彰、渾然一體,形成引人入目、獨具特色的宗教文化現象。所有尼眾寺院都有相同的假期制度,即每年放假兩個月,春耕一個月,秋收一個月,尼僧可以回家幫助家里勞動。但是在家期間,不得動刀割糧食 (不殺生戒),不能打糧食 (脫粒中易踩死、打死蟲子),所以在家也只能做些家務。西藏的尼眾寺院中,有的尼僧離家太遠 ,假期不回家,就兩三人結伴外出 “化緣” ,所得上繳寺院,用于寺院集體開支和幫助無家供養的尼僧。尼僧平時如果有事需要回家,例如父母有病或家有喪事,或者需要進城買生活必需品和看病時,不得一人行動 ,必須兩人同行 ,回寺后得向住持匯報。尼僧如有親戚朋友來探望,事先要秉報寺主、住持,經同意后 ,尼僧才能出寺院與親友們見面。一般寺院都有圍墻 ,寺院外有專門接待來訪者的客房。俗人不分男女不得進人寺內,更不能住在尼宅內。晚上尼僧必須回寺內住 ,不得留在客房與親友同住。親友來寺探望 ,每次最多兩天。這兩天中,尼僧可以與親友們一起在草地、河邊輕松地度過,吃到一些自己喜歡吃的食物和糕點水果 。我們可以看到其嚴密有序的內部制度,它規范和一致了原本零散的尼僧生活,又使尼僧的宗教情感得以體現。這些組織制度是按照藏傳佛教的內部要及慣例制定的,這也體現出尼僧在藏傳佛教的傳播過程中不容小覷的作用。
3 尼眾寺院的經濟情況
改革開放以后,藏地寺院正在國家政策的引導下,開始走‘以寺養寺,農禪并重的道路,各尼寺也不例外,尼僧在從事宗教活動的同時,參加生產勞動或縫紉、手工編織工藝品等,以此來增加寺院的經濟收入。隨著政策的引導和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寺廟開始走自主發展之路,如著名的拉薩倉古寺就設有自己的診所、餐廳和裁縫店,憑借高超的手藝和良好的口碑,在拉薩也算是小有名氣。但是總體來講,大部分尼寺地處高山峻嶺之中,遠離城市和村寨,很難發展,也不易得到廣大信徒的香火布施,群眾家里有紅白喜事也難以上高山請僧尼來念經超度、祝福消災。加上群眾的普遍認為尼僧主要是修煉自身,一般也不找尼僧做法事。所以通常情況下,尼寺的經濟都是比較拮據的。
正如德吉卓瑪的《藏傳佛教出家女性研究》中所提到的:“作為一個宗教共同體,卻沒有共同經營的具有實力的經濟體系,它不像是旱地尼眾寺院那樣,有寺院供給的舒適而整潔的僧舍和一日三餐等”,藏地尼眾寺院的經濟狀況無論是與旱地還是當地僧伽寺院相比,都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尼眾寺院的經濟情況與僧伽寺院差別很大,大部分尼寺地處高山峻嶺中,遠離城市,遠離村寨平均海拔都在 3以刃米以上不易得到廣大信徒的香火布施,因為尼僧沒有高學位,尼寺也就得不到像僧伽寺院一樣的社會地位和認可,沒有社會布施的財源收人 (扎巴、喇嘛則有一定津貼 )。更主要的是尼眾寺院沒有自己的土地、牛羊、佃戶,也沒有固定的大施主。有的尼眾寺院也有些牛、羊、豬、雞等,但都是居士們放生在寺內的,不能殺,不能賣 ,只能讓它們自然死亡。尼眾寺院要靠尼眾家庭對寺院的義務供養 ,比如凡是新人寺的尼僧,其家庭必須給寺院布施錢、糧 ,根據各家條件,多少不限,但最起碼要為全寺尼眾開一頓飯,每個尼僧至少 2 元錢,寺主、住持還要多些,每年的佛日也要給寺院布施一點。另外 ,每年秋季 ,大多數尼寺都通過 “化緣”為寺院乞得錢糧作為公共開支。透過尼僧生活來源的分析,我們發現尼僧不可能掌握十分豐厚的固定財產,更不可能擁有較多的周轉資金。尼僧們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瑣事都是互相幫著去完成。即使是有像維修房屋、砌灶夯墻等大型苦力勞動,也是寺中尼僧集體出力,共同完成。在寺院內,尼僧們以師徒關系結為一體,住在同一僧舍里起灶共居。
4 當今藏傳佛教僧尼研究的不足
在我國,對于藏傳佛教的女尼研究還很薄弱,不僅在有關藏傳佛教史的通論性著作中對此很少涉及、而且藏、漢、日及西方的記載也相當零散,這對于我們的研究提出了很大的挑戰。但是經過學者們的不懈努力,仍將藏傳佛教出家女這一群體的產生及其歷史沿革給我們重新展現。當前藏傳佛教出家女研究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沒有系統、全面的資料,每個地區都有其不同的特點和文化背景,所以不同地區的藏傳佛教出家女發展狀況都不一樣,這就需要我們做大量田野工作,寫大量的尼僧民族志,不僅要描述藏傳佛教出家女中的精英階層,而且要把普通尼僧寫入歷史納入到人類學、宗教學、民族學研究的范疇中來。以往的藏傳佛教出家女性研究領域比較狹窄,主要涉及歷史淵源、派別、宗教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內容,對藏傳佛教出家女性的文化教育、社會生活等方面的內容也是近幾年才逐漸涉及到。而且還有更多的領域未曾涉足或鮮有所及,諸如藏傳佛教出家女性的心理、宗教信仰、政治、經濟、健康狀況等。
雖然學術界在藏傳佛教出家女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因剛剛起步,還很薄弱,并且在研究中存在一些不足,對藏傳佛教出家女性的研究大部分仍停留在單一的歷史追述、女性現象方面,對藏傳佛教出家女性問題產生的歷史與現實的背景還沒有進行理論上的深入。這主要是由于中國的藏傳佛教出家女性研究缺少理論建構,或者說正在建構理論框架。
5 結語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宗教政策的落實和改革開放的春風,藏傳佛教重新得以全面發展。與此同時,一些曾回鄉務農或從牧的尼僧重披袈裟從幕后走上臺前,紛紛重返昔日的寺廟故地點燃了第一把香火,許多尼寺由此得以恢復。隨之剃度出家,削發為尼的女性,在廣大藏區與日俱增,并在各地不斷營造修行地或尼眾道場,為她們創造賴以生存的環境,且遍布于各個藏區,從而構筑了當今藏傳佛教一個龐大的社會實體或主要載體之一,在藏族社會中產生著廣泛的影響。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 是人類生活的基本組織形式,在人類和社會發展方面承擔著重要的職能。一部分的女性出家給許多的家庭帶來一些無奈, 一方面她們的出家解脫了自己在家庭中精神的折磨,不再在家庭里背負著沉重的家務勞動,還有那些來自丈夫的暴力,寺院是他們生存的惟一的避風港。藏傳佛教的女僧在不斷地出現,是藏族女性實現自我價值的一種體現, 是達到自我價值的最高境界,也是藏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現代社會發展中女性文化發生著變遷, 而藏傳佛教尼僧們依然過著他們清平的生活, 在青藏高原上寫著自己的歷史,為藏傳佛教的發展做著貢獻。筆者的學識有限, 但關于藏傳佛教女僧的研究至今還很少, 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
參考文獻
[1]楊恩洪. 西藏婦女口述史[M].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
[2]房建昌. 尼姑在藏傳佛教中的產生及其發展[J]. 中國藏學, 1988(2).
[3]供邱澤仁. 論尼姑在苯教中的地位及其作用 松潘扎雍仲卡尼姑寺個案研究[D]. 中央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08.
[4]周晶. 寺廟里的女人 20 世紀民主改革前西藏尼僧的生存狀態研究[J]. 青海社會科學,2005(2).
[5]德吉卓瑪. 格魯派尼眾僧團初探[J]. 西藏研究, 2004(1).
[6]妮瑪娜姆. 藏傳佛教尼眾寺院考[J]. 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9(4).
[7]德吉卓瑪. 藏傳佛教出家女性研究[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3.
[8]桑頂 多杰帕姆,扎圖登朗杰. 桑頂多杰帕姆活佛本生傳記 歷代轉世及桑頂寺簡史[J]. 德康索朗曲杰,譯.西藏研究,2003(4).
[9]劉夏蓓. 從生活所迫到自愿選擇甘南夏河尼僧出家原因的人類學調查[J]. 民族研究,2007(2).
[10]諾布旺丹、巴桑卓瑪.藏傳佛教的兩種女性觀[J]中國藏學.1995(3)
注釋
[1]德吉卓瑪,藏傳佛教出家女性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2月。
[2]察倉尕藏才旦,中國藏傳佛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4月。
作者簡介
德格吉(1988-),女,藏族,青海同德人,學校學院:中央民族大學藏學研究院在讀博士,碩士,研究方向:清代藏族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