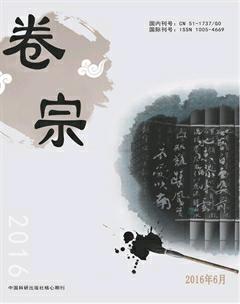論郗鑒對東晉政局的影響
摘 要:東晉高平郗鑒歷來被研究魏晉南北朝的史家所忽略。西晉末年,繼承了其祖郗慮門風的郗鑒,通過招撫流亡宗族,積累力量,得到了東晉王朝的重視。郗鑒南下之時正是王敦之亂前夕,在加入到東晉政府后,郗鑒幫助明帝先后平定了王敦之亂與蘇峻之亂。此外,郗鑒在經營京口之兵、解庾王矛盾、發展生產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可以說,東晉前期能夠得到平穩的過渡與發展,與郗鑒密不可分。
關鍵詞:郗鑒;東晉政局;影響
王夫之言:“東晉之臣,可勝大臣之任者,其為郗公乎!”[1]“郗公”,即高平郗氏郗鑒,東晉成帝時曾官至司空。但若提及“勝大臣之任者”,人們首先會想到輔佐晉元帝的瑯琊王氏王導而忽略了郗鑒的作用。事實上,縱觀東晉一朝,郗鑒確如王夫之所言,配得上是中流砥柱的“大臣”。其居功至偉,后人卻鮮有論及其功,可謂之憾。本文便從東晉前期的特殊政局出發,來探究郗鑒在其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1 家世背景
《晉書·郗鑒傳》:“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慮之玄孫也。”[2]要想全面了解郗鑒,首先要先了解其先世郗慮的生平。因為在士族門閥的魏晉南北朝社會中,先輩的影響往往能為整個家族的走向奠定重要的基調。據史書記載,郗慮字鴻豫,曾從師經學大師鄭玄,并在荀彧的推薦下,成為三國時期曹操重要的人才集團——“潁川集團”的一員,隨后逐漸得到曹操的重視,曾官至御史大夫。[3]但在建安十九年捉拿謀反未果的伏皇后一事中,由于在行動中并沒有身先士卒,表現出對曹操的忠心,[4]因此逐漸被疏離中樞,銷聲匿跡,甚至在史書中都未列其傳,只能散見于零星的史料記載中。
通過郗慮的生平可以分析得出:(1)郗慮是當時名士大儒,早年拜經學大師鄭玄門下;(2)郗慮當時官至御史大夫,位高權重,擁有很高的聲望;(3)郗氏家族直到郗鑒才開始重新登上歷史舞臺,可能是由于郗慮在伏皇后被誅一事中失去曹操的信任,從此隱匿而致。郗鑒作為郗慮的玄孫,顯然深受其影響。郗氏家族歷代傳承儒學門風,至郗鑒,也依然是“博覽經籍”[2],可謂當時儒學之集成者,而這種世襲家學的特點也是日后獲得東晉門閥士族文化認同的根本。[5]另一方面,雖然郗慮之后再無高官顯貴,但高平郗氏一族名門聲望尤在,在當地的宗族鄉里中仍具有較高的名譽。此外,以其祖郗慮的政治生涯作前車之鑒,再加上西晉后期戰亂紛仍,使郗鑒的政治嗅覺更加銳和謹慎。綜上,雖然史稱郗鑒“少貧孤,躬耕隴畝”,但“以儒雅著名,不應州命”,作為御史大夫之后,累世名望和名儒之后的有利條件使其在“鄉議”的基礎上成為了凝聚宗族鄉里的重要凝聚力,此外,郗鑒為人恩義,“復分所得,以恤宗族及鄉曲孤老,賴而全濟者甚多”[2],這種救人于危難、施人以恩義的行為最容易形成以深受眾人仰慕的領袖為核心的共同體,并由此不斷積聚力量。[6]因此郗鑒被眾人擁戴為主,攜千家避難于魯之嶧山,成為東晉建國前夕北方部曲武裝的一支。
2 東晉初政局與郗鑒南下
東晉建國之初,正是朝政不穩、政局動蕩之時。東晉王朝偏隅江南,實力遠遜于西晉,在與北方民族的作戰中也處于守勢。在國內,東晉王朝的政治特點是“皇帝垂拱、士族門閥、流民御邊”,晉元帝司馬睿雖居皇帝位,但整個朝政都控制在瑯琊王氏——王導和王敦的手中,王敦更是手握重兵,屯于重鎮武昌,遙望建康。而元帝不堪久居人下,便暗中培植自身勢力。在中央,任用戴淵、周顗等名士以制王導,軍事上,引劉隗、刁協等流民帥的武裝力量以制衡王敦,意圖恢復皇權政治。但由于東晉朝臣不愿看到皇權過度伸張而破壞門閥之序,尤其是皇權的膨脹更是損害了江南大族的利益,[5]因此,當王敦以“清君側”為由進攻建康時,晉元帝身邊也只有劉隗、刁協兩支流民武裝,其根本不是王敦的對手。之后建康陷落,劉隗、刁協被擊潰,王敦把持了朝政,晉元帝也在兵敗后郁郁而終。后明帝即位,王敦引兵退回武昌,但遙控朝廷,不臣之心漸起,此舉遭到了東晉群臣的反對,其弟王導也站出來反對其造反之心,支持東晉政府,“率群從昆弟子侄而是余人,每旦詣臺待罪”,[2]以求保住瑯琊王氏一族。但當時明帝即位不久,東晉王朝軍事實力嚴重不足,此時更難阻擋王敦東進之舉。在“王敦之亂”已露端倪之時,東晉王朝的局勢可謂不得不兇險,因此明帝便將希望寄托在當時都督兗州的郗鑒身上。
反觀郗鑒在被當地宗族鄉黨擁戴為主避于嶧山后,不斷積聚武裝力量,因此在元帝初鎮江左時被任命為龍驤將軍、兗州刺史。此后雖然遭到了徐龕、石勒的接連侵犯,但郗鑒始終忠厚仁義,對流民光加招撫,因此雖然“日尋干戈,外無救援,百姓饑饉,或掘野鼠蟄燕而食之”,卻“終無叛者”,所領部曲也“三年間,眾之數萬”,[2]隨后郗鑒便被加封為輔國將軍,都督兗州諸軍事,其所率領的部曲成為了一支重要的武裝力量。但其活動范圍主要在北方,且并未與司馬睿一同過江,因此郗鑒與東晉政府的關系是若即若離,自身獨立性很強。但據史料記載,在接下來的兩年時間里郗鑒便迅速渡江南下,并一度成為了東晉王朝的重要支柱。其南渡準備時間之短,被東晉政府接納之快,這其中的緣由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注意與思考。
《晉書·元帝紀》:
(永昌元年)秋七月,王敦自加兗州刺史郗鑒為安北將軍。[2]
《晉書·郗鑒傳》:
永昌初,征拜領軍將軍,及至,轉尚書,以疾不拜。[2]
由于郗鑒在北方已經成為一支重要的武裝力量,故成為王敦和東晉朝廷爭相拉攏的對象。王敦獨自加郗鑒為安北將軍,企圖繞過朝廷一方為己所用,足見對其重視;而此時朝廷也加郗鑒為安北將軍,但后來轉至尚書,卻有使郗鑒調離自己的流民武裝只身進入朝廷而對其加以提防的意味。而郗鑒本人也深知保持自身獨立的重要性,脫離了自己重要的軍事砝碼——兗州武裝力量而獨自進入朝廷任官,則必將很快淹沒于皇權與門閥士族的傾軋之中。因此,郗鑒“以疾不拜”,委婉地謝絕了朝廷的征召。但此時復雜的政治形勢使郗鑒不得不卷入了東晉朝廷與地方爭權奪利的斗爭之中。南下之事已成大勢,只得盡快提上議事日程,而至于是倒向王敦一方還是朝廷一方,郗鑒仍在觀望中。
這時,東晉政府的誠意打動了郗鑒,據《晉書·紀瞻傳》載:
時郗鑒據鄒山,屢為石勒等所侵。瞻以鑒有將相之才,恐朝廷棄而不恤,上書請征之,曰:“……若使鑒從容臺闥,出內王命,必能盡抗直之規,補袞職之闕。自先朝一來,諸所授用,已有成比。戴若思以尚書為六州都督、征西將軍,復加常侍,劉隗鎮北,陳眕鎮東。以鑒年時,則與若思同;以資,則俱八坐。況鑒雅望清重,一代名器。圣朝以至公臨天下,惟平是與,是以臣寢頓陋巷,思盡聞見,惟開圣懷,垂問臣導,冀有毫厘萬分之一。”[2]
起初戴若思鎮守合肥,與劉隗、刁協一起,是晉元帝所信賴的心腹。但在第一次王敦內亂中,戴若思兵敗被殺,劉隗、刁協被擊潰。此時紀瞻以郗鑒“補袞職之闕”,鎮守戰略要地合肥,其意圖是想拉攏郗鑒倒向東晉朝廷一方,支持明帝。但紀瞻只能起到舉薦作用,而無最終決定之權,因此他希望“惟開圣懷,垂問臣導”,使當時位于中樞、掌握朝政大綱的王導支持引郗鑒為援,而王導也必然采納紀瞻的意見,以鑒制敦。因此,明帝即位后,便拜郗鑒為安西將軍、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假節,并讓其鎮守建康的重要藩屏——合肥,既授予郗鑒重要官職,又不讓其離開自己的兗州武裝力量,以表自己的誠意,故郗鑒便接受任命,倒向東晉政府一方。
3 穩定江左
(一)“與帝謀”平王敦之亂
正如前面所述,手握重兵的王敦在明帝即位初便萌生不臣之心,不久便再次引兵東向,直指建康。明帝便以當時鎮守合肥的郗鑒為援,意圖節制王敦。王敦聞之,便上書拜郗鑒為尚書令,令其調離合肥,以減輕軍事壓力。郗鑒到建康之后,便立即“與帝謀滅敦”[2]。
郗鑒與明帝密謀的具體內容,史書中并無記載,但從其他零星記載中可以分析得出,郗鑒的建議是引流民帥的武裝力量為援對抗王敦,典型的代表便是蘇峻與劉遐。
《晉書·明帝紀》:
丁卯,加司徒王導大都督、假節、領楊州刺史。……以尚書令郗鑒行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征平北將軍、徐州刺史王邃,平西將軍、豫州刺史祖約,北中郎將、兗州刺史劉遐,奮武將軍、臨淮太守蘇峻,奮威將軍、廣陵太守陶瞻等還衛京師。[2]
《資治通鑒·晉紀》 明帝太寧二年六月丁卯:
帝將討敦,……郗鑒行上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郗鑒以為軍號無益事實,固請辭不受;請召臨淮太守蘇峻、兗州刺史劉遐同討敦。[3]
《晉書·劉遐傳》:
太寧初,自彭城移屯泗口。王含反,遐與蘇峻具赴京都。[2]
《晉書·蘇峻傳》:
王敦作逆,詔峻討敦。卜之不吉,遲回不進。……王敦復肆逆,尚書令郗鑒議召峻及劉遐援京都,敦遣峻兄說峻曰:“富貴可坐取,何為自來送死?”峻不從,率眾赴京師,頓于司徒故府。[2]
《明帝紀》中的記載大都是臨行前對將領的調遣安排,但其中一個細節不得不加以注意,即對王導和蘇峻(及劉遐),一個是“加”,一個是“征”。僅僅一字之差其實反映了一個重要的事實:王導本身就為東晉重臣,所以“加”稱號以坐鎮三軍;蘇峻、劉遐等流民帥是東晉朝廷為平王敦之亂特地從江北“征”召而來作為援助,其本身與東晉政府并沒有很強的歸屬關系,兩者性質不同。從《資治通鑒》、《劉遐傳》和《蘇峻傳》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對流民帥蘇峻、劉遐的征召正是郗鑒的建議,目的是增加東晉軍隊的實力對抗王敦。而在隨后的平定叛亂中,劉遐和蘇峻等流民帥的武裝,也確實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當時東晉政權剛剛建立,并沒有一支真正屬于自己的武裝,即使是想借流民帥之兵,也隨著王敦第一次攻入建康而蕩然無存。此時郗鑒引來劉遐、蘇峻之兵,正是恰到時機地支援了羸弱的東晉政府。在平叛中,劉遐與蘇峻同赴京都并大敗王含,切掉王敦一翼;而當蘇峻初到京師,道遠行速,軍旅疲憊,沈充、錢鳳欲趁機攻其不備,卻被蘇峻和其將韓晃將其部隊橫截于南塘并大敗之,此一役,王敦元氣大傷,不久便因病離世,叛亂也隨之被平定。因此,王敦之亂之所以會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被鎮壓下去,靠的是郗鑒所“密謀”的借助流民帥的力量,給東晉政府以強援,從而取得平定王敦之亂的勝利。
(二)平蘇峻之亂
郗鑒在平王敦之亂時引流民帥作為東晉政府的強力支援,劉遐、蘇峻等流民帥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事有利弊,王敦之亂后,流民帥蘇峻日益驕溢,并在平叛中積累了頗高的聲望,軍備也獲得了補充,實力大增。于是東晉朝廷便采取之前對待流民帥的做法,將其羈縻于長江以北,并加以安撫,以其作為南北之間的軍事緩沖力量。即使蘇峻日益驕橫,甚至有“得罪之家有逃者,峻輒蔽匿之”[2]的現象,東晉政府也大都對其“不聞不問”。此“憒憒”[7]之政對于當時的政治形勢來說,無疑是可取的:一方面,王敦之亂使東晉政府元氣大傷,兩次攻入建康也造成了京畿周圍的生靈涂炭,需要時日加以修養和恢復;另一方面,東晉政府也無強大的軍事實力與蘇峻抗衡,而將其羈縻在長江之北,使其作為南北對峙間的軍事緩沖力量,則有利于東晉王朝獲得短暫的安寧。但當時的護軍庾亮,在明帝初崩后,便意圖趁機掌握朝政,在接連廢黜南頓王司馬宗與其兄司馬羕等宗室勢力后,緊接著把目標對準了當時實力強大的流民帥蘇峻。為抑制蘇峻,庾亮通過下詔任蘇峻為大司農,位特進,引其至京,意欲收取其部曲私兵為己所用。不料此舉卻引發了蘇峻的直接起兵造反,隨后渡江攻入建康,東晉政府的京畿地區再度遭受了史無前例的災難。
蘇峻初反時,當時任徐州刺史的郗鑒欲引兵東渡,但遭到了庾亮的反對。等到王師敗績,建康淪陷,庾亮倉皇而逃,才重新任命郗鑒等人平叛。此時郗鑒接收的無疑是個巨大的“爛攤子”:首先京都淪陷,將士元氣大傷,京畿地區一片混亂,以至郗鑒“去賊密邇,城孤糧絕”;此外蘇峻兵馬兇猛,東晉政府可組織的兵馬不足,難以與之對抗。在此危急情況下,郗鑒采取了以下措施:(1)鼓舞士氣,在臨行前“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從而達到了“三軍爭為用命”的效果;(2)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戰略決策,即“先立營壘,屯聚要塞,既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采取消耗敵人的方法,挫其銳氣,“然后靜鎮京口,清壁以待賊”,[2]最終使敵道絕糧斷,從而不攻自破。
以上措施無疑穩定了東晉政府與軍隊混亂的局面,隨后陶侃被推舉為盟主,引兵從武昌順流而下,使蘇峻面臨被東西夾擊的困境。走投無路的蘇峻果然強攻京口意欲渡江北上退去,而最終在石頭城附近墜馬身亡,叛亂也很快被鎮壓。在此役中,郗鑒的措施在穩定軍心、切斷叛軍退路等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使剛剛建立不久的東晉政府再度避免更大的混亂。
(三)營京口之兵
對于京口,人們首先會聯想到謝玄于京口創建北府兵,并在淝水之戰中立下赫赫戰功的英勇場景。然而,我們絕不能忽視郗鑒在此地長期經營的作用,而京口也一躍成為東晉王朝重要的軍事堡壘。
郗鑒首次提出京口的重要性,在前面已有提及,即在蘇峻之亂中“靜鎮京口,清壁以待賊”,以達到消耗蘇峻的目的。郗鑒在平蘇峻之亂中都督揚州八郡諸軍事,而當時的撫軍將軍王舒、虞潭均受其節制。
《晉書·郗鑒傳》:
及陶侃為盟主,進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時撫軍將軍王舒、撫軍將軍虞譚皆受鑒節度。 [2]
《晉書·王舒傳》:
時將征蘇峻,司徒王導欲出舒為外援,乃授撫軍將軍、會稽內史,秩中二千石。……峻聞舒等兵起,乃赦庾亮諸弟,以悅東軍。[2]
《晉書·虞潭傳》:
會陶侃等下,潭于郗鑒、王舒協同義舉。侃等假潭節、監揚州浙江西軍事。[2]
《資治通鑒·晉紀》成帝咸和三年五月乙未:
陶侃表王舒監浙東軍事,虞潭監浙西軍事,郗鑒都督揚州八郡諸軍事。[3]
由此可見,整個三吳地區被分割成了兩個戰場,以王舒為首的是“東面軍”,以虞潭為首的是“西面軍”,他們均受郗鑒節制。郗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鎮京口,并控制了整個三吳地區。此舉無疑切斷了蘇峻的退路,因為要想過江退回北方,必渡京口,而京口一旦被東晉控制,蘇峻便遭受腹背受敵的困境,此足以顯示京口的重要戰略意義。
京口之位置,是京城建康的“東門”,向西可拱衛建康,保證京城的穩定,減少變故的發生:向北是北來流民重要的入口,可控制流民的數量,節制流民帥的勢力;向南則可以控制三吳,三吳是建康的核心地帶,大部分的糧食、物資都由三吳(尤其是會稽)運送到京都,有效地控制京口,便有利于三吳的穩定,一旦存有變數便可立即采取行動,控制三吳。《南齊書·州郡志》便充分肯定了京口的歷史價值:“今京城(指京口)因山為壘,望海臨江,緣江為境,似河內郡,內鎮優重。”[8]郗鑒在經營京口時曾在“賊帥劉徴聚眾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時“加都督揚州之晉陵、吳郡諸軍事,率眾討平之”,[2]維護了京口與三吳的穩定。因此,田余慶先生曾給郗鑒以高度的評價:“他(郗鑒)的軍隊雖然不曾獲得北府兵這一專門稱號,實際上卻已是具有特殊地位的北府兵。”[9]
(四)解庾王矛盾,防止門閥傾軋
庾亮,子元規,是庾氏家族重要的代表人物,其妹是明帝庾皇后。王敦之亂后,王氏家族受到了沉重的打擊,雖然王導盡全力保住了王氏一族,但已失去了強有力的軍事保障,雖位居中樞,但對東晉王朝的作用已大不如前。明帝深受王敦之亂之忌,加強了對王氏家族的提防,進而更加親庾亮而疏王導。庾亮與皇室結親后權力不斷上升,其對王導依然處于中樞位置甚為不滿。于是在明帝初崩,成帝即位不久,庾亮便開始著手廢黜王導,意欲把持朝政。
《晉書·王導傳》:
于是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于外。南蠻校尉陶稱間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為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覺智者之口。則如軍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為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于是讒間始息。時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聚上流,擁強兵,趨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污人。”[2]
從上述記載中可以看出,王導與庾亮的矛盾深來已久,而此時的王導已再無實力與庾亮抗衡,通過政治和輿論手段減輕壓力。但庾亮對王導的態度卻是“大奸不掃,何以見先帝于地下”[2],可見其對王導的痛恨和堅定的廢黜之心。但縱觀成帝一朝,直到王導、庾亮先后死去,也未發生庾王門閥傾軋的禍亂。究其原因,我們便不得不提及郗鑒在其中的斡旋作用。
郗鑒深知庾亮有獨攬朝政之心,雖然庾亮因蘇峻之亂而遠離建康,但手握重兵,又是成帝之舅,因此遙控朝廷,大權獨攬。若庾亮攻入建康,勢必會造成門閥傾軋,那時東晉王朝又要面臨生靈涂炭,這是郗鑒所不愿看到的。因此郗鑒拒絕了庾亮向其提出的廢黜王導的建議,“至是,亮又欲率眾黜導,又以咨鑒,而鑒又不許”[2]。庾亮之所以要爭取郗鑒的意見,主要是因為忌憚郗鑒的京口之兵。前面我們已提到,京口是建康的門戶,起重要的拱衛作用。王敦之亂后形成了長江上游和下游兩大軍事力量,“開啟了荊、揚之爭的序幕”[10],一是上游的武昌力量,其主是庾亮,一是下游的京口力量,其主是郗鑒,雙方實力勢均力敵,因此在廢黜王導一事,郗鑒不同意,庾亮便不敢輕舉妄動。此外,郗鑒還力主郗氏和王氏聯姻,如歷史上“東床快婿”的故事,便是郗鑒為其女選擇王導之侄王羲之為婿,使兩族交好,互為支援。因此庾亮雖深有廢黜之心,無奈郗鑒“靜待京口”與以節制而不敢發難,因此“在這兩大軍事勢力的微妙平衡的支持下,由各個渙散的集團混合而成的東晉王朝反倒嬗變為結構相對穩定的政權”[11],而在這種相對穩定中,郗鑒在其中的努力斡旋起到了重要的調和作用。
(五)發展生產
永嘉之亂后,中原地區經過戰火洗劫后經濟一片凋敝,于是南渡流民集團便到相對穩定的江淮地區發展生產,其中尤以京口、晉陵一代最為典型。魏晉以前,江南地區人口稀少,仍然屬于不發達地區,“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執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12]3270。到了漢代,江南地區仍然有待開發,“吳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之一都會也,……江南卑濕,丈夫多夭”[13]1668。兩晉之際,流民集團因躲避戰亂移居江淮,京口、晉陵一帶也隨之獲得了較大的開發。例如《元和郡縣圖志》中記載:
信豐湖在縣東北三十里,晉元帝大興四年,晉陵內史張闿所立。舊晉陵地廣人稀,且少陂渠,天多惡穢。闿創湖,成灌溉之利。初以勞役免官,后追紀其功,超為大司農。[14]
《宋書·州郡志》:
晉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鑒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晉陵諸縣,其徙過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僑郡縣以司牧之。[15]
譚其驤先生根據《宋書·州郡志》中記載統計,“江蘇省中南徐州有僑口二十二萬余,幾乎占全省僑口十之九。南徐州共有口四十二萬余,是僑口且超出本籍人口二萬余。有史以來移民之盛,迨無有過于斯者也”[16]。可見這時期南渡至江淮地區的流民大都集中在京口、晉陵一帶,人口的大量增加,也為這一地區經濟活動的開展帶來了豐富的勞動力。以至于后來的東晉南朝,京口和晉陵地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今京城(即京口)因山為壘,望海臨江,緣江為境,似河內郡,內鎮優重。宋氏以來,桑梓帝宅,江左流寓,多出膏腴”[8],“晉陵自宋齊以來,舊為大都,雖經寇擾,猶為全實”[17]284。由此可見,京口、晉陵在經過開發之后,已經成為東晉南朝的重鎮之一,而在其中郗鑒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4 結語
田余慶先生曾言:“東晉初年政局,三五年一大變,變則干戈擾攘,臺城丘墟。”[18]69郗鑒繼承了先世門風,通過招撫流亡,逐漸形成了一支重要的武裝力量。之后追隨明、成兩帝先后平定了王敦之亂與蘇峻之亂,并及時調和了庾、王兩大家族的矛盾,使東晉王朝在歷經一系列動蕩之后進入到平穩的發展時期。縱觀郗鑒一生,從鎮守京口開始,他就擁有了與其他士族爭奪權力的資本。但他始終從東晉一朝的大局出發,竭力維持穩定的局面。整個東晉的歷史走向,也深深打下了郗鑒的烙印。
參考文獻
[1] 王夫之.讀通鑒論[M].長沙:岳麓書社,1982.
[2] 房玄齡.晉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
[3] 司馬光.資治通鑒[M].北京:中華書局,1956.
[4] 陳壽.三國志[M].北京:中華書局,1959.
[5] [日]川勝義雄.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6] [日]谷川道雄.中國中世社會與共同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7] 劉義慶.世說新語[M].北京:中華書局,2011.
[8] 蕭子顯.南齊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2.
[9] 田余慶.秦漢魏晉史探微(重訂本)[M].北京:中華書局,2011.
[10]張帆.中國古代簡史(插圖本)[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11][日]川本芳昭著.中華的崩潰與擴大[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
[12]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63.
[13]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4.
[14]李林甫.元和郡縣圖志[M].北京:中華書局,1983.
[15]沈約.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
[16]譚其驤.長水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7]姚思廉.陳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2.
[18]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M].北京:中華書局,2012.
作者簡介
陳俊維(1993-),男,山東昌邑人,現為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魏晉南北朝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