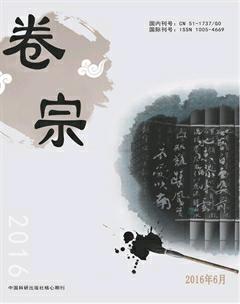巴別爾小說《我的第一只鵝》特點淺析
吳璐婷
摘 要:巴別爾小說別具特色,本文謹以《我的第一只鵝》為例探究其背景、環(huán)境和場面構(gòu)置上的特點。
關(guān)鍵詞:《我的第一只鵝》;背景;環(huán)境;場面構(gòu)置;特點
從背景上有以小見大、筆力萬千的特點。該小說在背景方面的介紹上顯得非常簡略,并且沒有用太多的筆墨去交代具體的時間、地點、人物等背景,而是以參謀長口授的命令引入的,令團長“率所部朝丘古諾夫·多勃雷沃特卡方向前進,與遭遇之敵交火,并殲滅之……”由此我們可以窺見小說的背景是戰(zhàn)爭歲月,簡潔明了地把背景融合在小說中,為后文的情節(jié)發(fā)展、人物設置打開了一扇門,非常流暢通順,且不著筆墨直接描寫戰(zhàn)爭大規(guī)模的殘酷與血腥,減少了給讀者的災難感,充滿人文關(guān)懷,但這是為了更深層次地表現(xiàn)戰(zhàn)爭帶來的危害,看似輕描淡寫,實則加重了后文“殺鵝”事件帶來的震撼,從側(cè)面反映出戰(zhàn)爭,突出其殘酷和對人性的扭曲。
環(huán)境上,首先,用色彩襯托環(huán)境,比喻簡潔、精準。“我”跟著設營員去村里找個下處住下時,“面前是環(huán)形村道,黃不棱登的,像南瓜”,“天上,奄奄一息的太陽正在吐出粉紅色的氣息”,“黃”、“粉紅”這樣的暖色調(diào)體現(xiàn)出“我”此時心情不錯,對融入即將面對的集體有著渴望與期待,而“我”聯(lián)想到的“像南瓜”反映戰(zhàn)爭帶來的饑荒、“貧乏”,與后文老婆子“一提吃的事兒,我寧愿上吊”遙相呼應。“我”明白戰(zhàn)爭的饑荒才會聯(lián)想到食物,而“奄奄一息”則暗示了“我”的期待若有若無、條件不容樂觀,美好事物也掩蓋不住災難感,表現(xiàn)對未來的擔憂。另外,環(huán)境描寫在情節(jié)前后的相互照應。“我”到哥薩克群體中卻倍受欺侮,想融入他們、把這兒當家,所以在他們煮豬肉時會想起遠方故鄉(xiāng)的炊煙,會“勾起了我孤身在外、饑腸轆轆的鄉(xiāng)愁”,而在“我”暴力殺鵝的“壯舉”后,卻覺得“月亮像個廉價的耳環(huán)”,看到的景物而聯(lián)想到的事物不同是由心境造成的,環(huán)境畫風突變的轉(zhuǎn)折襯托出“我”內(nèi)心的痛苦、委屈、絕望和艱難,后文“夜晚用它蒼茫的被單……發(fā)燙的額頭上”則表明了“我”精神上受到的傷害感和矛盾的心理。
場面構(gòu)置上,以小見大,開篇不直接描繪戰(zhàn)爭場面而以與師長見面、參謀長給團長的命令來交代戰(zhàn)爭背景,場面小中見大。另外,采用前后對比的手法構(gòu)置場面,殺鵝前構(gòu)置的場面是“我”初來乍到、文弱可欺、不入哥薩克們的眼,所以被嘲笑、欺侮、扔箱子、羞辱卻無可奈何,;而“我”兇暴“勇武”地殺鵝后,場面構(gòu)置就大不一樣的,哥薩克們對“我”的態(tài)度有了很大的轉(zhuǎn)折,認為“這小子跟咋們還合得來”,并叫“我”“老弟”,邀“我”一同進食,態(tài)度轉(zhuǎn)變的畫面極其諷刺,“英雄”如此欺軟“惜”硬,并以暴力血腥的行為為同類而無人道主義和愛心,這樣的場面構(gòu)置暗含著英雄主義的消解,“我”由被欺到融入并大聲念《真理報》說明殺鵝行為讓哥薩克們接納、認可了“我”,“我”得到了一張帶血的門票,前后對比的場面設置讓人心頭為之一顫。
參考文獻
[1]曾思藝. 試論《騎兵軍》創(chuàng)作的藝術(shù)特色[J]. 廣東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4,06:60-64+87.
[2]俞航. 空間的拼貼:巴別爾《騎兵軍》敘述結(jié)構(gòu)分析[J]. 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5,03:30-36.
[3]曾思藝. 對革命的中性藝術(shù)敘事——試論巴別爾的《騎兵軍》[J]. 邵陽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04:116-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