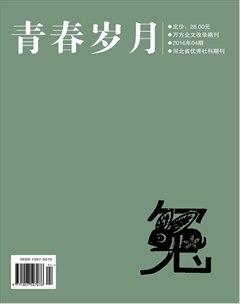譜一曲來世相約的亡音
彭伊樺
【摘要】《詩經(jīng)》中現(xiàn)存兩首悼亡詩,一是《邶風(fēng)·綠衣》,一是《唐風(fēng)·葛生》,此兩者開創(chuàng)先河,為悼亡詩之濫觴。本文通過對(duì)《唐風(fēng)·葛生》的分析來領(lǐng)略它的詩情魅力,體味古人樸素的愛情觀與纏綿悱惻的執(zhí)著,尋繹周人愛情之純潔堅(jiān)貞,伉儷相篤之深厚融洽。并試圖通過與后世文學(xué)比較,簡(jiǎn)要分析其對(duì)后世悼亡作品的影響。
【關(guān)鍵詞】詩經(jīng);葛生;悼亡詩;愛情
一、近在咫尺,生死永隔
日子真的慢起來,分分秒秒均是煎熬。阮籍問的是: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卻不知沒有盡頭的等,是會(huì)讓人發(fā)瘋的。葛藤覆蓋著荊條,蘞草長(zhǎng)滿山野,一位女子面對(duì)著亡夫的墳?zāi)箿I眼摩娑、低低哭訴:“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dú)處。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dú)息。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dú)旦。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后,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后,歸于其室。”這是迄今我們見到的最早的悼亡詩,講述的是一個(gè)癡情女子懷著濃濃相思不舍在亡夫墳前絮語。篇首以墓地所見荒涼之景起興,奠定了全詩哀怨凄楚、纏綿悱惻的悲涼基調(diào)。墳前的葛條蘞蔓,枝枝錯(cuò)錯(cuò)抵死纏綿,就像愛人那樣相依相偎,然詩中的未亡人卻形單影只,孤獨(dú)寂寞,好不悲涼。
安意如說:“中國(guó)最早的詩歌不是寫在紙上四平八穩(wěn)的,它們是被唱出來的,飛流而下地跌宕起伏,珠玉銀盤地清脆響亮。誠(chéng)然,一首《葛生》,三句詠嘆,“誰與?獨(dú)處!”“誰與?獨(dú)息!”“誰與?獨(dú)旦!”這一唱三嘆,將主人翁克制著的情感由弱轉(zhuǎn)強(qiáng),吟唱而出,悠悠夏日共愁長(zhǎng),茫茫冬夜心發(fā)慌。讓人體會(huì)到:孤獨(dú)本是兩面的,墳?zāi)瓜碌娜斯陋?dú)也就罷了,未亡者的孤獨(dú),該是分外的漫長(zhǎng)。這里的一唱三嘆仿佛是她守著孤墳時(shí)流下的淚水,沖刷著她自己的心壑,也祭奠著墳中的孤魂,其中該包含了多少死別恨、孤獨(dú)怨和相思情啊!在那個(gè)戰(zhàn)爭(zhēng)紛飛的年代,人的生命從來由不得自己掌控,多少家庭在戰(zhàn)火中分崩離析,多少離人的眼淚撒在飛揚(yáng)塵土之上。主人翁一面想象他枕著角枕,蓋著錦衾在荒野蔓草之下獨(dú)眠;一面自己傷感,想著未來漫長(zhǎng)歲月的可悲,惟有百年之后與良人同穴,才是歸宿。我的愛人葬在此,荒郊野嶺誰同住?我的愛人葬在此,荒郊野外灘同息?我的愛人葬在此,荒郊野外獨(dú)特已?
二、地老天荒,情重綿長(zhǎng)
姚際恒在《詩經(jīng)通論》評(píng)價(jià)“冬之夜,夏之日”此句甚妙,見時(shí)光流轉(zhuǎn)。生者始終沒忘記兩人的情義,不著思念之語,卻盡得思念之意。誠(chéng)然,冬之夜,夏之日,均為一年中最是漫長(zhǎng)的階段。詩人以兩段時(shí)間的相互交錯(cuò),極言時(shí)光流轉(zhuǎn)之漫長(zhǎng),歲月消失之不易。其實(shí)詩中后兩章不僅僅體現(xiàn)的是文字順序的顛倒,更是痛處達(dá)到頂峰后的一種升華,一種近乎感情上的瘋狂宣誓:生我為之守寡,死我與之同穴!“同穴共壙”是封建社會(huì)中夫妻愛情堅(jiān)貞如一、至死不渝的象征。然詩中未亡人她“百年之后”追求的卻不是與他“同穴共壙”,而是和他“同室共居”,期待百年之后回到他的身邊共同生活。四言一句,簡(jiǎn)練純凈,反復(fù)詠嘆,唱出心底最執(zhí)著的眷戀,極言兩人伉儷情深,細(xì)刻出了她和丈夫雖已人鬼異處但仍一往情深的真摯感情。
多么古典又多么深沉,這其實(shí)是一種眷眷的愛。予美亡此,誰與獨(dú)處?百歲之后,歸于其居。即使生時(shí)無法相守,哪怕是死后尸骨的相見,亦是一種慰藉。“夏之日,冬之夜”深情,死生也無法隔絕,為了那種深刻的愛戀,應(yīng)許這夏日冬夜的漫長(zhǎng),無怨無悔的守候與篤定。如此平靜又如此厚重,從容得連死生都不在意。我可以不求死生同存亡,不哭天搶地,而是深情宣誓:我的心不會(huì)因多活于人世的短短數(shù)載而曲變,即使百年之后也仍能為你跳動(dòng),與你同在;我可以照常地生活,我可以閑看庭前花開花落,漫觀天邊云卷云舒。我可以看山戲水逗閑云,偷得浮生半日閑;我可以看日升月落花燃河山,我可以自己一個(gè)人走過現(xiàn)世安穩(wěn),歲月靜好;我可以連同你的生命一起活下去,即使城樓西斜,月光潸然。你,一直與我同在。夏日冬夜的更迭是生命的程,百歲之后的回歸則是又一次生死相許。沒有戲劇性的情節(jié),沒有生前卿卿我我的回憶。死,到此時(shí)成了一種感情的信念,成了重相廝守的希望。一如《葛生》中的那個(gè)女子,冬夜漫漫,夏日燦燦,待到百年后的再同穴而居,也沒有什么不可,心中摯愛也分毫未改。
三、傷逝惜別,堅(jiān)貞哀婉
《葛生》可謂悼亡詩的濫觴,然“悼亡”命名,卻自西晉潘岳始。悼亡詩在唐人中,以元鎮(zhèn)的《遣悲懷》七律三首和《離思》七絕五首最有名。詞人中,則以蘇軾和納蘭性德為冠。
悼亡詩詞感情真摯,情辭哀婉,感人至深。《葛生》中的“葛生蒙楚,蘞蔓于野”,在篇首以墓地所見荒涼之景起興,奠定全詩哀怨凄楚、纏綿悱惻的悲涼基調(diào)。潘岳《悼亡詩》:“如彼翰林鳥,雙棲一朝只。如彼游川魚,比目中路析。”使用比、興的手法,將夫妻二人比作翰林鳥、比作游川魚,以比目魚的撕裂謂夫妻生離死別。在《葛生》中,詩人面對(duì)“其室”、“其居”,想到“角枕燦兮,錦衾爛兮。”此乃觸景傷情。蘇東坡《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以墳?zāi)箒砑耐嘘庩栂喔舻陌肌!陡鹕分小鞍贇q之后,歸于其室”也表達(dá)詩人渴望于死后相遇,再續(xù)前生未了緣的愿望。納蘭性德《金縷曲·亡婦忌日有感》“待結(jié)個(gè)、他生知己。還怕兩人俱薄命,再緣慳、剩月零風(fēng)里。”就是難抑對(duì)亡妻的思念,想跨越今生來世的鴻溝的傾訴與表達(dá)。
然,詩經(jīng)中的文字魅力,不僅在于值得回味的意蘊(yùn)雋永,不僅在于對(duì)后世的詩文影響,更多的是力透紙背的真摯情感。這些被吟詠著的充滿血淚的哀歌,其力足以穿透血肉,凈化人的靈魂。這種感染力,來自上古人民的真情實(shí)感及其古樸的生活情趣,自其纏綿徘惻的情思和深沉的抒情格調(diào),那些至死不渝的愛情絕唱,可以穿越時(shí)空穿越人心穿越一切隔閡,成為人們心中的夢(mèng)想與期許。反觀現(xiàn)代社會(huì),處處充斥著:只求曾經(jīng)擁有,不求天長(zhǎng)地久的“速食愛情”,寧愿在寶馬車?yán)锟蓿辉冈谧孕熊嚿闲Φ摹拔镔|(zhì)愛情”,各種婚戀網(wǎng)、婚介所、三姑六婆極力撮合,生拼硬湊的“絕配愛情”。這些所謂的速食愛情、物質(zhì)愛情、絕配愛情,將千百年來祖先流傳的關(guān)于愛情海枯石爛堅(jiān)貞不渝的信仰擊得粉碎,在不再單純的愛情追逐之間,在形形色色的愛欲糾纏之間,我們的心中是否還有“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zhí)子之手,與子偕老”的信念與堅(jiān)貞?是否還有“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后,歸于其室。”的情深守望?
【參考文獻(xiàn)】
[1] 程俊英. 詩經(jīng)注析[M]. 北京:中華書局, 2006.
[2] 余冠英. 詩經(jīng)選[M]. 人民文學(xué)出版杜, 1979.
[3] 姚際恒. 詩經(jīng)通論[M]. 中華書局, 1958.
[4] 全宋詩[M]. 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 1991.
[5] 全唐詩[M]. 中華書局, 1999.
[6] [清]納蘭性德. 飲水詞箋校[M]. 中華書局,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