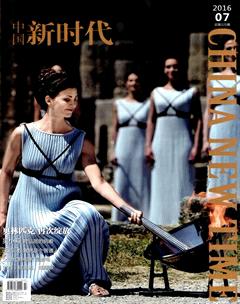父母代替相親 靠譜嗎
王志琴
為了幫助子女早日完成結婚這件人生大事,父母們可謂想盡了各種辦法,代替子女相親就是其中一種。
2016年6月3日,來自《北京青年報》的一條新聞吸引了眾多人的目光,標題為“父親代替兒子相親 見10個對象花掉13萬”。文中講述了安徽人王先生代替大兒子到廣西相親,一星期見了10個相親對象,前后花費13萬元,而被王先生看中的那名女子,卻涉嫌騙婚,讓王先生欲哭無淚。之所以會去代替兒子相親,是因為王先生的兒子交友圈子窄,兩個兒子都沒對象,王先生心里特別著急,于是南下去相親。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無論是在古代社會還是現代社會,婚嫁都被當作一件大事。而相親,是婚嫁之前作為男女雙方了解對方的一個重要環節。
相親禮俗由來已久。在我國古代,男女結婚要經媒人說合,說合后,男方往往提出看一看的要求。這種男方在媒人的帶領下到女家作初次訪問的活動,稱之為“相親”。
相親禮俗起源于擇婿。父親看到某個青年男子各方面條件不錯,有意將女兒許配給他,便主動談及婚事。春秋戰國時,史書開始載有擇婿之事。到了漢魏六朝,擇婿禮俗十分盛行。漢高祖劉邦即是呂后父親呂公親自挑選的女婿。到了明清,相親變為專門相看當事人。
1919年五四運動后,城鎮進步青年受新思潮影響,向往自由婚姻,出現以感情為基礎的自由戀愛和自主婚姻。新中國建立以后,年輕人的婚姻自由更是受到法律保護。人們不再要求女性“大門不出二門不邁”,也不再提倡包辦婚姻。按說在這樣輕松的氛圍里,無論男女,找到合適的另一半應該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事實并非如此,大齡適婚男女的婚姻問題成了一個社會熱點問題。
據北京市統計局、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公布的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顯示:2015年,男性占大齡未婚群體的55%,未婚男性更多集中在農村。而大齡未婚女性有92.5%集中在城鎮。不僅在我國,其他國家的大齡青年也在為婚姻問題發愁。2014年,新加坡男性首次結婚的年齡中位數從2005年的29.7歲推延至30.2歲,女性從26.8歲推遲至28.2歲;而韓國2014年的數據顯示,當地男女分別在32.4歲和29.8歲結婚,結婚年齡較10年前推遲約2年。在這樣的背景下,相親又流行了起來。
對于相親這種行為,不少人表示理解,認為這是一個可以牽線搭橋的方式。在他們看來,相親就是“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甚至你所認識的人里沒有出現合適的人的時候,別人從另一個圈子給你拉一個人進來而已”。
在這個層面上,相親是必要的。男女雙方面對面相親無可厚非,因為相親可以讓兩個人都能認識對方,給雙方提供一個了解的機會。喜歡就繼續發展,不喜歡的就不再聯系。
然而,另一種方式——父母代替子女相親,就顯得不那么受子女歡迎了。近幾年,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武漢以及其他大中城市里,每到周末,在一些人氣很旺的公園里就會看到許多父母聚集在那里,代替子女相親。這些父母以“50后”“60后”為主體,他們的子女則主要集中在“70后”“80后”和“90后”這幾個年齡段。
為了幫助子女早日完成結婚這件人生大事,父母們可謂想盡了各種辦法,代替子女相親就是其中一種。在諸如周末、節假日這樣固定的日子里,父母們會在公園里占據一個位置,每個位置前面,擺放的是一張張展示單身青年男女信息的資料,詳盡交代了年齡、身高、學歷、工作、月薪、房產以及擇偶要求,有的還寫明了父母的聯系方式,甚至附上了孩子的照片。通過篩選辨別其他人的信息和與其父母交談的方法,父母們會幫兒女們找到他們比較滿意的對象。
談起代替子女相親的原因時,這些父母的回答可以歸結為兩點。第一,現代社會中,子女忙于打拼事業,工作壓力太大,周末加班的大有人在,經常出差的也不在少數,沒時間自己去相親。第二,子女的社交面窄,沒有機會接觸異性。
同時,當下擇偶的結構性失衡,也使人們感覺社會上“剩男剩女”越來越多。而上述這些原因,使得一部分父母越來越焦慮,為了子女的幸福考慮,他們自發組織起來,代替子女相親。
相親過程中,父母遇到自己心儀的對象后,就會相互交換手機號、QQ、微信等聯系方式,通過網絡讓彼此有了初步的了解后,再由子女們決定是否見面,繼而進一步發展。
只是,不少父母都是背著子女來的,孩子因為種種原因還沒對象或者不想結婚,而當父母的卻在背后著急,于是就利用周末的時間,親自上陣,為子女挑選對象。如果遇上不錯的適婚對象,他們會對子女說是通過朋友介紹的。因為對這種相親方式,很多子女們并不贊成甚至激烈反對。
父母的苦心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這樣的相親方式真的有效嗎,能為子女找到合適的另一半嗎?由于初次見面,且當事人缺席,父母們無法對對方子女的性格、品行等方面進行判斷,只好從一些硬件上進行匹配,包括學歷、工作、收入等方面,婚姻變成了雙方父母的選擇和博弈,成了赤裸裸的“拼條件”。在和對方父母的交流中,父母們更看重對方的家庭條件,其中子女的外貌、年齡、職業、收入、戶口、住房、婚史、屬相等以及父母自身的形象資本、社會地位、經濟資本、家庭支持網絡成為了重要的考察內容,而人品、性格、興趣愛好、共同的價值觀等原本應該更加重視的問題反倒被忽視了。
父母的出發點是好的,畢竟逼著子女去相親容易引起他們的反感。也正因如此,父母充當孩子的“代理人”,幫兒女物色合適的對象便成為父母關愛子女的一種方式。
但問題在于,父母即便找到了他們覺得合適的人選,但對兒女的婚姻究竟有沒有幫助,幫助有多少呢?就算父母對自己看中的人選特別滿意,但如果當事人自己不滿意,父母的心血就白費了。更重要的是,當許多父母對兒女的婚事大包大攬時,并沒有考慮到子女真正的需求,強行匹配甚至會引起兒女的反感。
而且,美滿的婚姻是建立在雙方的感情基礎上的,而對于這一點,“代替相親”的父母卻無法幫子女抉擇。父母的焦慮和心急想必子女們都明白,但感情這件事卻不是旁人可以感受或者代勞的,以自己的幸福標準去幫子女匹配另一半這種做法顯然有失穩妥。
因此,在婚姻大事上,父母代替子女相親這種擇偶模式,究竟合不合適,還要打上個問號。
專家觀點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孫沛東:“白發相親”,一方面的確擴大了可選擇的范圍;另一方面,也使父母們容易產生“吃著碗里看著鍋里”的心理。他們的行動看似積極,心態上卻是只求最好,這反而降低了成功率。經常有父母抱怨子女眼光太高,其實是他們自己有時太過理想化。對兒女的感情投射使他們就像拿著一面放大鏡,不自覺地放大自己子女的優點、優勢。
陜西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謝雨鋒:相親這種方式是比較傳統的擇偶模式,給適婚年齡的青年們提供了一個相識的機會,本身這種方式并沒有問題。之所以現在一些條件不錯的女性難找對象,主要還是“定位”不清。
南昌市社科院社會學所副所長戴慶鋒:父母代相親是一種無奈但現實的行為。一方面父母對子女婚戀的急切,使得他們不得不越俎代庖式地代子女相親;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當前中國婚齡青年因各種原因無暇顧及婚姻的無奈。婚姻對象還是婚齡青年親身經歷之后,才能有最佳的衡量。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講師秦國偉:對于現在各種相親活動,如非誠勿擾,如富豪相親,如公園相親,要區別對待。對于公園相親,反映了我們當前婚姻選擇的艱難,父母上陣一定程度上損害了青年人的婚姻自主權,是不值得提倡的。但對于已經被險峻的生活逼得沒有出路的青年人來說,這不失為不得已的選擇。說到底,我們現在講中國夢,找到一個對的人結婚是每一個人心中的夢,但這個夢現在卻難圓,電視相親、富豪相親和公園相親對圓這個夢都收效甚微。
河北省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周偉文:“白發相親族”現象并不存在于短期,而是長期以來在全國范圍內普遍出現的社會現象。而這一現象正從一線城市向二三線城市下沉,隊伍不斷擴大。這與當前社會轉型背景下“70后、80后”成長的特殊經歷有關。從青年人角度而言,“70后、80后”長期處于“被選擇、被安排、被人生”的成長環境中,存在心理與生理年齡不符的現象。他們面對壓力難以做出正確選擇,對父母產生“選擇性依賴”。這與“50后、60后”父母“包攬式”教育有直接關系。
大齡青年心聲
趙先生:我今年29歲,在一家媒體從事設計工作。我感覺愛情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不熱衷通過相親尋找另一半,也不同意“父母代相親”。我能理解那些代子女去相親的父母,但我認為這種方式帶給年輕人的壓力會更大。我的父母就很好,在感情上一直尊重我的選擇。今后我即使嘗試相親也會自己親自去,因為兩人之間的感覺最重要。
張小姐:我今年29歲,在私企工作,月薪3000元,我比較贊成父母代相親。我26歲研究生畢業之后,來到這家私企工作,總覺得找個離家或離單位比較近的男朋友才現實。可我平時工作忙壓力又大,每天晚上到家都七八點鐘了,好不容易有個周末也只想在家休息。就這樣,我邁進了大齡青年的門檻。我覺得父母閱人無數,經驗豐富,由他們幫忙找女婿,不僅能為我提供更多的異性信息,還可以減少今后的家庭矛盾。
何先生:參加相親活動,就應該是以誠相待,男女雙方相互見面,大家第一印象感覺合適了,就繼續交往,嘗試著往深一步發展。如果連相互見個面都要由家長代勞,這個誠字又從何談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