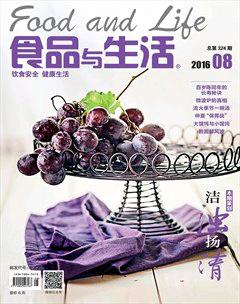老大同的“家”(二)
周彤
公私合營后,老大同醬園遷到了不遠的廣東路233號,并更名為“上海老大同油醬店”。歷經幾十年的發展,此時的老大同香糟早已在業內成為本幫菜的一種秘密武器了。而它捧紅的最著名的一家餐館,就是本幫菜四大名店之一的“同泰祥酒樓”(另三家是“榮順館”、“德興館”、“老正興”)。
1976年,高中畢業的王浩秋被分配到“上海老大同油醬店”。“文革”過后的上海人對于城里老字號“單位”的重視程度是今天的人們很難想象的。王浩秋在這里“學生意”很賣命。
1954年開始的公私合營,是解放后中國對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所采取的一種方式。簡而言之,當家人是“公家”的,但以前的老板作為“資方代表”可以享受較高的工資和股份分紅。
認認真真的王浩秋很快發現,這家老字號中,真正掌握技術核心的都是單位里謹慎寡言的“資方代表”。
香糟的生產工藝看起來很簡單,將酒廠的黃糟運來,拌上老曲引子,再加上磨碎的香辛料,一起攪拌均勻后,封進小口的陶壇子里,陳放兩年就可以了。
但細細推敲下來,這里每一步都暗藏玄機。
比如酒糟是味道的底坯,原料酒糟不好,香糟根本出不來,而原料糟是與黃酒廠的生產工藝分不開的,所以要做糟,先得懂做酒。
比如作為發酵種子的老糟曲種與原料糟的配比是多少,一定要把握“輕酵慢漲”的原則,也就是說不能放得太多,要在確保全部香糟發酵的前提下,盡量少地用老糟曲。
再比如香糟味型的點睛之筆是中藥香料配方,香料可以多一味,也可以少一味,比例可以多一點,也可以少一點,就像炒菜時放的鹽和糖一樣,有一個寬容的范圍,但一定有一個最佳的比例。這個比例老師傅一般是不外傳的,能夠傳給你的比例也能用,但往往少了一口味道上的神韻。
王浩秋是高中畢業生,在恢復高考前的1976年那會兒,他幾乎算是單位里高學歷的知識分子了。但他也是一個有心人,這一點他秉承了老一代上海技術工人的優良傳統——踏實認真、刻苦鉆研。
隨著老一代師傅們的退休,王浩秋成了廠里為數不多的掌握香糟生產全部技術核心機密的人。但是,這又有多大的“用處”呢?
1993年,改革開放后的上海顯然已經容不下鬧市區里放著這么一個醬園子了,老大同搬到了青浦縣趙巷鎮,名字也改為“上海老大同調味品廠”,王浩秋任廠長。
此時上海的餐飲市場已然發生了一系列新的變化:房租水電等固定成本節節攀升,但本幫菜的生產效率和菜肴利潤卻上不去;廚師的手藝越來越速成化了,敬業精神和創新意識越來越弱,但脾氣和工資卻上去了;由于城區黃金地段價位的不段攀升,城市化改造實際上演變成了現代工商業對傳統服務業的格式化改造。
不知不覺中,上海的餐飲業也在進行著某種“格式化”:高檔化菜肴一定比實惠化菜肴賺得快;快餐化飯館一定比手工化飯館混得好;“添加劑廚師”一定比“老手藝廚師”吃得開。
“同治老正興”、“源記老正興”、“一家春”、“同泰祥”等一大批老字號本幫菜館紛紛消失了。
王浩秋的地盤比原來更大了,但老大同香糟的銷路卻比原來更差了,這是王浩秋無能為力的。
更麻煩的還在后面。香糟生產本來是一種根據傳統經驗試制出來的調味品,如果要擴大銷路,顯然使用起來更為方便的香糟鹵比需要再次加工的香糟泥更好賣。
要把香糟泥加工成香糟鹵,技術上一點不難,只需要在香糟泥里兌點黃酒和水,入味以后再濾掉糟渣雜質即可。一包香糟泥市售5.5元,一瓶上好的陳年黃酒市售18元,加工出的糟鹵本應比黃酒更貴才對,但現代食品工業的“技術”,可以使一瓶香糟鹵僅售5元。
如果王浩秋也想做香糟鹵的話,那么他的產品得過幾道指標關,比如酒精度含量≥1.5;總氮含量每100毫升≥0.18克;污染物、真菌毒素、微生物含量也有相應的限量等。這些林林總總的檢測指標幾乎意味著香糟鹵最重要的市場通行證。
但就像如今的高考一樣,5元錢一瓶的香糟鹵成了業內人人皆知的、味道上的“高分低能”者,它當然還是香糟鹵,但那種四平八穩的香型是完全不可能讓當年的杜月笙魂牽夢縈的。比起“歐、顏、柳、趙”來,印刷體的“楷書”更“科學”和“規范”,但印刷體的“楷書”卻沒有“味道”了。
從監管部門的角度出發,出臺這樣的管理規定是無可厚非的,畢竟沒有規矩市場會更亂,但這種只認硬指標不認軟文化的“科學”態度是存在著明顯漏洞的,因為它換了一種方式更為直接地宣判了傳統風味的死刑。
尊重科學與尊重文化是彼此矛盾的嗎?以物為本的“標準”一定高于以人為本的“規矩”嗎?沒有人回答這個問題,或許這個問題真的“很傻很天真”吧!
2013年10月,老大同在青浦的租地合同到期了,趙巷鎮也對這塊地皮有了更具“發展前景”的規劃。于是,這個上海最地道的糟香風味生產基地從此不得不搬出上海。而此時,王浩秋本人已經58歲了,再過兩年,他也得退休了。
后 記
老大同現在搬到了蘇州市吳中區甪直鎮,算是回到了它的蘇州老家。但如今蘇州的發展步伐也挺快,香糟這一傳統調味品到了蘇州也還是沒有什么“錢途”的,這里會是本幫香糟最后的“家”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