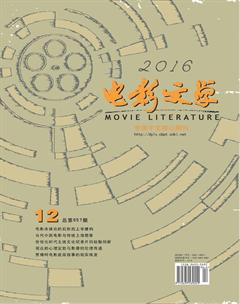觀眾“期待視野”與科波拉的電影創作
李新紅
[摘要]在胡塞爾、海德格爾提出“視野”相關概念的基礎上,姚斯進一步創造出文學接受理論的新概念——期待視野。從“期待視野”角度看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的影片,可以更清晰對比出其在原著基礎上的創造性改編,他不止一次地給觀眾帶來不可思議的驚喜。科波拉影片從來都不是按照原著按部就班的線性發展,從觀眾“期待視野”出發,科波拉的成功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即劇情改編與原著的離合,人物特性的重新塑造,戰爭與人性命題的延伸思考。
[關鍵詞]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電影;期待視野
在胡塞爾、海德格爾提出“視野”相關概念的基礎上,姚斯進一步創造出文學接受理論的新概念——期待視野,即讀者在閱讀文本之前,本能地對作品有個人化的提前設想,設想與文本之間的“游離”成為評價作品成敗的重要標準。從“期待視野”角度看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的影片,可以更清晰對比出其在原著基礎上的創造性改編,他不止一次地給觀眾帶來不可思議的驚喜。科波拉影片之所以被稱為“再創作”,是因為他從來都不是按照作品原著按部就班的線性發展,總是以自己個人的理解對作品重新解讀,既而在電影中以他所理解的樣子拍攝制作。對于一部作品,“作者未必然,讀者未必不然”是無可厚非的,但在觀眾眼中,得知改編某部作品后,他們了解的基本輪廓和想象空間大都局限于小說本身,而科波拉指導的系列影片是超脫于小說之外的獨立創作,這勢必造成觀眾“期待視野”與實際狀況的巨大反差,反差空間越大,意味著導演融入的自我因素越多,給觀眾帶來的驚喜也越大,傳達的信息量當然更加超越文本。所以,人們常常毫不掩飾地用貶低文本作品的卑劣來凸顯科波拉影片創作的成功。若單從觀眾“期待視野”角度出發,成功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即劇情改編與原著的離合,人物特性的重新塑造,戰爭與人性命題的延伸思考。
一、劇情改編與原著的離合
科波拉的成名劇作是根據《巴頓:磨難與勝利》和《一個士兵的故事》兩部回憶錄改編的《巴頓將軍》。將學界對影片的觀點大體分類,不難發現影片改編成功的訣竅是:既符合歷史又有諸多細節性的合理新變。眾所周知,劇本決定影片基礎的靈魂,在耳熟能詳的歷史基礎上既能充分表現人物個性,又能帶來耳目一新的“陌生化”,是劇本改編的最高追求,科波拉創作電影的核心價值亦在于此。排除因為生計原因而不得不接手的低質量“違心產品”,其電影生涯中,值得稱道的無不是經過自己深思熟慮后的改編之作,如《教父》三部曲、《現代啟示錄》《伊奧船長》等。改編就必然與原著之間存在或多或少的“離合”,離合主要有兩個方向,一是劇情的調整,二是人物形象的重塑。調整的內在邏輯是否合理,重塑形象是否巧妙都是放在與原著的對比中來感知的。因此,對比是把握觀眾“期待視野”的內核。
第一,情理之中的巧妙融合。小說文本是線性的描述,盡管有插敘、倒敘、補敘等不同的創作手段,但與直觀的視覺影像相比,它無法做到“蒙太奇”式的剪輯和“隨心所欲”的場景切換,這就需要編劇者對文本采取整合。面對歷史真實題材的《巴頓將軍》,科波拉并沒有像“歌德”派那樣站在美國政府和軍隊的立場上,一味地“粉飾”;當然也不是以反對戰爭、歌頌和平的批判態度抹殺巴頓的功績。而是結合兩部回憶錄,做情理之中的巧妙融合,一方面通過幾個細節來塑造巴頓在軍隊中特立獨行、嚴厲苛刻的個性。如第一次被安排到北非部隊后,看到士兵們在正常值班時間,個個沒精打采,不是睡覺,就是玩游戲,從底層到干部,毫無美國大兵的氣勢,難怪在第一場與德軍的遭遇中就敗得一塌糊涂。巴頓對此深惡痛絕,在沒有獲得參議院通過的情況下,就讓手下將將軍的星標戴在領前,在副手布萊德雷看來真是膽大妄為。同時,他已開始著手整肅軍紀,重塑美軍剛強意志,其要求苛刻,甚至“關心”士兵的衣襪整齊與否,乃至不放過一個懦弱的神情。另一方面選取幾段富有深意的對話來表現巴頓對政治的無知,他僅僅是一位“戰場的神話”。在以24小時行軍100公里的“神速”下,他順利渡過萊茵河,攻克德軍的重要防線巴勒莫。但隨即又信口開河發表非議蘇聯的言論,導致自毀前程。科波拉心目中的巴頓與《亮劍》中的李云龍有神似之處,這一形象在《巴頓:磨難與勝利》和《一個士兵的故事》中是不明顯的。
第二,意料之外的劇情調整。創作型導演科波拉不唯對材料選擇有著犀利的眼光,在劇情設置上也表現出高人一等的魄力。文本中的普通情節一經他改編,即刻變得扣人心弦,這就是與觀眾“期待視野”產生良性反差后帶來的正面效應。康納德《黑暗的心》本是以非洲大陸熱帶雨林為發生環境的架構,科波拉在改編過程中為了與時代接軌,將非洲改為亞洲,將戰場移至越南柬埔寨,瞬間將《現代啟示錄》與美國政壇的軍閥斗爭相結合,政治敏感性極大地拓寬了這部電影的敘事空間。人們并不感到這樣的改編會影響康納德小說的主題,反而覺得是劇情的調整挽救了小說文本的乏味。同時,科波拉深刻明白威爾德小分隊追殺庫爾茲的歷程正是認識自我、反思戰爭的影射,只是在康納德筆下,這一隱性反對非正義戰爭、批判政府功利主義的“算盤”被科波拉不失時機地放大,以至于影片殺青后,被影視部門強行勒令刪去近一個小時的篇幅。其“反政府”的言論,使人們不禁懷疑這是否真的出自美國導演之手。正因為秉持自由思想、獨立人格的信念,數年后全劇才得以面世的《現代啟示錄》被公推為不可多得的“史詩巨制”。科波拉意料之外的劇情調整將《黑暗的心》送上美國圖書暢銷榜,當然更多的人還是認為影片取得的成就遠遠超過文本。
二、人物特性的認知與新變
科波拉有著坎坷的人生經歷,20世紀80年代,他在拍攝《現代啟示錄》過程中遇到諸多磨難,以致長期拖延,后果是“年輕”的工作室倒閉,并背上數百萬元的沉重債務,且遭遇家庭婚姻危機。慘痛的經歷磨平了他創作的“棱角”,現實的逼仄“強制”他收斂年輕時的鋒芒,但一位天才創作導演是不甘于僅僅在“俗套”中徘徊的,追求創新依然是其不變的動力。尤其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科波拉表現得異常“任性”,從上文談及的“戰爭神話”巴頓,到秉性截然不同的教父科里昂和麥克,再至成長中追問自我的威爾德和庫爾茲,他都是在以自己的人生體驗和感悟來塑造人物特性。因為感同身受,所以各種人物形象都在小說基礎上打上了科波拉自身的情感烙印。
首先,傳承與新變。馬里奧·普佐的《教父》是在債務危機情況下憑借個人喜好與市場營銷策略而簡單創作的,若說真正為其奪得“頭號暢銷書”的并不是作者本人,而是科波拉完美的改編。《教父》1、2的成功固然值得稱贊,但與《教父3》相比,后者對觀眾“期待視野”的沖擊更大。這得力于科波拉對教父形象的傳承與新變,如果第三部仍然是在溫文爾雅、悲天憫人與深謀遠慮的維托·唐·科里昂角色中掙扎,審美疲勞的觀眾并不會為《教父3》買賬,著力于新變的科波拉也不會為此重操舊業。邁克.科里昂的特殊就在于他與父親有著截然不同的心狠手辣,又有兩位哥哥不具備的智謀,但又對黑手黨炙手可熱的權力和事業不感興趣,他并不是利益崇拜者,也不是權位的奴隸。面對黑道代表素洛佐和政府化身的警長的雙重威脅,邁克毫不客氣地將其擊殺,面對卡洛的“吃里爬外”和法布里奇奧的殺妻之恨,邁克埋藏于深處的血腥終于被完全激發,當冷峻的他肅清家賊,平定叛亂,榮升為新一代教父時,我們看到了維托·唐·科里昂的身影,只是比后者更加“殘忍”。但當看到邁克對家庭、妻子如此的深愛,以及甘于放下一切,過平靜的生活時,“教父”的形象在邁克身上再次升華。傳承和新變是科波拉影片超越觀眾“期待視野”的秘訣。
其次,成長與認知。團隊系列在美國電影中占據重要位置,從《變形金剛》系列中不同身份和功能的汽車人,到《速度與激情》系列中不同任務分配的組合,乃至《復仇者聯盟》《X戰警》等都存在一個配合密切、形象各異的優秀團隊。其實早在30余年前的科波拉時代,團隊就已經被搬上大銀幕,只是與后期“英雄”主義形象不同。在《現代啟示錄》中,威爾德團隊的塑造是一段成長與認知自我的過程。隊長是唯一一個有著明確信念的軍人,但這是建立在美國政府“洗腦”基礎上的,代表國家形象最“完美”又極脆弱、矛盾的典型,他認真履行軍人的職責,卻并不知道已經失去自我,淪為別人的工具。上尉威利、蘭斯和大廚三人面對戰場皆是困惑的,除了服從命令,他們不知道身為軍人到底要干什么。參軍使威利失去家庭,大廚失去夢想,蘭斯失去生活樂趣,尋找庫爾茲是這些困惑者的成長歷程,在一步步靠近最后目的地時,他們的自我認知得以完成,四人的不同結局即是明證。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成長過程何嘗不是科波拉認知自己的注腳?最震撼的莫過于威爾德的經歷,目睹戰場的殘忍和可怕后,他成功擊斃庫爾茲,但不幸的是他已然成為另一個“庫爾茲”。科波拉在塑造團隊組合時,極力地去挖掘他們內心的真實聲音,并以團隊“解散”的結局昭示認知的成功,他在威爾德與庫爾茲之間悄然畫下的“等號”,使文本中兩個貌似不同的形象產生了本質的關聯。
三、戰爭與人性命題的延伸思考
改編與創作的支撐點是導演對整部作品中心的把握以及影片主題的再思考。就科波拉執導的影響最大的《現代啟示錄》和《教父》而言,戰爭與人性的反思是其努力追問的深層命題。
先說戰爭的意義。對美越戰爭的反思是導演對這一命題的延伸解讀,他借庫爾茲脫離美軍,建立獨立王國的故事告訴我們,戰爭不是解決糾紛的良好途徑,甚至是罪惡的深淵。正義的戰爭是體現一個民族堅強意志的“名片”,但20世紀四五十年代,美國政府一味推行的“正義”戰爭不過是部分軍閥主義分子的個人意愿,是另一種殖民主義的推廣。深受其害的美國大兵不知道自己為何而戰。巴頓將軍剛進入北非戰區時,軍隊紀律的渙散其實正是士兵困惑的直接表現,而巴頓不惜犧牲大量士兵的生命換來成功登陸的舉止,已經明白道出“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殘酷現實。威爾德團隊成員的迷惘同樣在詮釋所謂“正義”之戰的扭曲。倒是庫爾茲的脫韁和自我覺醒,在試圖告訴我們,非正義的戰爭所帶來的后果不僅僅是越南人民的堅決抵抗,更可怕的是本國軍隊的人心渙散和迷失自我。
再說人性黑暗的探尋與揭露。康納德《黑暗的心》本身就有著現實與象征兩個層面的寓意,一是現實中戰場硝煙下的黑暗,二是利欲熏心的人性“黑暗”。科波拉敏銳地把握住小說兩大寓意,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深挖人性迷失的根源與生命存在的意義。作為美國軍人典型的威利上尉,他一方面想早日結束戰爭,回到寧靜、和平的正常人生活狀態,恐怕這也是每一位士兵的真實心聲;另一方面,當他們回到“田園般”的靜謐后,卻發現自己的心仍在戰場上,似乎唯有完成艱難的任務和沖鋒陷陣的廝殺才足以實現其自我價值。不可調和的矛盾背后是士兵人性的迷失,他們在不知不覺中被灌輸為正義的化身,從來沒有捫心自問到底需要什么樣的生活,其所作所為是否合情合理。與此相比,縱使《教父》中邁克多么殘忍,但他并沒有在錢、權、色等欲望驅使下失去理性,并且他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這或許是身為“教父”的真正價值和意義。
從觀眾“期待視野”角度出發,可以充分展現科波拉電影中的“創作”閃光點,不難發現,其創作成就的取得與不甘“俗套”的雄心是分不開的,除了影戲層面劇情、人物塑造等技術性調整之外,在電影史乃至文化史上,應該重視其對戰爭和人性命題思考的現實意義和藝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