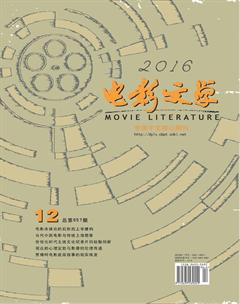英美恐怖影片中的畸人形象
石江澤 吳東敏
[摘要]盡管各國的恐怖影片在具體恐怖元素的表現形態以及各元素背后的文化意義上有所區別,但是在人物塑造上,有意打破觀眾所熟悉的生活秩序這一點卻是基本一致的。由此,恐怖影片中出現了“畸人”群像。尤其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較為流行,后現代主義思潮的起源地英美地區,銀幕上的畸人形象更是層出不窮。文章從外形怪異的畸人形象、心理扭曲的畸人形象、舉止古怪的畸人形象三方面,分析英美恐怖影片中的畸人形象。
[關鍵詞]英美電影;類型片;恐怖片;畸人
盡管各國的恐怖影片在具體恐怖元素的表現形態以及各元素背后的文化意義上有所區別,但是在人物塑造上,有意打破觀眾所熟悉的生活秩序這一點卻是基本一致的。由此,恐怖影片中出現了“畸人”群像。所謂畸人指的便是擁有異于常人的外表或精神世界,或是表現出種種怪異的行為,并且在某種程度上能夠給其他人帶來傷害之人。尤其是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較為流行,后現代主義思潮的起源地英美地區,銀幕上的畸人形象更是層出不窮。盡管非英美地區同樣涌現出了不少經典的帶有畸人形象的恐怖電影,如加拿大影片——大衛.柯南伯格的《靈嬰》(The Brood,1979),德國影片——湯姆.提克威的《香水》
(Perfume:the Story of a Murderer,2006)等,但是其文化源頭依舊是可以追溯到英美的。且無論就數量抑或質量而言,英美影片中的畸人無疑都更為全面,也更具代表性。對這些畸人形象進行剖析,能夠使人對英美恐怖影片有著更為透徹的理解。
一、外形怪異的畸人形象
畸人的反常之處往往并不僅僅體現在外表或心理上,并且就電影而言,由于要以畫面呈現的方式讓觀眾直觀感受到畸人之“畸”,因此畸人們的變態、怪異往往也會體現在行為之中。從電影的表現重點以及觀眾最直接的觀感上來說,英美恐怖影片中的畸人之畸是各有側重的,可以用外形、心理與行為來分別論述,但并不意味著這是一種絕對的劃分方式。
外形怪異的畸人形象能夠直接將畸人從普通人中區分開來,使觀眾一目了然,同時,從心理學的角度而言,人在面對自己所陌生的事物時,其產生的恐懼感往往要高于其面對熟悉事物之時,外形與正常人大相徑庭的人物形象,尤其是當這種與正常的區別主要在于角色的丑陋和丑惡時,人物形象能夠刺激觀眾的視覺,激發起觀眾警惕、害怕的情緒。但另一方面,外表的丑陋或怪異并不代表內心的扭曲,一部分畸人實際上擁有著與普通人毫無二致的情感、思維乃至道德觀,甚至有人始終沒有放棄對于來自正常人的愛與理解的信奉和追求。影片的震撼之處由此而產生,畸人本身的外貌就足以給觀眾帶來沖擊,畸人正常的內心又有著愛、自尊等需求,但畸人有可能也正因為種種難以融入主流社會的外表而讓人忽視了他們內心美麗、正常的一面。當所謂的正常人陷入畸人所制造出來的困境中時,也應該為他們曾經對待畸人的態度而有所反思。
早在20世紀30年代,托德·布朗寧執導的《畸形人》(Freaks,1932)就曾引起了巨大的爭議,該片也可以視作是畸人形象的發軔之作,同時又是外表畸形的畸人集大成之作。影片的主人公們幾乎全部為馬戲團中的畸形人,如侏儒、沒有四肢的人、連體兩姐妹、沒有下肢的人、長胡子的女人等。由于他們大多無法如正常人一般勞動,因此被作為獵奇的對象在馬戲團演出,他們是馬戲團老板的搖錢樹,而觀眾對于他們也只有好奇或憐憫,而并無平等相待的意愿。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就沒有單純而渴望美好事物的心靈,只是他們畸形的外表阻礙了他們向美好的邁進。如侏儒漢斯愛慕著作為正常人的美貌女子一一秋千技巧表演者克里奧佩特拉,克里奧佩特拉心儀的卻是同為正常人的大力士赫克留斯,同時又垂涎于漢斯的財產,故而假意嫁給漢斯。在婚禮上,克里奧佩特拉的一句“怪胎”激怒了在場的畸形人,由此引發了一場悲劇。電影的最后,天上下著瓢潑大雨,地下一片泥濘,畸形人們用爬行的方式包圍逼近克里奧佩特拉,他們怪異、骯臟而猙獰,但是很顯然真正邪惡的一方卻是所謂的正常人。正是正常人對畸形人的嘲笑與利用,才導致了畸形人最后的殘忍報復,布朗寧利用這一看似以怪誕來做噱頭的影片拋出了“到底什么才是正常”的嚴肅質問。
與之類似的還有凱文.康納的《弗蘭肯斯坦》(Frankenstein,2004)以及一系列根據瑪麗.雪萊小說《弗蘭肯斯坦》改編的電影作品。主人公是一個誕生于實驗室的科學怪物(monster),而締造他的便是科學家弗蘭肯斯坦。弗蘭肯斯坦本身也可以視作一個“畸人”,他離群索居,一心在密室之中進行科學研究,這種自絕于人世的“父親”自然無法給予怪物良好的成長環境,在發現已經無法控制怪物之后,他選擇了殺死怪物來補過。怪物的外表異于常人,并且他因為自己的外貌已經被弗蘭肯斯坦定義為“邪惡之物”,被打上了“非人”的標簽,無法進入到正常人的群體之中。怪物擁有著如白紙一般的心靈,但是在一次又一次地嘗試向人類示好失敗以后,也意識到了自己的出生是“被詛咒”的,于是他選擇了在田野之中棲息,與弗蘭肯斯坦一樣躲避人世,并且懇求弗蘭肯斯坦再給他創造一個同類。在得到弗蘭肯斯坦的拒絕之后,絕望的怪物選擇了報復人類,并最終與弗蘭肯斯同歸于盡。怪物的出生并非他本人的錯誤,人類以理性創造了怪物,而富有人性的、多愁善感的怪物最終卻成為人們淡漠的感情和匱乏的科學道德的犧牲品。
這一類畸人實際上是“外丑內美”的,而作為“正常人”的人類則往往表現得對他人的痛苦視而不見,肆意踐踏他人的尊嚴或情感,應該為電影中出現的毀滅與災難負責。
二、心理扭曲的畸人形象
這一類畸人形象則可以被稱為“外美內丑”。在弗洛伊德的理論中,人類的行為是由其性本能來控制的,而性本能則分為肉欲的本能與愛的本能,一旦這兩種本能遭受到抑制,長期沒有得到合理的發泄,人的心態就會逐漸扭曲,先是感到空虛、失落或迷茫。而一旦生活中出現了攪動心潮的觸媒,最終有可能導致精神抑郁甚至是精神失常。而這樣心態異常之人若是行為難以受到法律與道德的約束,便有可能對他人造成傷害。在深受弗洛伊德理論浸淫的英美電影中就存在著大量本能無法釋放的畸人,其在外表上與正常人幾乎沒有區別,這一點則很好地為電影營造出了懸疑感和恐懼感。與第一類畸人不同的是,心理扭曲的畸人往往更易接近他人,甚至還會給人一種友善、真誠的印象,這就與其后來暴露真面目時的形象形成鮮明的對比。同時,由于電影在構圖、音樂等方面對氛圍的營造,觀眾有可能在已經意識到人物的詭異之處后,為劇中與畸人交往而渾然不知者備感擔憂,恐懼感便在這種擔憂中不斷升級。
以根據斯蒂芬.金小說改編,羅伯.萊納執導的《危情十日》
(Misery,1990)為例,在電影中,畸人無疑是護士安妮.威爾克斯,但是她卻是以一個樂于助人的正面形象出現的。電影一開始,男主人公一一暢銷書作家保羅.謝爾頓就因為暴風雪而遭遇了車禍,不僅自己雙腿受傷難以行走,加之大雪封山的情況下,他已經不可能順利返家。而這時候,保羅的忠實書迷一一獨居于山上的安妮卻從天而降出手相救,不僅將保羅安頓在自己家中悉心照顧,且一再表示自己對保羅書中女主人公米舍麗的喜愛。安妮自幼就暴露出了情緒不穩定且極具破壞欲的性格缺陷,最終表現為邊緣性人格障礙。當她獨自一人救起保羅后,她便沒有打算幫助保羅獲取外界的信息,而是一心想獨占保羅,并逼迫保羅修改他的手稿,因為她不愿意米舍麗在保羅的筆下死去。意識到安妮有躁狂抑郁性精神病的保羅一心想逃跑,卻被安妮打斷雙腿。電影中安妮也有暴怒、毀物、斗毆、罵人等怪異行為,但是其作為一個畸人的本質卻是體現在心理上的。安妮自認為是上帝派到保羅身邊來的,對于保羅離開自己有著過分的焦慮,不惜囚禁甚至摧毀保羅,是一個典型的“魔鬼護士”。
而英美恐怖電影的一個共同點便是,由于人類心理的復雜深奧,電影雖然給出了畸人的成因,但無意于探討畸人的出路。當電影對觀眾恐懼心理的營造已經成功,畸人的任務也就宣告結束了,電影一般都會在敘事中給予觀眾一個明確的答案,即電影以內心扭曲的畸人的死亡,或是他人對畸人的成功逃離而告終。例如,在佐米·希爾拉的《孤兒怨》(Orphan,2009)中,女主人公伊斯特擁有美好的外表,以一個懂事乖巧的小女孩形象贏得了約翰和凱特夫婦的喜愛,他們為彌補自己的喪女之痛而收養了伊斯特。不料伊斯特卻是一個患有垂體功能減退癥的30歲婦女,她有著如正常婦女一樣的性欲,然而卻無法滿足,為此伊斯特脾氣極為火暴,在手腕和脖子上都有精神病院禁錮她時留下的傷疤,饑渴壓抑之下的伊斯特選擇從一個孤兒院輾轉到另一個孤兒院,以孤兒的身份接近男主人公并企圖謀殺男主人公一家。在伊斯特身份暴露,殺死約翰后,為了保護子女而奮起反抗的凱特用力將伊斯特踢人冰河上的洞中,終結了這一畸人的罪惡。
這一類電影非常明確地將觀眾的恐懼體驗置于對主人公扭曲心理的營造而不是造型藝術上,讓畸人們不斷挑戰觀眾的道德良知和愛心,這種人物形象所帶來的驚悚感相較于單純以鬼魂、怪物來挑戰視覺承受極限的影片來說顯然會持續更長的時間,這也是英美恐怖片區別于亞系恐怖片的地方之一。
三、舉止古怪的畸人形象
英美恐怖影片之中還存在一類畸人形象,其外表正常,就心理而言也并沒有明顯的癥狀,是“外美內美”者,只是在特定的環境內,如時代變化后新浪潮對人的沖擊,家庭環境對人的桎梏等,其精神世界產生了畸變,最終導致的便是其行為舉止的怪異。相比起前兩類畸人的出現更具有偶然性,這一類畸人的出現更像是整個社會造就的悲劇,他們也較容易獲得觀眾的理解、同情甚至是喜愛,在以諸多離經叛道的舉動滿足觀眾生命本能沖動的同時,他們的遭遇對于同樣處于困境之中的觀眾來說,也提供了某種啟示。
如根據奧康納同名小說改編,約翰·休斯頓執導的《慧血》(Wise Blood,1979)中,男主人公莫斯便是一個環境造就的畸人。在軍隊中留下的傷痕將他推向“沒有耶穌,自我救贖”信仰,然而破敗的家鄉和怪誕的圖金漢卻已經不再是信仰生存的良好土壤,如圖金漢到處都是浮躁、唯利是圖之人。這些激發了莫斯神經質的秉性,他馬不停蹄地到處宣揚他創立的“不要耶穌”教,最終成為一個將自己弄瞎并每天不斷在折磨自己的苦行僧。莫斯的出現是與美國南方的蛻變息息相關的,所有人都在社會的巨變中無一幸免,在墮落的社會中莫斯的理想一步一步被摧毀,最終他發現他尋找到了一條通向內心的方法,那就是不斷地自殘。
畸人在受虐的同時也在施虐。又如,在派蒂·杰金斯的《女魔頭》(Monster,2003)中,女主人公沃諾斯之所以深陷罪孽深重的人生中,是與她的童年經歷分不開的。由于被雙親拋棄,她從小就忍受無休止的毒打和謾罵,后來又染上了毒癮。為了維持生存,她不得不在公路上為來往司機們提供廉價性服務。直到遇到年輕的女孩希爾比時,沃諾斯的生活才出現了一縷亮光。然而一來當時的美國社會對于同性戀依然十分苛刻,二來希爾比又愛慕虛榮,迫使沃諾斯繼續出去賺錢。而悲慘的童年賦予沃諾斯的學歷低下和粗鄙性格又導致了她求職屢屢受挫,不得不重操舊業。然而一個公路上的變態嫖客終于成為沃諾斯淪為畸人的誘因。在第一次殺人奪車后,沃諾斯成為一個心狠手辣的公路女魔頭。
畸人這一類不符合常理的人物能夠帶動起不符合常理的情節,對于恐怖電影來說有著重要的意義。英美恐怖電影為觀眾貢獻了一批畸人群體形象和不同的畸變原因,這批畸人形象關系著電影的藝術感染力,也展現著導演們對于怪異、變態等概念的理解和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