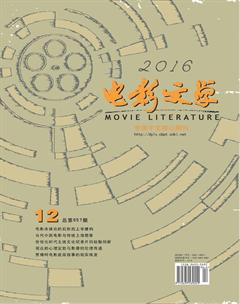羅恩·霍華德影片的影像敘事策略
張澤建
[摘要]美國導演羅恩·霍華德被美國最為權威的票房統計機構認定為僅次子斯蒂芬·斯皮爾伯格和羅伯特·澤梅克斯的第三位累積票房最高的導演。霍華德在擁有傲人的商業戰績的同時,其電影也是影評界和奧斯卡的寵兒。這是與他既能遵循好萊塢電影制作的游戲規則,同時又不忘記展現個人獨特的敘事魅力息息相關的。文章從混合性敘事策略、人物視角策略、懸疑設置策略三方面,分析羅恩·霍華德影片的影像敘事策略。
[關鍵詞]羅恩·霍華德;電影;敘事策略
美國導演羅恩·霍華德(Ronald William How-ard,1954— )被美國最為權威的票房統計機構認定為僅次于斯蒂芬·斯皮爾伯格和羅伯特·澤梅克斯的第三位累積票房最高的導演,但是與前兩者擁有電影的特許經營權(即拍攝系列電影的授權)不同的是,在《達.芬奇密碼》(The Da Vinci Code,2006)和《天使與魔鬼》(Angel & Demons,2009)之前,霍華德并沒有利用系列電影為自己爭取票房,其影片取悅大眾的實力可見一斑。而另一方面,霍華德在擁有傲人的商業戰績的同時,其電影也是影評界和奧斯卡的寵兒。這是與他既能遵循好萊塢電影制作的游戲規則,同時又不忘記展現個人獨特的敘事魅力息息相關的。單純就敘事技巧而言,霍華德并不是一個有意炫技的導演,相比起眾多敘事大師所熱衷使用的如環型敘事、章回體敘事、多線并進式敘事和倒敘等而言,霍華德更傾向于以一種樸實無華的方式來完成敘述,讓故事本身而非講故事的方式來打動觀眾。但在具體的敘事過程中,霍華德又能夠做到令電影的節奏張弛有度,視角富于變化,并將現代傳媒的觸角伸入到電影創作中來,共同實現影像敘事的感染力。
一、混合性敘事策略
羅恩.霍華德在電影的批判功能上一直保持著較為溫和的態度,但這并不代表霍華德無意于通過電影來展開反思。而其中最為明顯的便是霍華德在電影中流露的媒體批判。從20世紀80年代之后,霍華德敏感地意識到了現代媒體對于人類生活的侵襲。早在奇幻電影《現代美人魚》(splash,1984)之中,隱去魚尾去紐約尋找自己孩童時小伙伴的美人魚,就因為被電視媒體曝光了美人魚的真實身份,隨后被人們以科學研究的名義關了起來。美人魚和艾倫·鮑爾兩人的愛情也從私人事件變成了全民事件,陷入都市生活的物欲橫流之中。隨著時代的發展,霍華德對“娛樂至死”年代現實社會之中新聞界對于人們生活的正面或負面影響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這反映在他的電影之中便是有意使用了混合性的敘事策略,即將觀眾在潛意識之中理解的電影敘事的“假”和傳媒敘事的“真”相混合,導演在銀幕之上重建起來的是一個復雜的世界,甚至情節被有意地割裂,其內涵讓觀眾揣摩不盡。
以政治電影《對話尼克松》(Frost/Nixon,2008)為例,電影敘事被以一種脫口秀式電視節目的方式來呈現。整部電影的主體部分由大衛.福斯特對前美國總統尼克松的采訪組成,其余部分則依然保留了戲劇性因果敘事。在簡要地介紹了這一次采訪的前因,如福斯特作為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記者如何聯系上了想為“水門事件”開脫的尼克松,兩人都如何想著主導這一次對話等。訪談節目開始,雙方你來我往,唇槍舌劍,電影所運用的鏡頭語言和時長基本都與訪談節目保持一致。電影此時已經由邏輯敘事進入到了心理敘事,即在兩人的來言去語之中,觀眾所關心的已經不是具體的事件,而是尼克松本人的主觀心理變化過程。
而霍華德的《艾德私人頻道》(Edty,1999)則是將電影與一款24小時真人秀節目相混合,使整部電影呈現出一種“戲中戲”的敘事模式。主人公艾德被NWBC廣播公司找來專門開設了一個實況拍攝節目,讓他的私人生活每時每刻都暴露于公眾面前。“戲中戲”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平淡而乏味的艾德日常生活,這同樣使得觀眾毫無興趣,節目收視率令節目監督十分難堪;二則是意外帶來的戲劇性,如艾德在探望哥哥時發現哥哥出軌,導致觀眾目睹了一場跌宕起伏的三角戀,又如電視臺故意聘請模特去勾引艾德等,都導致了收視率的一夜飆升。這種混合性敘事將對情節的編排隱藏于直播模式之中,觀眾在做電影觀眾的同時也是節目的觀眾,這一敘事策略新奇而能促使觀眾進行思考。
二、人物視角策略
在文學創作之中,敘事視角的變換是使得作品充滿陌生化效果和對比效果的重要策略之一,如零焦點與內外焦點等敘事視角便是在文學之中最先得到實踐的。電影亦借用了文學這種多變的敘事角度,盡管對于觀眾來說,電影之中敘述人的變化不能用一目了然的人稱和詞匯變化來標示,但這種敘述人被更換的模糊性反而有助于增強電影的審美效果。霍華德的敘事策略使電影在表現“客觀現實”的同時,又能夠進入到觀眾與劇中人的主觀世界之中,構建出一種“主觀現實”。
以霍華德贏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的《美麗心靈》(A Beautiful Mind,2001)為例。影片是數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約翰.納什的人物傳記片。而電影所關注的并非納什在學術上不斷向前開拓的過程,納什早在讀研究生時就發表的博弈論可以說已經成為他一生中最高的學術成就。霍華德抓住了納什人生中最令人唏噓的一段經歷,即長期罹患精神分裂癥,并一直抗拒醫院給予他的治療,以至于最后只能在普林斯頓大學形容枯槁地游蕩,成為傳說中的“數學樓幽靈”。在電影中,霍華德靈活地出入于內外視角之中。納什在剛進人大學時就擁有了一個知心的舍友,舍友還有一個乖巧可愛的侄女。隨后納什被國家安全部門召集從事極為重要的,需要對周圍人保密的破譯密碼工作,他的手腕里也被植入了用來進入國家安全局的芯片,納什開展了一系列繁雜的計算工作……觀眾也同樣對此深信不疑,事實上這一切都是霍華德以納什的內視角來拍攝的。
即使當納什被送入精神病院之后,部分觀眾依然堅信納什為國家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因為安全局沒有留下任何線索而導致納什被冤枉為神經病,甚至希望納什不要吃下那些會令他思維遲鈍的藥。而所謂的破譯密碼、安全局特工乃至納什的舍友都是不存在的,這些都是納什自己想象出來的產物。而納什的痛苦與觀眾是一樣的,即他無法分辨到底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在被不斷地進行電擊和服藥治療后,納什的日常生活也一塌糊涂,甚至差點淹死自己的孩子。霍華德用視角的切換來宣告這一殘酷的事實,即當納什在對國家安全局特工說話,懇求他不要再來找自己的時候,鏡頭一轉,納什正在對著空氣喋喋不休,而周圍經過的人都以奇怪的眼光看著他。在表現納什的康復時,霍華德同樣是通過視角切換來進行的。納什又一次看到了舍友與小女孩,他從本能上不希望他們離開他的生活,可是他的理智又告訴他這一切都不是真的,因為小女孩多年來始終沒有長大,在納什的溫情告別中,舍友與小女孩微笑遠去。正是霍華德的這種處理方式,納什的經歷顯得尤為瘋狂而離奇,同時還帶有些許溫馨。
三、懸疑設置策略
在傳統故事片中,敘事一般是采用“上帝視角”的,這樣的敘事能夠更完整地將整部電影的故事脈絡呈現給觀眾。而霍華德則有意在上帝視角之中又加入精彩的懸疑,讓觀眾在觀影過程中體驗著一次幾乎無法喘息的、激動人心的歷險。當在進行情節的鋪墊與人物的介紹時,影片采用上帝視角進行較為詳細的介紹,讓觀眾理解故事的有關信息,但是在最為關鍵的部分則將“謎面”在電影一開始拋給觀眾,而在電影的最后才將謎底揭曉,使觀眾的好奇心能夠保持到最后。而電影的主干部分則圍繞著懸念的揭示而展開,且人物往往面臨著極為嚴峻的局勢,甚至面臨生死關頭。觀眾在被“謎面”吸引之后,對于解謎的迫切心理使觀眾很容易便代人了主人公的角色,跟隨著主人公經歷一波三折的情節,急切地想了解劇情將走向何方。
這方面最為典型的莫過于改編自丹·布朗暢銷小說的《達·芬奇密碼》與《天使與魔鬼》。兩部電影都以一樁神秘的謀殺案展開,并且隨著主人公的活動,觀眾發現謀殺案還在接二連三地發生,主人公在需要破解甚至是阻止一樁樁刑事犯罪的同時又面臨著諸多科學、歷史、宗教等難題,并在外部條件的限制下處處掣肘,如《天使與魔鬼》之中正值梵蒂岡新教皇的選舉盛事;甚至是遭到追捕與追殺,如《達·芬奇密碼》中主人公蘭登被法國警方視作犯罪嫌疑人等。并且在兩部電影之中,導演都給出了疑似的犯罪嫌疑人,但是導演故布疑陣,在影片的最后觀眾會驚訝地發現,兇手或幕后指使者并非前面嫌疑處處指向的對象,而是另有其人,并且真兇還是對主人公給予過莫大幫助之人。電影的敘事也就由此扣人心弦,并在真相大白之后讓觀眾喟嘆不已。
即使是在其傳記影片《鐵拳男人》(Cinderella Man,2005)中,霍華德依然保留了懸念。影片根據真人真事改編而成,現實之中的原型人物并沒有死于拳臺之上,而是利用了最后勝利的獎金安享晚年。對于稍微了解故事背景的觀眾而言,電影的結局是不難猜測到的。整部電影的敘事也是平鋪直敘,由影響主人公吉米.布洛克人生命運的幾場重要的拳賽串聯而成,在鋪墊了布洛克一家所面對的重重生存問題之后,很顯然作為一部帶有勵志色彩的影片,主人公勢必在最后一戰中力挽狂瀾,挽救家人和自己作為男人的尊嚴。但是霍華德有意在電影之中渲染了敵人麥克斯作為拳王曾經將兩個人活活打死在拳臺之上的歷史,這一新聞甚至令布洛克的經紀人都深感不安,而一向鼎力支持丈夫事業的妻子梅也因為目睹朋友丈夫的葬禮而強烈地反對布洛克參加這一戰,而麥克斯也有意挑釁布洛克,聲稱在梅做了寡婦之后會如何“照顧”她,等等。同時布洛克肋骨上的傷也十分嚴重,此時觀眾已經產生了對二人孰勝孰敗的關心,而在最終的血戰中,旗鼓相當的兩人也沒有以一方倒地而結束,而是裁判在經過了復雜的統分后宣布布洛克勝利,期間連布洛克的經紀人都失態地表示裁判一定在搗鬼。可以說,整個拳擊場因霍華德極具懸念感的敘事而變為氛圍緊張的人間煉獄。
與之類似的還有同樣有著現實基礎的《阿波羅13號》(Apollo 13,1995)。電影根據發生于25年前的一段驚心動魄的人類對太空的征服史改編而成。盡管觀眾明白遇險的阿波羅13號最終一定可以轉危為安,但是因為霍華德在制造懸念上的出色,觀眾在阿波羅13號順利著陸之前始終都保持著沉重的心情。首先是宇航員們面臨氧氣和能源的缺乏,而不得不就地取材做出簡易過濾器,并且緊急取消了登月計劃,隨后是嚴寒的來襲,導致其中一個宇航員弗雷德發起了高燒,全體宇航員此時面對的是生理與心理上的巨大壓力。為了盡可能地節約能源,他們盡量不開啟電腦而使用手來操作要求極為精確的任務。而地面上的工作人員也在絞盡腦汁地為他們設計出返回地球的最節能程序。最后是當所有人所能做的工作都完成后,宇航員們只能以聽天由命的心態來等待重返大氣層,此時的觀眾還需要為他們擔心機艙的隔熱層與降落傘是否有損害。更令人揪心的是在飛船在大氣層中高速摩擦之時,其與地面的通信是中斷的。直到飛船著陸艙中傳來對休斯頓的呼叫時,電影的懸念設置才告一段落。如果說《鐵拳男人》中的懸念制造來自于敵方的“攻心”策略,那么《阿波羅13號》之中的懸念則由現實中的重重困難組成。
綜上,羅恩·霍華德并非一個試圖采取顛覆性敘事手法的導演,但是他在電影之中展現出來的敘事手段是靈活多樣的,充分展示了影像在敘事上的無窮魅力。霍華德的混合性敘事策略、人物視角策略以及懸疑設置策略拓寬了電影的表達空間,深化了電影的文化內涵,也顯示了霍華德在擺脫傳統敘事手法束縛的努力。這也正是霍華德電影為何能做到“曲高和眾”,在藝術性與商業性之間保持平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