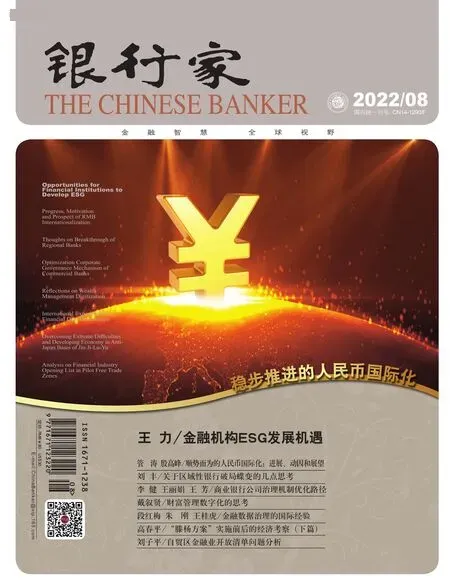經濟形勢分析漫談
王松奇
一、題目
這里說“經濟形勢”,由于沒有“當前”這樣的限定語,因而可以將之理解為一般性的經濟形勢分析。如果加“當前”定語,那就是短期經濟形勢分析,在經濟研究領域所謂“短期”通常指一年以內,在做形勢分析講座時,如果講短期問題,一般都要引證最近兩三個季度的數據。
在經濟形勢分析時常看到有人愛加“宏觀”定語。如是,則文章或講座的內容就會被限定在非常狹小的范圍,因為西方經濟學中規范的“宏觀”定義就是總量問題,它所牽涉的大體是總供給總需求儲蓄投資消費生產出口進口生產可能性邊界市場出清過剩失業就業等等一系列人們熟知的概念。西方經濟學家如果搞宏觀經濟形勢分析的講座通常是把上述這些概念的現實或歷史數據變成曲線圖在那里折騰來折騰去。
既非短期又不限定宏觀只是一般性地講經濟形勢,那就可以國內國外、短期長期、理論實際、數據案例、政策動向、問題規律地任馬由韁隨意發揮了。
二、數據
經濟形勢分析應當是以數據為基礎,這是毫無疑義的。什么人可以不用數據?通常有兩種:一種是特別聰明的人;二是特別權威的人。特別聰明的人可以用邏輯判斷和理論推演就把情況說得絲絲入扣、現象本質;特別權威的人如2016年5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的《開局首季問大勢——權威人士談當前經濟形勢》文章中被訪談的那位權威人士在洋洋灑灑一萬多字的談話中僅提到一個GDP增長數據,其他數據全都不用卻也把降杠桿、大水漫灌、L型等說得有鼻子有眼。
作為只是受過一定正統訓練的普通研究人員,人微言輕,無論講課寫文章在經濟形勢分析時必須以數據分析開路,這樣才顯得貼近實際。
在中國,引用數據最頭疼的是數據的準確性問題。地球人都知道,中國有一個不可否認的國情是“數字出干部”。地方官員們常常以數據證明的政績謀求上級的重視以之追求升遷,因此過去許多年都存在黨委管統計數據的情況。GDP數據各地在上報時不同程度地摻水即虛報一定比例已成公開的秘密。僅以2015年一季度的數據為例:全國GDP為140667億元;而31個省份一季度總和為143072.91億元,超過全國總量2405.91億元,這種地方加總數據與全國總量數據“打架”情況是中國的舊常態,問題的根源就是地方官員出于政績動機的數據摻水。
雖然數據有不可信之處,但在中國討論經濟形勢時又離不開數據,怎么辦?出路有二:一是甄別修正;二是自訂指數。甄別修正就是根據經驗將最可能摻水的統計數據估計出摻水系數,然后透過修正值看形勢的真實狀況;自訂指數最經典事例則是克強總理在遼寧省當省委書記時說過的——我不大看統計局公布的數據而主要看用電增長率、信貸增長率和鐵路貨運量變動數據,這三項指標后來被國外媒體冠名為“克強指數”。
在過去一些年我經常會被人請去講經濟形勢,講經濟形勢時也常常以數據分析開路。個人認為盡管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可能存在水分,但人民銀行調統司的數據卻是千真萬確的,也就是說中國的金融數據不存在造假問題。說到這里,有人可能會說,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瞞報現象難道不是很普遍嗎?商業銀行的報表肯定有不真實的內容,那人民銀行調統司的數據在采集基礎方面不也存在摻水問題嗎?這樣說,實在讓人無言以對。在此等情況下,我們引用任何數據都應當小心翼翼才是,多用些甄別修正的法子就是了。
三、邏輯
中國經濟是大國經濟,產業狀況、行業結構、要素稟賦、區域發展差異等等都有自己的特點,因此要真正了解中國國情著實不易。更令人著迷的一點還在于作為轉型經濟國家,30多年體制制度背景一直變動不居,決策層多年來一直把改革開放當成執政目標性口號,而每一屆領導集體的改革決心、改革路線圖及執行落實能力存在相當大差異,這又為我們著眼于長期的形勢分析帶來了一些不確定性。例如國企改革,我們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60條中勾畫出了一個總體改革藍圖,之后又新推出了一個《國企改革指導意見》,但這個指導意見和十四屆五中全會即20多年前的那份《指導意見》比,有些內容好像還退步了,對于國企改革,我們的領導人的說法此一時彼一時,大家覺得無所適從。以至于到現在為止,我們對國企改革的最終目標和階段目標、實施路徑、保障措施、動力機制等等至關重要的問題都不甚了了。在中國,講形勢牽涉到長期問題就必須和改革和體制制度相聯系,而路線圖如果不清晰,你長期問題就很難談。
所以,為安全省力起見,我們還是多講中短期問題為妙。中短期形勢分析時,有些邏輯關系是板上釘釘簡明清晰式。如用電增長率通常都能準確反映全社會生產景氣狀況,銀行信貸增長率一般情況下都是貨幣政策松緊的準確尺度,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乘以0.7的系數通常就是中國GDP剔除了水分的真實數據等等。在中國各產業部門中,金融部門是最令人犯暈的部門。比方說,“股市是經濟的晴雨表”這句老生常談的格言式論斷在中國就偏偏失靈。中國股市常常以脫離或不吻合于中國宏觀經濟表現而聞名于世,經濟形勢趨冷時我們的股市可能狂漲不止;經濟不斷向好時,我們的股市也可能跌跌不休。沒辦法,它就這么任性。另外,還有更讓人想不明白的是我們的貨幣和物價統計數據,中國的M2與GDP之比已達200%,用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教條去分析中國似乎早都該出現野馬式通貨膨脹了,但至2016年二季度,我們的CPI又回到“1”時代,而PPI已連續下降52個月,似乎通縮的陰影仍揮之不去。顯然,中國有一大堆“迷失的貨幣”(Missing Money),錢都到哪去了?每當想到這個問題,每當想這個問題百思不得其解又突然意識到自己也被人稱之為“金融學家”時就常常產生強烈的跳樓沖動。大約在四五年前,中國經濟學界突然出現一陣聲浪說中國是用貨幣超發創造了30多年經濟超高速成長神話。說這種話的人不僅有德高望重的老經濟學家、半生不熟的中青年經濟學家還有曾經在中央銀行擔任過要職的學者型官員。這些人有一個重大疏忽,即如果一個經濟體能用貨幣超發創造持續達30年以上高速成長經濟周期,那么,在天堂里仍顯榮耀的那些貨幣面紗論、貨幣中性論等理論先賢們恐怕個個都得找繩上吊了。貨幣是否超發,這牽涉了很多理論和貨幣供給實踐問題,那些沒有受過長期金融教育研究訓練的還是少談為妙。
四、政策
政策是一種特殊資源,一個經濟體政府是否強大的衡量標志就是看其政策資源的利用能力。
政府制定政策可以從理論出發(例如改革前的情況)也可以從實際從常識出發(例如小平同志的改革開放政策)。這些可能是籠統意義上的政策,在宏觀經濟領域調控政策通常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幾十年前,也有美國經濟學家提議將收入政策也看成是宏觀經濟政策,但應者寥寥,最后已無人提及。所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就是標準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宏觀經濟政策管什么?通常來說,它們就是經濟成長和發展大棚里的溫度調節器。氣象學家們常說“溫度決定一切”,例如假若全球年度平均氣溫再提高6度以上,人類就可能滅亡,說的就是溫度的重要性。一國的經濟成長和發展也是同樣道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之提供的溫度背景,決定了社會生產力達于其可能性邊界的程度,亦即全社會物質資源的利用程度,溫度過熱過冷都不利于經濟成長和發展,而保持適中的溫度背景又難度甚高,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經濟學家關注的永遠是效果,因此,要從經濟運行實際出發制定政策檢驗政策不斷地改善和修訂政策,誰管經濟誰負責,從實踐效果出發該怎么干就怎么干,這就算盡職盡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