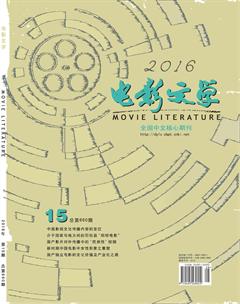解讀電影《鄉村里的中國》的農民生命觀
褚興彪
[摘要]《鄉村里的中國》是一部紀錄片,以第三方為觀察視角,以普通鄉村普通個體為形象載體,客觀記錄當代鄉村村民的日常生活,展現民眾對生命觀的認知。生命是人類共同關注的話題,鄉村以其上承下傳的文化張力,謹慎而強韌地延續農民生命觀。文章從影片中農民對“生命”本原思考、金錢與“德”的博弈、存在感與“中庸”的平衡三個方面進行解讀,認為對“天、地、人、神”的敬畏與和諧具有正向性; 對“德”的堅持與金錢的誘惑存在糾結;存在感的尋找具有“中庸”的適宜性。
[關鍵詞]《鄉村里的中國》;生命觀;紀錄片
當下,鄉村題材電影主要聚焦于“希望田野”般的主旋律,而《鄉村里的中國》以紀錄片的方式,失卻語言重構、情結人為導向、規律化結局的電影藝術形式,展現原生態鄉村生活,包括原生態田園、民間語言、民俗形式、相處方式等,真實得“令人窒息”。影片不僅忠實地記錄當代鄉村的真實處境,也帶給受眾更多社會思考。
導演焦波是一個攝影記者,他的攝影畫冊《俺爹俺娘》在國內外反響巨大,拍攝電影并不是他的專長,但“生于斯長于廝”的家鄉情結表現以及對鄉村的真實理解使本影片產生強烈震撼。影片以“一年”為時間周期,以“節氣”為連續點,真實展現山東淄博沂源縣中莊鎮杓峪村的鄉村生活。影片沿兩條主線展開,分別為兩個原生家庭(杜深忠家、杜洪法家)一年的生活歷程。杜深忠家四口人,即夫妻倆與一兒一女,這一年,夫妻倆種的蘋果比別人家結的少,女兒結婚了,兒子在讀大學;杜洪法家就父子倆,父親種蘋果,兒子讀大學,這一年,兒子學業取得進步,父子關系更融洽了。內容拓展分縱橫兩個方向,即橫向的鄰里關系與縱向的國家形勢發展。
生命觀是人類社會道德倫理的“核準”,生命的意義在于“核準”的建立,由此,生命觀即為人類“觀念”認知所主導的生活狀態,是本原力量的顯化創生。[1]影片《鄉村里的中國》通過村民日常生活表象,折射出他們對待生命本身、生死、時代變遷、鄰里關系處理、金錢與道德、生命存在價值等多角度審視態度,從中反映他們對于“生命”本原的思考、金錢與“德”的博弈、“中庸”與存在感的平衡。
一、關于“生命”本原的思考
生命本原是生命過程的展現,即“生、老、病、死”的客觀流程及精神狀態。老子認為道為“萬物所由”,是物之本體與本原,由此,生命本原在于遵循自然規律。民間對于生命本原的思考在于“天、地、人、神”的關系思考,體現出“逐善”心態,這一思考結果呈現出祈福納祥的民間信仰表象。影片《鄉村里的中國》表現的杓峪村民俗信仰不刻意、不精鑿,如行云流水般體現在民眾生活之中。
影片一開始即為“立春”,春天萬物萌動、蓄勢待發,是一個令人振奮的節氣,杓峪村關于春天祈愿有以下表現:杜深忠作為“村中的才子”為村民的羊圈寫了一個大大的“春”字,并說 “龍年春到發羊財”,其中“羊財”具有雙關的吉祥寓意,即羊群壯大發羊的財,因“羊”通“洋”,“洋財”也為大財之意。主家說“寫得挺好”“不孬”,體現了順心順意的民間祈愿。在門口做“女紅”的老人們討論著“縫黃尾巴的不好看”“紅公雞綠尾巴”“頭上縫個豆子,小孩不生痘子”等,這些細節顯示了村民通過民間造物祈愿吉祥。夜晚村民圍著篝火舉行“咬春”民俗活動,“下面我們開始咬春,咬蘿卜”“誰咬著了誰就有一年的好時運”,一個小女孩大喊:“我咬著春了,我咬著春了。”一個老奶奶笑著說:“好不容易咬著春了,你還把它吐了。”從而把活動推向歡樂的高潮。祥和、樸素、歡樂的春天民俗是村民對一年嶄新的期望,不管這一年有多少坎坷,春天的祈愿是村民發自內心的精神支撐,具有引導生活的正向性。
生命傳自父母承于子孫,尊老愛幼不僅是社會規約,也是村民內心自覺的樸素生命觀,其中有對天地神靈的祈求,也有對現實生活態度的表露。影片對子孫興旺、老人安康有著含蓄表達,如在婦女生育檢查時村長與一個婦女的對話,村長張自恩問:“不查能行了不?”“能,他說叫我來這一次就行了。”“你今年多大了?”“49了。”“那你還得來,現在生活好了,你還能生,還得來。”這一組對話的邏輯為“還得來”,因為“還能生”,以直白的對話含蓄地表達對生殖的祝愿,雙方能心領神會的主旨在于民俗心理的切合;當張光愛家的果樹被人噴了除草劑,從而與張光學家的矛盾得到激化,矛盾處理非常棘手,但雙方退讓一步的原因是“我是看在小孩面上”,底線是“小孩想考學也好,想去當兵也好,咱不牽扯”,這種想法除去鄉村處理人際關系的秩序規范外,還可以理解為對后代的愛護,有“愛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傳統美德。通過神性對后代庇護的表現有兩處:一為張自軍葬禮下葬時喊道“孝子填倉,萬石余糧”“滿了嗎”“滿了”,即人死為神,可以在另一個世界保佑后代富足,使悲傷的家屬得到精神安慰與寄托;另一處為杜深忠女兒出嫁的儀式,燒香時唱詞為“觀音奶奶兩對包袱,月老兩對,路神一對,保佑平安的一對”“今日良辰,三炷清香,酒席香案,請神高高在上,案前紅綠包袱各一對,內有金銀財寶,黃錢數尊,明人指點,凡人操辦,今日吉時,以紙馬香錁,隆重奉還,各路尊神永保佑善信女大喜之際,大吉大利,平平安安”,男方迎娶時新郎說:“我把新娘的蓋頭挑一挑,想要兩個大胖小。”這些習俗都有“逐善”內涵,把祈愿通過神靈保佑及內心暗示獲取吉祥意象,兆示生生不息的民眾精神。
二、金錢與“德”的博弈
從影片中也能看到現代商業氣息對傳統的農業文明帶來的觀念沖擊。商品社會物欲橫流,因金錢誘惑而使“生存之道”出現變動,但金錢與“德”未必是你進我退的反比關系,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恰恰說明二者的正比遞進。在經濟快速發展的時代,巨大的金錢沖擊會使部分人利令智昏,即使平常鄉村也會波及。《鄉村里的中國》通過對某些事件的發生即處理方式反映出當下農村人對二者之間的博弈。
為使城市綠化快速有效,到農村購買古樹名木的事情屢有發生。杓峪村的古樹主要為柿子樹,樹齡達百年,不僅有維持生態的作用,也有造福子孫后代的經濟意義。對此,村民自然心知肚明,“少了一百年,長不了這么大的樹”。經過權衡,有村民最終把樹賣掉,他們自嘲道:“俺這幾個人給這棵樹辦了農轉非了。”貌似樂觀、幽默的語言,卻闡釋了無奈、不舍得、可惜、不得已等多種心態。局外人對此評價也出現糾結心態,通過杜深忠夫妻倆的對話可見一斑: “這叫剜了大腿上的肉貼到臉上”“就是看到那點錢了”“人家都肥得哼哼的,你在這里窮得吱吱的”“他別哼哼,再下去幾年以后,子孫后代我叫他哼哼”“現在只要有錢就行了,有錢的王八坐上席,沒錢的君子下流坯”,這一組對話中杜深忠妻子堅持金錢至上,而杜深忠堅持不能急功近利,最終二人誰也說服不了誰。但是在自家事情的處理上,卻尊重人的真性情,如得知女兒戀愛后,他們共同認為:“只要是你們兩個人互相真心相愛就是條件,我不反對”。當女兒出嫁時,夫妻倆拿出兩萬塊錢給女兒,女兒說:“你們養我這么大了,還得搭上錢。”夫妻倆說:“怎么是搭上呢?”體現出對女兒的關心,從而將“金錢”條件降低一格。影片中因分錢鬧矛盾有兩次體現,一是關于賣樹,“前幾天那里不是賣了一棵,錢沒分明白還差點打起來了”;二是關于張自軍事故的賠償,逝去的人剛下葬,家里人為525萬元的賠償款鬧得不可開交,因錢而產生的是非不好評價,村民對此的態度則是豁達而無奈的,即凡事都要想得開。
物質的貧乏也使得金錢可以替代某些“理”,如張光愛與張光學家的矛盾,起因與錢無關,卻因張光愛被打,此種背景下金錢就有了替代性,即賠一萬塊錢或再打人家還回來。村長作為“調和人”,講的“生存之道”是為了小孩、為了鄰居雙方都退一步,從而將“錢”的要求降低。由此可知,鄉村人重在對“順心”之“理”及相處之“道”的遵從。年終村委會分酬金,因發的酬金不夠某些委員的摩托車油錢,村長自己拿出二百元錢,委員沒要錢卻氣呼呼走了,大家最終的意思是順順利利過年,錢多少其實并不重要。
三、存在感尋找及中庸表達
每個人都有天性及愛好,但受環境影響,也許不能從事自己最熱衷的工作,于是在生活中不斷調整自我認知以尋求發展。尤其是當代社會的發展迅速,更多人通過更換工作及環境獲取理想的生活狀態,這種環境的適應建立在正確客觀的自我認知的基礎上,是一種健康積極上進的心態,因此,存在感尋找是人生定位基礎。 “自我認知包括兩個方式,即場獨立型自我認知引導場獨立型認知、場依存型自我認知引導場依存型認知方式”[3],換句話說,則是客觀自我認知與受環境誘導的自我認知。影片中表現的杓峪村村民自我認知體現在每個人的個性保持,環境誘導包括村莊現實環境與外界環境。杓峪村的村民在自我認知的基礎上尋找適宜存在感,而存在感的尋找則是通過中庸之道的論證得以平衡。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中庸是“至德”的高度,后演進為“極高明而道中庸”,而尋常百姓對此的表現則為不偏不倚,無過不及。[4]影片對此的展現體現了當代鄉村對傳統文化延續及生生不息的上進精神,是當代中國鄉村農民生命觀的真實寫照。
杜深忠有文化人愛好,如寫小說、練書法、拉二胡、彈琵琶,但在杓峪村種蘋果他就不是內行了,果子總比別人家結得少,他認可這一點,但也通過堅持個人認知體現存在感與生命價值。影片中夫妻倆給蘋果樹點花,杜深忠說自家果樹開花少,自己還不如半個女人,妻子接話說是夫妻兩人都懶很匹配,但當妻子說“下三濫找那惡兒郎”時杜深忠發火了,這其實是夫妻倆自謙,但當謙虛過度則傷害了杜深忠。果樹管理不好是技術不行,但也不能打上“惡兒郎”的標簽,畢竟他還是個文化人。另一個片段體現在村長找杜深忠寫毛筆字,杜深忠說怕寫不好,村長寬慰他說這不是練書法,杜深忠則反駁說不是練書法你來寫,村長馬上說:“我只是會說,不會寫,你才是我們村的才子。”這段交流是外界對杜深忠的評價,也符合杜深忠的自我認知。存在感的中庸表達是建立個人價值、樹立人生信念的基礎,也是鄉村民眾獲取自信的方式。
四、以務實為基礎的人生價值判斷
杓峪村村民為改變命運而做過許多嘗試,方式主要有求學、參軍、外出務工、外界援助,這些嘗試有辛酸也有慰藉,這些改變有較強的務實性,因務農辛苦而對后代讀書寄予較高期望,影片對此有兩處表現,兩處共性在于以現實生活為參照給予后代勵志性說服,一處為“你看我們做豆腐賺錢容易嗎”并導出“成不成才要看你有沒有志氣了”。另一處為杜深忠對兒子的教育:“咱為什么拿出所有的精力來供孩子上學……咱就是沒有辦法、無奈,這土地不養人,你要好好讀書。”影片中對外出“打工”的認識較為悲觀,有村民因打工失去生命,他們認為大部分人都是因生活所迫才外出,通過打工經歷認為打工是艱難的,如“五年掉了十三個牙”,務實性使他們將對打工的排斥轉移到對土地的依賴,通過種植經濟作物、提高技術實現鄉村致富,但對“科學院的、大學教授” 推銷式支持持排斥態度,對政府支持采取積極態度,如對“第一書記”修路的配合,因為基礎設施建設對村莊發展有支持作用。他們認為農業觀光園項目對經濟發展有促進作用,因此村長兩次爭取項目傾斜。
五、結語
《鄉村里的中國》通過對現實社會表征記錄呈現當代鄉村的真實面貌,因選題取自平常鄉村、平常人物而使其具有時代性特征,通過村民信仰、相處之道、社會適應等角度反映當代鄉村人的生命觀,表現在信仰的正向性、關系處理的調和性、積極進取的人生價值趨向。影片對于客觀理解鄉村文化、人生價值判斷具有積極的社會現實意義。同時,其反映的鄉村經濟、發展瓶頸也對“三農”發展策略提供基礎,具有時代性意義。
[基金項目] 本文系2014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項目“廣西古村鎮景觀設計特征與文化傳承研究”(項目編號:14EG156);2015廣西教育廳社科基金項目“廣西古建筑空間特征解析與傳承保護研究”(項目編號:Ky2015yb019)。
[參考文獻]
[1] 吳正榮,馮天春.《壇經》大生命觀論綱[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2] 楊守戎.莊子生命本原論[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12(12) .
[3] 廖鳳林,車文博.自我認知類型引導認知方式的實驗研究[J].心理科學,2005(03) .
[4] 鄭男.儒家的中庸思想演進[D].上海:上海師范大學,2013 .